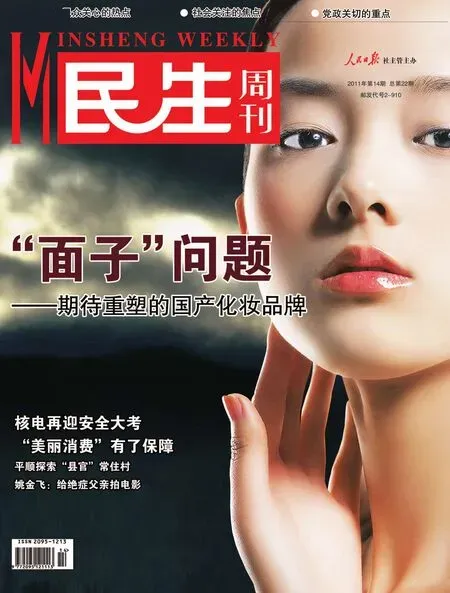核電:魚與熊掌能否兼得?
□ 本刊記者 韓宇明
核電:魚與熊掌能否兼得?
□ 本刊記者 韓宇明
福島之后,一時間人們談“核”色變。“核電”也成為社會關注、民眾關心的熱門話題。
安全性能、技術爭議,核電發展自“切爾諾貝利”核危機之后,再次遭受輿論的巨大壓力。對于核電安全的擔憂,使得我國開始開始重新考量核電發展布局。然而能源緊缺,減排壓力,卻讓發展核電成為不得不走的能源之路。
安全與核能,真得就像魚與熊掌一樣,不能兼得嗎?就此,記者做了專題調查采訪。
核電發展目標或放緩?
國務院的一紙通告,讓此前炙手可熱的核電項目突遭“變故”。3月16日,國務院連發5條措施,要求立即組織核電項目安檢,不符合安全標準的立即停止建設,暫停審批核電項目包括開展前期工作的項目,同時抓緊制定核安全規劃,調整中長期規劃。
在此前召開的2011中國能源工作會議上,核電項目規劃剛剛得到“擴容”。2006年我國頒布的《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2005-2020)》中提出的目標是,到2020年我國核電裝機容量為4000萬瓦,而那次會議上目標被修訂為8600萬瓦,增加了一倍多。“十二五”規劃綱要更是對此做出了布局,到2015年,我國核電發展的規模將達到4000萬千瓦,這意味著早先制定的目標要提前5年完成。
因為福島核危機,這一切或許都將面臨變數。
實際上,福島事件發生的第二天,環保部副部長張力軍就曾表示,我國核電發展的決心和安排不會改變,但是會吸取日本的經驗教訓。中國核能行業協會副秘書長馮毅也曾對媒體表示,福島事故讓世界核電發展面臨嚴峻挑戰,但不能因噎廢食,當務之急是理性地拿出應對措施。但是3月27日,國務院相關通知的發布,還是給我國核電發展布局潑了“冷水”。
核電建設需要高投入和高技術的支持,而且帶有較大風險。我國核電建設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從無到有,2010年裝機容量已到達1080萬千瓦。按照國務院通知下發前的計劃,2015年要達到4000萬千瓦,2020年則要達到8600萬千瓦。這就意味著,我國核電裝機容量五年內要增長3倍,10年內增長7倍。此前30多年,我國核電容量也才剛剛達到千萬級別,這也難怪不少分析人士認為,過速發展,難免有“躍進”之嫌。
部分企業和地方政府發展核電熱情過高、目標過大、動作過快,會給經濟和安全帶來較大風險。
我國核電項目經過30多年的發展,已經有13個運營核電機組,近30個在建機組和90個籌建機組。在建規模居世界首位,超過了全球在建核電機組容量的40%。而2020年8600萬裝機容量目標如果實現,我國核電規模則有可能達到世界第二。這些巨大的數字即使不會因為福島而改變,至少也會有所調整。
國家核安全局局長李干杰此前在清華大學的一次演講中就提到了這一點,他認為,部分企業和地方政府發展核電熱情過高、目標過大、動作過快,會給經濟和安全帶來較大風險。目前核電發展的人才瓶頸較大,在人才不能保障的前提下,盲目擴張必然會帶來安全隱患。從這一點上看,我國核電發展布局即使不會有根本性的改變,在這些具體的操作層面也會有所調整。
不得不走的道路
核電發展正在經歷前蘇聯“切爾諾貝利”事件后最大的考驗。但是,幾乎沒有專家懷疑福島核危機會讓核電發展受到太大阻礙甚至停滯不前。
“我國核電發展的路子不會改變。”3月25日,在中國工程院文獻情報中心參加一次“核安全研修”活動時,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中國工程院院士潘自強如此展望我國核電發展趨勢,“國家指定的核電發展數字也不會有太大變化。”在潘自強看來,發展核電不是應不應該發展的問題,而是必須發展的問題。
目前世界上采用的能源主要是以煤炭、石油為主的化石能源,這些都是不可再生的,一旦用完就不會再有。這時候就必須發展替代能源。太陽能、風能等可再生能源無疑是最優選擇,但是目前技術和資金上都需要進一步突破,還不能大規模投入使用。核電就成了化石能源與可再生能源之間的一個“過渡能源”。
環境和成本問題也是必須考慮的因素。“核電幾乎是零污染的。”潘自強介紹,“發展核電的本身并不產生污染物包括溫室氣體,但是其配套生產過程會產生溫室氣體,也只是火電的1/100。”總體算下來,核電每千瓦時電能的成本比火電要低20%以上。一座100萬千瓦的火電站每年要耗費三四百萬噸煤,而相同功率的核電站則只需要鈾燃料三四十噸。而且,在目前主要的替代能源中,核電的成本要遠低于太陽能和風能。

因涉及到地質條件、廢料處理等安全問題,一些核電項目遭受外界質疑。
聯合國氣候大會上的劍拔弩張,讓中國承擔著巨大的碳排放壓力。2009年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我國提出到2020年單位GDP碳排放量下降40-45%的目標。為此,到2020年,我國可再生能源將占能源消耗結構的15%,這其中核電預計占到4%。2010年我國核電裝機容量1080萬千瓦,每年能減少6700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目前我國碳排放量為每年70多億噸,如果核電容量增加到8000萬的級別,那么每年將減少50多億噸二氧化碳,占到了我國每年碳排放量的70%多。
目前主要的反核力量集中在歐洲。早在2002年德國就已經宣布要在2020年關閉核電廠,但是去年默克爾政府又宣布17座核電廠延后12年服役。這其中的反復博弈,能源需求和減排壓力無疑都是根本原因。瑞典早在1980年就以全民公投方式確定30年后實現非核家園的理想,但是在沒有替代能源的情況下,如今只關閉了一家。
安全與否的考量
魚與熊掌不能兼得,但是核電發展與核電安全或許并不會出現零和博弈的場景,相反,最終結果可能就是雙贏。
“接受核電發展是沒問題的,但是審批要更嚴格、安全防范措施要做的更好,我們科學工作者也要加大這方面的研究。”潘自強說。福島核危機帶來的既是對核電發展的一次嚴峻挑戰,也是重新審視和發展核電的一次良好機遇。
日本福島核電站采用的是所謂“二代加”的技術,即二代技術的改進型,在出現故障停堆后,要啟用備用電源帶動冷卻水循環散熱。此次危機發生后,外界對于需要外部能源帶動的這種“二代加”技術提出質疑,認為三代技術更為可靠。目前我國核電機組采用的主要也是二代加技術,但是,采用的卻是進一步改進的“壓水堆”技術,雖然與福島核電站同屬二代加型機組,但是設計上的優勢使其比福島沸水堆相對更安全一些。
實際上,目前全世界在役的441臺核電機組中,絕大部分為二代或者二代加型,符合國際原子能機構對于核電設施的安全要求。在潘自強看來,日本福島核危機的關鍵在于,沒有考慮到海嘯因素。“對核設施的影響主要是9級強震引發的海嘯帶來的。”這個級別的地震和海嘯是超乎設計想象的。因此福島核電站故障并不能說明二代加不行。
在核廢料處理問題上,目前爭議也比較大。核廢料具有極強烈的放射性,其半衰期長達數千年、數萬年甚至幾十萬年。也就是說,在幾十萬年后,這些核廢料還可能傷害人類和環境。所以如何安全、永久地處理核廢料是科學家們一個重大的課題。 3月25日下午,世界環保組織“自然之友”專家Joerg Naumann在參加中國工程院文獻情報中心舉行的“核安全研修”活動時就提出,他們反對核電項目的重要原因,就是核廢料處理上目前技術還不完善。不過在潘自強院士看來,目前深埋處理核廢料的方式,是安全可行的,這種儲存方式能至少保證10萬年內的安全。人類的科學技術不斷發展,對于核廢料的處理能力會不斷增強。而且,從成本角度來講,核電相比其他能源仍然具有很大優勢,這是一個利益權衡的問題。
相比技術上的爭議,提高核電站抗災級別,尤其是沿海地區考慮到海嘯因素,加強核安全審批和檢查,這些可能更為現實。而這些工作也正在展開。國內核電巨頭中核集團與中廣核集團目前已經完成自查,全國范圍內的安全檢查正在展開。我國目前有三級核應急機制,從國家到地方再到企業。浙江省環保廳副廳長、核應急辦公室主任章晨此前檢查秦山核電站時,提到日本福島核事故剛一發生,浙江就立即進入了核應急待命狀態。《浙江省核電廠(基地)核事故場外應急預案》顯示,浙江省軍區、各專業組、海鹽縣、秦山核電站等都有應急計劃。
不過,也有不少未盡之處需要改進,如,核應急管理專業人才缺乏,人力資源素質有待提高,核電站與地震、海洋、氣象等部門的監測預報聯動機制尚未形成等。福島核危機無疑對此敲響了警鐘。
能源結構調整轉型
在能源緊缺的背景下,發展核電成為不得不走的道路,不過以福島核危機為契機,我國乃至全球或許將再次審視能源結構布局。
核電的成本優勢決定了其發展命運,在如今的替代能源中,核電成本遠低于太陽能和風能發電成本。核電如今在許多國家的電力供應中占到了較大比例。目前世界上已有核電機組約441臺,總裝機容量3.7億千瓦,占世界總發電量的16%。30多個核電國家和地區中,核發電量超過20%的國家和地區有16個。法國的核發電量占到其總發電量的77%,歐盟平均占到35%,日本34%,韓國約40%,美國20%。而到2010年,我國發電裝機總容量為9.62億千瓦,其中核電1080萬千瓦,只占到總發電量的不到2%。距世界平均16%的水平差距很大。
而按照“十二五”規劃綱要,到2015年,我國非化石能源要占到能源結構的11.4%,預計到2020年占到15%,其中核電將占到4%。這意味著,未來10年間,我國能源結構轉型中,核電依然是重要的發展目標。
但是,福島核危機后,我國核電發展規劃可能微調,不少分析人士認為,成本更大但是更為安全可靠的可再生能源將得到發展機遇。如太陽能,其發電形式更符合清潔能源的標準,風電發展也有望進一步突破。目前太陽能發電需要突破的難題很多,如降低光伏發電成本,建設配套網絡等。風電發展的電網建設也比較滯后,目前國家正在對電網進行規劃,預計在未來兩三年也會有所突破。
從全球背景來看,核電發展也遭遇到了信任危機。在歐洲,這一危機自“切爾諾貝利”之后就沒有停止過。Joerg Naumann就介紹,目前德國已經暫時關閉1980年以前投入運營的7座核電站,暫停去年通過的“延長核電站運營期限計劃”。但是他也不否認,在核電占到77%的法國,如果停止核電將會是什么樣的景象。而就在去年,默克爾政府還曾因為能源和減排壓力,宣布17座核電廠延后12年服役。
“核電目前仍然是最主要的過度能源。只要確保其安全性,發展核電就是沒問題的。”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中國工程院院士潘自強說。
□ 編輯 尹麗麗 □ 美編 龐 佳
鏈接
沸水堆與壓水堆
沸水堆:字面上來看就是采用沸騰的水來冷卻核燃料的一種反應堆。福島核電站建于20世紀70年代,屬于沸水堆。
壓水堆:字面上看就是采用高壓水來冷卻核燃料的一種反應堆。中國建成和在建共有13臺核電機組,除秦山三期采用CANDU堆技術,山東榮成采用高溫氣冷堆,其余均為壓水堆。
沸水堆與壓水堆不同之處在于沸水堆沒有蒸汽發生器,一回路水通過堆芯加熱變成約285℃的蒸汽并直接引入汽輪機,因此常規島布置有一回路的冷卻劑管道,管道失效可能引起冷卻劑泄漏。壓水堆的一回路和蒸汽系統通過蒸汽發生器分隔開,而且蒸汽發生器安置在安全殼內,只要蒸汽發生器完整,放射性物質不會釋放到環境中,即使蒸汽發生器故障破損,利用安全殼貫穿件關閉,放射性物質也不會釋放到環境中。
沸水堆壓力遠低于壓水堆壓力,因此在系統設備、管道、泵、閥門等的耐高壓方面的要求低于壓水堆。壓水堆由于壓力高,且多了蒸汽發生器、穩壓器等設備,技術性能要求及造價都要高許多,但安全性高于沸水堆。
壓水堆核電廠因其功率密度高、結構緊湊、安全易控、技術成熟、造價和發電成本相對較低等特點,成為目前國際上最廣泛采用的商用核電堆型,占輕水堆核電機組總數的3/4。我國核電站以及潛艇基本都采用了先進的壓水堆核電機組,安全性比福島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