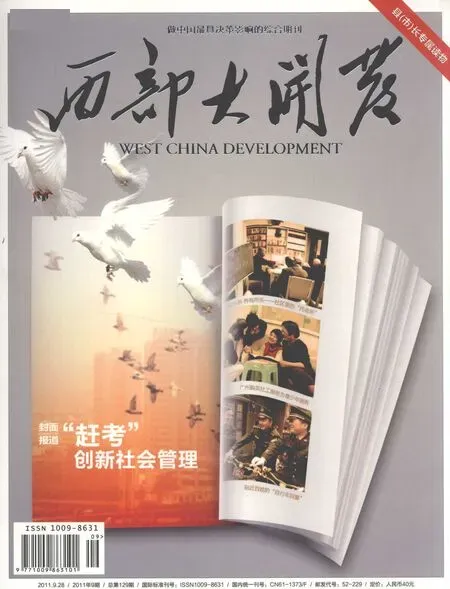地方官員政績追求八宗“最”
中國社會的發(fā)展,一直都銘刻著深厚的行政烙印;地方官員的政績追求,常常左右著一方福祉興衰。誠然,政績的優(yōu)劣沒有唯一的評判標(biāo)準(zhǔn),但由此衍生出來的政績觀卻指引著執(zhí)政者的施政內(nèi)容和效果,也在推動社會發(fā)展的列車輕快或負(fù)重前行。為此,本刊記者梳理列舉了當(dāng)下官員政績觀的8種正負(fù)極表現(xiàn),力求將事實(shí)還原給讀者,把思考留給各位市縣長。
最剛性的政績——招商引資
“招商引資是牽動全局的工作、最硬的政績,其成效如何是檢驗(yàn)我們?nèi)旯ぷ鞯淖钪匾獌?nèi)容……必須將其作為經(jīng)濟(jì)工作的生命線,堅(jiān)持作為最硬的‘一票否決’,從而促進(jìn)各級干部把主要精力放在招商引資和項(xiàng)目建設(shè)上……”這是西部某縣今年的一份政府工作報告。值得注意的是,該報告通篇寫滿了“招商引資”4個字。該縣某廣場上還打著一條橫幅,“建立以招商引資論工作好壞、干部實(shí)績的考核指標(biāo)體系”。
綜觀改革開放30多年來,招商引資在中國經(jīng)濟(jì)高速增長中可謂功不可沒。從中國的國情出發(fā),從發(fā)展的現(xiàn)實(shí)來看,招商引資是繞不開的一環(huán)。這些年來,地方之間的競爭,爭的是招商引資的實(shí)力;官員之間的政績比拼,主要拼的也是招商引資的本事。人們批判的是惡性競爭,反感的是弄虛作假,諷刺的是盲目受騙,質(zhì)疑的是招商成“招傷”。“項(xiàng)目上,干部上;項(xiàng)目下,干部下”。招商之殤,根子上源于對干部考核評價機(jī)制的不科學(xué)、不健全。在實(shí)踐科學(xué)發(fā)展觀、加快政府職能轉(zhuǎn)變的今天,招商引資在政績考核中的“一枝獨(dú)秀”,已經(jīng)越來越不合時宜。
最沖動的政績——大拆大建
1.修一棟樓要花50萬,產(chǎn)生出的GDP就是50萬;2.因?yàn)樵谛薜倪^程中出現(xiàn)質(zhì)量問題,炸掉它則要10萬,再在原址上修同樣一座樓花80萬,產(chǎn)生的GDP是多少?答案是140萬。“不拆不建不發(fā)展,小拆小建小發(fā)展,大拆大建大發(fā)展,快拆快建快發(fā)展”。這幅杭州市火車東站附近掛出的標(biāo)語,被一些地方視為城市發(fā)展的經(jīng)驗(yàn)之談,也說出了許多地方執(zhí)政者的心里話。
武漢市委書記阮成發(fā)因大搞城市建設(shè)被戲謔為“滿城挖”,全市5000多個建設(shè)工地遍地開花。贊同的人認(rèn)為,阮書記“罵名”背后是百姓明天的幸福生活;反對派則認(rèn)為“滿城挖”背后是畸形的政績觀。而關(guān)于“滿城挖”的是非,最終還是要在歷史中得到定論和檢驗(yàn)。大拆大建的橫行,源于在政績工程和GDP崇拜的驅(qū)動下,不少地方官員的政績沖動。他們除了將其看成是發(fā)展經(jīng)濟(jì)最有力的手段外,更視其為樹政績的捷徑。
最扎實(shí)的政績——基礎(chǔ)建設(shè)
前不久,長江流域持續(xù)強(qiáng)降雨,有地方防汛堤決堤,水淹全城。武漢全城交通幾近癱瘓,坐落在珞珈山的武漢大學(xué)居然泡在水中。在咸寧,有些居民劃著皮劃艇去買菜。人們只得自我解嘲為“看海”。
一些城市忙著進(jìn)行的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就未必是真“基礎(chǔ)”了,而多是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城市基礎(chǔ)設(shè)施包括多個方面,但不少官員熱衷顯性的那些高樓、道路、橋梁、地鐵,對埋在地下的供熱、供水、排水、排污這些管線工程卻重視不夠。他們心中,搞城市環(huán)境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是“只見投入,不見產(chǎn)出”的活。但路越修越寬,卻越來越堵;房子越修越多,價格卻越來越高,誰之過?
更嚴(yán)重的是,由于工程質(zhì)量不過關(guān),甚至有未批準(zhǔn)先開工、完工未驗(yàn)收等眾多問題,錢江三橋垮了、動車追尾了、高樓倒塌了……國內(nèi)不少大城市都提出口號要建國際大都市,從隨處可見的起吊機(jī)可見這場基礎(chǔ)設(shè)施的大建設(shè)運(yùn)動正在爭分奪秒,但區(qū)區(qū)一場暴雨襲來,一些城市的現(xiàn)代化面貌就被戳穿了。
最艱難的政績——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
河南林州在飄雪中迎來了由國家發(fā)改委牽頭的三級調(diào)查組,接受調(diào)查的將是那座已被關(guān)停了兩年多卻仍在發(fā)電的優(yōu)創(chuàng)電廠和停熱事件。據(jù)知情人士透露,優(yōu)創(chuàng)電廠關(guān)停后仍在發(fā)電不是秘密,一直在向林州官莊220千伏變電站聯(lián)網(wǎng)供電。這種行為,除了涉嫌套取中央財(cái)政落后產(chǎn)能補(bǔ)貼款,更是地方上對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大戰(zhàn)略的一次挑釁。
經(jīng)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fā)展,中國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但同時一些深層次的問題逐漸暴露,最明顯的莫過于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不合理、科學(xué)技術(shù)沒有得到完全合理的利用。中央政府多次將調(diào)整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和轉(zhuǎn)變發(fā)展方式放到顯著位置,要求不再實(shí)施粗放型的發(fā)展模式,擬轉(zhuǎn)向節(jié)能環(huán)保型、綠色科技型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模式上來。
轉(zhuǎn)型的難度比發(fā)展還大,因?yàn)檫@需要打破利益,重新分配,很可能會讓推動者在短時間內(nèi)不見政績、甚至只見“敗績”的事,這恐怕也是一些地方在此一直畏首畏尾的原因。若說從早期的關(guān)閉“五小”僅僅是試探政府的決心有多大,那么到關(guān)停小電廠、重組煤礦、鋼廠那可就是要揮淚斬馬謖了,誰不心疼?但現(xiàn)實(shí)要求我們做出改變。
最期盼的政績——食品安全
三鹿奶粉、毒火腿、絕育黃瓜、牛肉膏、染色饅頭、膨大西瓜……它們正在傷害著國人,而監(jiān)管它們的人呢?民以食為天,食品安全是老百姓第一關(guān)心的重大問題,也是中國面臨的一個巨大挑戰(zhàn)。一個國家的食品安全水平與其經(jīng)濟(jì)社會發(fā)展程度密切相關(guān)。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食品生產(chǎn)消費(fèi)大國,但“食品安全”已經(jīng)成為社會關(guān)注度頗高的詞匯,原因是近年來頻發(fā)的食品安全事故。
最新被打翻神壇的是山西的醋壇子,“勾兌”、“防腐劑”這樣的字眼挑動了公眾的敏感神經(jīng)。社會上每次談?wù)撌称钒踩鹿蕰r,“監(jiān)管不力”是必然會碰觸到的話題,而問責(zé)疲軟是其重要因素之一。
在很多食品質(zhì)量事件中,工商、質(zhì)監(jiān)、農(nóng)委等部門相互踢皮球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導(dǎo)致問責(zé)最后不了了之。而在具體的地方上,對暴露出來的造假行為,除了直接造成死亡的以外,多數(shù)置若罔聞,漠視其長期存在——用川南某市一名質(zhì)監(jiān)局辦公室主任的話來講,就是“曝光什么抓什么,沒有曝光的繼續(xù)做”。食品安全關(guān)乎一個民族能否健康發(fā)展,這是民眾心里最期盼官員能出的政績。
最優(yōu)質(zhì)的政績——改善民生
民生連著民心,民生是最大的政治,而改善民生則是最大的政績,也涵蓋了民眾需求的方方面面。教育是民生之基,健康是民生之本,分配是民生之源,保障是民生之安。本刊報道過的陜西省神木民生實(shí)驗(yàn),在教育、醫(yī)療、養(yǎng)老等民生領(lǐng)域率先大膽突破,推行了12年免費(fèi)教育、全民免費(fèi)醫(yī)療、城鄉(xiāng)統(tǒng)籌養(yǎng)老保險等“十大民生工程”,這也是當(dāng)?shù)毓賳T們一份優(yōu)質(zhì)的政績。
衛(wèi)生部部長陳竺認(rèn)為照神木模式推廣,“大概1/5的縣都可以做起來”。原民政部官員王振耀也算過一筆賬,全國按照神木的標(biāo)準(zhǔn)實(shí)行免費(fèi)醫(yī)療,4300億元就可以實(shí)現(xiàn)了。反觀經(jīng)濟(jì)并不發(fā)達(dá)的寧夏首創(chuàng)高齡老人津貼,廣西防城港率先落實(shí)孤兒最低養(yǎng)育標(biāo)準(zhǔn),海南昌江黎族自治縣實(shí)行免費(fèi)學(xué)前教育。今年8月,身為國家級貧困縣的湖南省桑植縣進(jìn)行了醫(yī)改,34.2萬該縣農(nóng)民只要交150元,就能在全縣46個鄉(xiāng)鎮(zhèn)衛(wèi)生院享受住院全報銷政策……這些說明,錢不是最大問題,政府的決心比財(cái)力更重要。
最前沿的政績——幸福指數(shù)
我有一個夢想,希望身在農(nóng)村的家鄉(xiāng)被建設(shè)得更美,環(huán)境更好。首先要改造房子,再把道路修建成一條條寬闊的柏油路,兩邊裝上明亮的路燈,還要把醫(yī)院改造一下。然后,我還要改造學(xué)校、菜場、通信……
2011年,“十二五”規(guī)劃開局,“幸福指數(shù)”成為熱詞。部分省區(qū)市將其置于重要位置,并提出要“GDP減速,幸福提速”。經(jīng)濟(jì)社會的發(fā)展歸根結(jié)底體現(xiàn)在國民幸福的提升上,廣州市政府參事室主任張嘉極認(rèn)為,“幸福指數(shù)”應(yīng)該囊括收入、保障、物價、住房、教育、環(huán)境、醫(yī)療、文化等各項(xiàng)內(nèi)容。從這個意義上,有人把“幸福指數(shù)”比喻成轉(zhuǎn)型時期那把擺脫“GDP崇拜”的鑰匙,再恰當(dāng)不過。但幸福本是個龐大復(fù)雜的話題,不同人對幸福的理解是不同的,更遑論量化。
幸福感其實(shí)更多來自對“明天幸福”的憧憬,溫家寶總理與網(wǎng)民交流時有關(guān)“幸福”的表述言猶在耳,讓人們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對未來有信心。強(qiáng)調(diào)民眾幸福,這對政府執(zhí)政提出了更高要求,希望地方政府做一些實(shí)實(shí)在在的事情,特別是關(guān)注弱勢群體、欠發(fā)達(dá)地區(qū)。

最長遠(yuǎn)的政績——環(huán)境保護(hù)
廣西來賓市從2008年開始就對金秀瑤族自治縣不再考核GDP,鼓勵其搞好生態(tài)建設(shè)和環(huán)境保護(hù)。最終交出的成績單卻出人意料的漂亮,該縣的GDP比去年同比增長12.6%,財(cái)政收入同比增長38%,比全廣西的增幅高18個百分點(diǎn),創(chuàng)下歷年增幅之最,同時各類環(huán)保指標(biāo)全面上升。之后,來賓市又將這種考核方式應(yīng)用在了忻城縣,并準(zhǔn)備在合山市繼續(xù)推廣。
優(yōu)美的環(huán)境,一直是大連最靚麗的一張城市名片。但這樣的美麗不是憑空得來的,大連人對環(huán)境一直充滿著抗?fàn)幒瓦M(jìn)取,其積極應(yīng)對PX項(xiàng)目的勇氣和做法尤其值得稱道。當(dāng)?shù)卣诳偨Y(jié)經(jīng)驗(yàn)后,宣布PX項(xiàng)目停產(chǎn),也開始更加成熟。
廈門市政府則是在民意之下更早終結(jié)PX項(xiàng)目的。今年5月,廈門將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納入法制化軌道和干部考核體系,結(jié)果將作為各區(qū)政府年度績效評估指標(biāo)之一。
在去年的全國礦山生態(tài)環(huán)境恢復(fù)治理現(xiàn)場會上,環(huán)境保護(hù)部副部長李干杰感嘆,盡管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做了大量工作,但礦山生態(tài)環(huán)境恢復(fù)治理的速度,仍遠(yuǎn)遠(yuǎn)趕不上資源開發(fā)的生態(tài)破壞速度。環(huán)保部高官這樣的聲音意味深長,部分地方政府“犧牲環(huán)境發(fā)展經(jīng)濟(jì)”的沖動,看似是有著提高地方經(jīng)濟(jì)收入的壓力,但根本前提還是在以GDP為核心考核政府官員政績的指標(biāo)體系。萬源歸宗,這不僅是環(huán)保部門面臨的一項(xiàng)困難,也是本文探討所有問題的命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