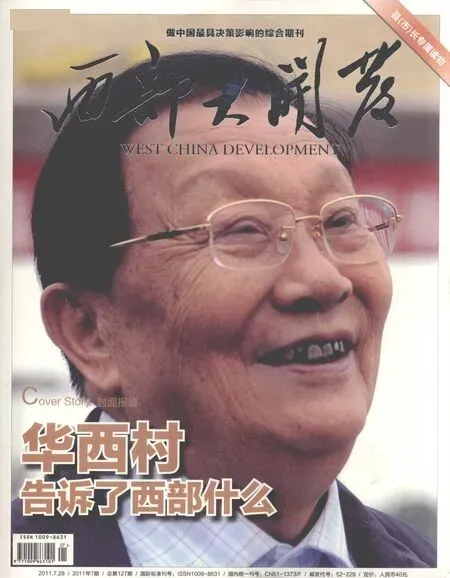一線企業挺進三線城
◎ 文 / 記者 趙代波 周勵

城市化和城鎮化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從城市化到城鎮化的悄然轉變,代表著一種更加務實的姿態來迎接這種變革。到三線去,立足一二線的商人們開始謀劃起了反圍剿。從“城市化”到“城鎮化”的轉變,悄然擴大著三線的想象空間。 一次商業戰略的大轉折,已經近在眼前——
什么叫三線?答案眾說紛紜,不同行業、不同領域的劃分標準各不相同。有兩種比較靠譜的劃分標準,一種是通常把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定義為一線城市,各省會城市和副省級城市為二線城市,其他地級市和縣級市為三線城市。另一種說法,三線城市是指比較發達的中小城市,以及有戰略意義的大中城市和經濟總量較大的小城市。
不論如何,越來越多的一線企業已經開始奔向人們印象中的“三線”。這無疑是中國經濟走向的一次重大逆轉。
小城的天空
“寧愿做小池塘里的大魚,也不愿做大池塘的小魚”。如今有一批人才,他們在中心城市已經找到不錯的工作,而因為生存、發展、實現自身價值等壓力,他們更愿意放棄中心城市光鮮的外表,到中小城市去尋找更廣闊的天空。
這還僅僅是人才反向流動的例子。原本立足于一二線城市的企業,也紛紛扛起了“到三線去”的大旗。“像萬科、金地、招商等房企往年都是一線城市樓盤的銷售情況要好于三線城市,但今年情況卻相反,三線城市的銷售情況好于一線城市。”一位地產業內人士告訴記者,開發商預計“限購令”至少要執行一年以上,因此在兩年左右的時間里,三線城市的銷售情況對大型房企很重要。今年,這些房企也加大了對三線城市的投資和開發力度。
而在一二線城市貼身肉搏后,外資零售企業也意識到了三線城市的重要性。在最近幾年全國開店布局中,沃爾瑪新增的門店絕大多數都在三線城市,占到了2/3以上的比例。
2010年,沃爾瑪、家樂福、歐尚三大世界500強企業在不到1公里的路段內輪番開店。然而,這個路段卻不是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而是位于蘇東南的一個縣級市——昆山。這個城區人口僅僅60萬左右的三線城市,除了上述三家企業外,還聚集著大潤發、樂購和易初蓮花等零售巨頭。
根據我國零售業的WTO進程,直到2004年,三線城市才全面向外資開放。此后短短一年多時間,外資零售巨頭在三線城市遍地開花。光是2005年,沃爾瑪就在三線城市開出了10個門店;而沃爾瑪在建或正在籌建的18個新店項目,其中有14個是在中國的三線城市。布點三線城市的黃金地段,這也許是外資零售商在中國的最后一次擴張機遇。
有地、有錢、有人,開往三線的大軍,已是浩蕩。
保利地產、恒大地產、碧桂園等地產企業,李寧、安踏等服裝企業,蘇寧、國美等零售企業……一大批一線中國企業早于大軍未動,就當起了探路三線的排頭兵。而諸如沃爾瑪、家樂福、肯德基、麥當勞等原本只注重一二線城市的國際巨頭,甚至LV、奔馳、迪士尼等專注小眾市場的超級品牌,也紛紛開始向三線進軍。
有地、有錢、有人,開往三線的大軍,已是浩浩蕩蕩。

據了解,目前中國城市數量已經達到666個,城市人口近3.6億。除去寥寥可數的幾十個一二線城市之外,其余600余座城市均為三線城市。
挺進三線的N個理由
三線城市的消費能力如何?市場空間有多大?企業進入三線有哪些優勢,又需要動用怎樣的資源?事實上,企業征戰三線除了擴張的主觀愿望外,還源于三線市場自身的無窮魅力。面對這塊巨大的蛋糕,哪個企業能不動心?
據了解,目前中國城市數量已經達到666個,城市人口近3.6億。除去寥寥可數的幾十個一二線城市之外,其余600余座城市均為三線城市。
更進一步,為了拉動內需,國家提出以消費為主導的“縣域經濟”。而整個所謂的“縣域經濟”,總人口高達7.5億人,這是一片何其廣袤的市場!
另外一組數據是,京津滬深4個一線城市所占全國GDP的比重,從1994年到2004年整整10年時間,只有小幅增長,僅僅是從10%上升到了14%。我們不妨回想一下,十年間,這4座城市的范圍擴大了多少倍,人口增加了多少,GDP凈值增長了幾何?
一線城市的大發展,并沒有沖淡三線的成長力度。相反,一大批三線城市在迅速崛起,其經濟增長速度大大高于北京、上海、深圳和廣州。有的城市經濟增長速度,甚至可以連續數年達到30%以上。三線對一線追趕的腳步,不但沒有放緩,反而越來越快。
可以看見的是,自1998年以來,我國城鎮化水平每年都保持了1.5%~2.2%的增長。在未來10~15年內,城鎮化進程仍將以無可阻擋的勢頭迅猛發展,成為拉動未來中國經濟的主體力量。而這股力量,正是三線城市有待挖掘的市場空間。
在一二線城市已經進入常規周期之際,跳躍式的發展與市場潛力,才是真正吸引企業的地方。據國家信息中心統計,目前一級市場的汽車銷量增長率為8.1%,而二級、三級、四級市場的銷量增長率分別為27.6%、33.7%和36.0%,遠遠高于一級市場。“有時候,越是小城市里的消費者,追逐豪華車品牌的熱情越高,浙江有不少民營經濟非常發達的三線城市,比如溫州、紹興、臺州、金華、寧波、義烏、瑞安、諸暨、青田等,那里的消費力一點都不比杭州差。相比之下,杭州4S店已經幾乎飽和,相互間的競爭日趨白熱化,而三線城市里競爭還不充分,市場很大。”
一項調查顯示,中國70%以上的中產階層都處于三線城市。中產階層是一個比較模糊的概念,也許一線城市的人均收入高于三線,可三線城市的生活必需成本更低。因此,三線城市額外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反而可能會更高。
政府將4萬億的額外支出大部分投向了中西部地區,迄今為止,這些地區約得到了總投資額的62%。三線城市的發展,正基于這樣的勢頭得以迅走疾奔。
不得不去的理由
在這樣的情況下,一線企業進軍三線的理由就不言自明了:
1.需求拉動。經過多年的發展,三線城市已與十年前的一線城市發展水平相當,積聚了強大的消費能力。
2.競爭壓力。目前一線城市雖然談不上絕對飽和,但市場潛力已經大受限制,而且營銷成本也在急劇攀升。一線品牌們迫切需要尋找新的增長點,三線城市正好是還未開發的處女地,自然成為新的競技場。
3.成本驅動。經過多年苦心經營,一線企業們已經收回了在品牌和商業系統上的投資,具備相對較低成本的優勢,進入三線城市的財務壓力大大減小。
4.系統成熟。經過十多年的摸索,一線企業已經完成了經驗和人才的儲備,其采購、生產、物流和銷售系統已臻完善,具備在三線城市發力的條件。
5.安全需要。一線城市的競爭是背水之戰,而向三線城市擴張,進可攻、退可守。
6.政府支持。一線城市企業扎堆、資本密集,而對三線城市來說卻是如獲至寶,政府必然會大開綠燈和積極扶持。
7. 市場潛力。盡管三線城市平均收入和支出水平仍低于一線城市,但畢竟人口基數大,潛力更大。
8.盈利水平。在三線城市,經營費用、人力支出、運營成本等相對較低,價格競爭也不如一線城市那么激烈,盈利前景樂觀。
事實上,除了這些企業本身的內生因素,還有許多外生因素在帶動企業的走向。其中首當其沖的,便是大城市的溢出效應。中心城市的輻射范圍越來越廣,在這些城市周邊的三線市場,更是經歷了很好的培育期。當一二線城市生存空間近乎飽和,這溢出的部分,恰恰就是周邊城市最好的發展動力。
而這一切,還依賴于交通的大發展。1小時生活圈、24小時生活圈……交通的飛速進步,同時帶來了人們生活圈子的擴大,物流的便利,時間成本的縮小,這為企業進軍三線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
一位重慶某區縣的房企老板告訴記者:“我們要做區縣市場的龍湖。”可這些企業的發展,卻又受到實實在在的限制:他們缺乏資金、缺乏人才、缺乏視野、缺乏經營能力、缺乏真正的一線品牌那樣的大格局。他們所擁有的,僅僅是作為地頭蛇的資源:他們熟悉某個細分市場、具備充沛的本土人脈資源、在當地有一定的號召力。
這樣的企業要想更進一步提升自己,必然會積極尋求與一線企業的結盟,進行優勢互補。而隨著這些三線炮火的加入,無疑又能為一線企業的進軍鋪平道路。
進入三線的壁壘
決定三線勝負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價格。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娃哈哈的非常可樂在大城市的銷售效果并不理想,但在農村卻異常火爆。非常可樂的知名度遠不及“兩樂”,但低價成了其對付國際知名品牌的“殺手锏”。
而一線品牌如果延續過去高端的市場定位,將很難進入三線城市,或者即使進去也難以生存。雙鹿冰箱董事長陳泉苗坦承,一線品牌搶占三線市場明顯的弊端在于,這些品牌要求較大的市場規模,要求高品質的形象。這讓他們在三線市場的營銷中,很難去主動降低這些方面的費用。一線品牌在三線城市步履蹣跚的很大一個原因,就是為品牌所累。
三線市場的特征與自降身段的矛盾,構成了一線企業的兩難。除此之外,三線市場的營銷方式低端化、渠道管控分散化、市場布局零星化等要素,也讓習慣了在一線城市高舉高打的企業們頗為犯難,這就是三線城市的進入壁壘。
誠如一些企業家所言,在三線城市,你開車兩三個小時才可能看到1家屬于自己的店,但在北京,你可能開兩個小時就能看到30家店。店開得越偏,對管理能力的要求就越高,對整個市場的掌控度也應該越強。
三線未來變局猜想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袁鋼明談到,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帶動其他地區發展的一貫思路,使得資源與政策向優勢地區傾斜的趨勢從未改變。
猜想一:經濟格局趨于均衡發展
將資源、人力和資金引向中心城市,引向沿海地區,這種模式產生了兩種隱性補貼:在外部,中國補貼世界;在內部,內陸補貼沿海,三線補貼一二線。于是,我們看到了一二線與三線的不平衡格局,這也是所謂的龐大內需始終無法真正啟動的根本原因。由于地區發展差別巨大,才出現了一線與三線之間的鴻溝與落差。這導致人流與物流統一的大市場框架難以形成,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也難以全面施行和落實。
所幸的是,我們看到政府一直致力于通過再分配來改善三線與一線的區域不平衡。及至一系列的區域經濟規劃出臺,一線城市更加注重經濟轉型和產業結構的調整,而三線則開始發力。所以,三線城市為自己謀取更大的上升空間,一二線城市與三線城市之間的經濟發展趨于均衡,必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中國經濟格局變革的主題。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旗幟鮮明地指出:
“城市化在發展中國家沒有成功先例,城鎮化才是中國的路子。”
猜想二:城市功能專業化
然而,我們在城市化進程中一大弊病就是,城市功能過度集中,一線城市把所有事情都干完了。談到美國,我們都很清楚紐約是金融中心,底特律是汽車制造中心、休斯頓是航天城、華盛頓是政治中心、拉斯維加斯是賭城……而我們的中心城市,比如北京,甚至一些省會城市,都承載了過多的功能——既是工業中心,又是金融、文化、政治,甚至娛樂的中心。
城市化并不是要消滅三線,而是結合不同區域的競爭優勢,使得各個地區的“增長極”成長為大城市,并用快速交通線將大、中、小城市連接起來,形成聯系緊密、分工明確的產業鏈和城市帶。要防止“大城市病”,根本出路是在城市帶的規劃中,明確城市間的分工,同時對大城市實行功能分區。
壞消息是,我們二三線城市的發展過程,大都比照著北京、上海的思路來進行,一味謀求大而全,個個都想做“國際化大都市”。這不但造成了城市功能的重疊,也造成了資源的浪費,抑制了城市優勢的發揮。隨著越來越多三線城市的崛起,這種傾向必將被更加細致的專業化分工所取代。
猜想三:企業變“小”
比起一線城市來,三線城市各方面資源的成本都相對較低,競爭不算太激烈,而對新品牌又有先入為主的慣性思維。一線企業搶占三線資源,對于成本持續走高的經濟格局而言,無疑將占據許多先發優勢。
不過,這并非就是企業進軍三線的唯一思路。最明顯的例子便是,許多不同行業的隱形冠軍,大部分來自于三線城市。這些企業的品牌知名度對于普通大眾而言可能并不高,但他們會在某個細分市場中做到競爭優勢的最大化。
事實上,一線企業更加注重大眾品牌與普適價值的打造,而三線企業在乎的是局部市場的份額;一線企業總是期望做成無所不包的商業帝國,而三線企業在“專一度”上更具有提升空間。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企業格局,我們很難說孰優孰劣。
我們所認為的“小”,并不是企業規模的大小,而是專業性上的更加細化與深入。
猜想四:從城市化轉向城鎮化
早在幾年前,就有西方經濟研究機構預測,中國的城市化要求再建100個千萬人口的大城市。而來自國務院的消息也明確顯示,“十二五”期間,我國城鎮化水平預計超過50%,進入城市社會。不過,近一兩年,我們已經很少提“城市化”,取而代之的是——城鎮化。
這是一種微妙的變化。城鎮化發展的一般規律是,當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以上、城鎮化水平達到30%以上時,城鎮化就進入快速發展時期。而中國目前的情況與之非常吻合。一些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甚至認為,21世紀影響世界最大的有兩件事,一是技術革命,一是中國城鎮化。
然而,從1999年到2007年,中國的城市建成區的面積擴大了7.2%,但吸納的人口只增長了4%。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旗幟鮮明地指出:“城市化在發展中國家沒有成功先例,城鎮化才是中國的路子。”而2010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更是強調,要將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發展作為城鎮化發展重點。
2011年伊始,我們就注意到,一批企業正悄悄地從一線城市轉向三四線市場。衷心地希望他們能在頭破血流的一線激戰市場外,辟出一片清新的藍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