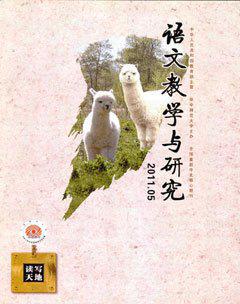談讀書
關于讀書,周氏兄弟有兩個出人意料卻意味深長的比喻。魯迅說:“讀書如賭博。”就像今天愛打麻將的人,天天打、夜夜打、連續地打,有時候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來還繼續打。打麻將的妙處在于一張一張的牌摸起來永遠變化無窮,而讀書也一樣,每一頁都有深厚的趣味。真正會打牌的人打牌不計輸贏,如果為贏錢去打牌在賭徒中被稱為“下品”,賭徒中的高手是為打牌而打牌,專去追求打牌中的趣味。讀書也一樣,要為讀書而讀書,要超功利,就是為了好玩,去追求讀書的無窮趣味。周作人也有一個比方,他說:“讀書就像煙鬼抽煙。”愛抽煙的人手嘴閑空就覺得無聊,而且真正的煙鬼不在于抽,而是在于進入那種煙霧飄渺的境界。讀書也是這樣,就在于那種讀書的境界,它是其樂無窮的。我們的教育,特別是中學教育的最大失敗就在于,把這如此有趣、如此讓人神往的讀書變得如此功利、如此的累,讓學生害怕讀書。我想同學們在中學里都是深有體會的:一見到書就頭痛,其實要是我一見到書就高興、就興奮。中學教育把最有趣味的讀書變成最乏味的讀書,這是我們教育的最大失敗。現在同學們進入大學后就應從中學那種壓抑的、苦不堪言的讀書中解放出來,真正為趣味而讀書,起碼不要再為考試去讀書。這里涉及到一個很有趣的問題,讀書是為什么?讀書就是為了好玩!著名的邏輯學家金岳霖先生當年在西南聯大上課,有一次正講得得意洋洋、滿頭大汗,一位女同學站起來發問(這位女同學也很著名,就是后來巴金先生的夫人蕭珊女士):“金先生,你的邏輯學有什么用呢?你為什么搞邏輯學?”“為了好玩!”金先生答道,在座的同學們都覺得非常新鮮。其實“好玩”兩個字,是道出了一切讀書、一切研究的真諦的。
還有一個問題:讀什么書?讀書的范圍,這對同學們來說可能是更現實的、更具體的問題。魯迅先生在這方面有非常精辟的見解:年輕人大可看本分以外的書,也就是課外的書。學理科的偏看看文學書,學文學的偏看看科學書,看看別人的研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這樣對于別人、別的事情可以有更深切的理解。周作人也自稱是雜家,他主張大家要開拓自己的閱讀范圍,要讀點專業之外的書。
這里我還想談一談理工科學生的知識結構問題。恩格斯曾經高度評價文藝復興時期的那些知識分子說:“這是一個產生巨人的時代。”所謂巨人都是多才多藝、學識淵博的人。那時候的巨人像達·芬奇這些人,不僅是會四五種外語,而且在幾個專業上都同時發出燦爛的光輝。恩格斯說:“他們沒有成為分工的奴隸。”這使他們的性格得到完整、全面的發展。在“五四”時期也是這樣,“五四”開創的新文化的重要傳統就是文理交融。我們中國的第一代、第二代甚至第三代自然科學家,他們都在多個方面有很高的造詣。可以隨便舉幾個例子。著名人類學者裴文中寫的小說,曾受到魯迅的贊揚,還選入了他所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卷。植物學家蔡希陶當年就一邊在云南采集植物標本,一面寫有濃郁的邊地風情的小說。還有一位北大物理系教授丁西林,他的一生,在物理學和戲劇創作兩個領域都取得杰出的成就。老一輩的自然科學家、醫生、工程師,都有很高的中國古典文學的修養和西方古典音樂的修養,他們有的在業余時間寫的詩詞、散文,都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如竺可楨、梁思成、華羅庚等等,就是他們寫的學術論文、報告,文筆都是很優美的。一個真正的大學者,一個健全發展的現代知識分子,他在受到社會和知識分工制約的同時,也在努力突破分工所造成的限制,盡可能地擴展自己的知識結構,以求得自身學識、思維能力與性格的相對全面的發展。
因此,同學們在初進大學,設定自己的目標時,就應該給自己提出雙重任務:既要進入專業,學好專業知識,打下堅實的專業基礎,并且以做本專業的第一流專家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另一方面,又要走出來,看到專業之外的廣大世界,博覽群書,獲得人文精神的熏陶,開拓更加廣大、自由的精神空間,確立更高層面的目標:做一個健全發展的自由的“人”。
※ 錢理群,著名學者,代表作有《心靈的探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