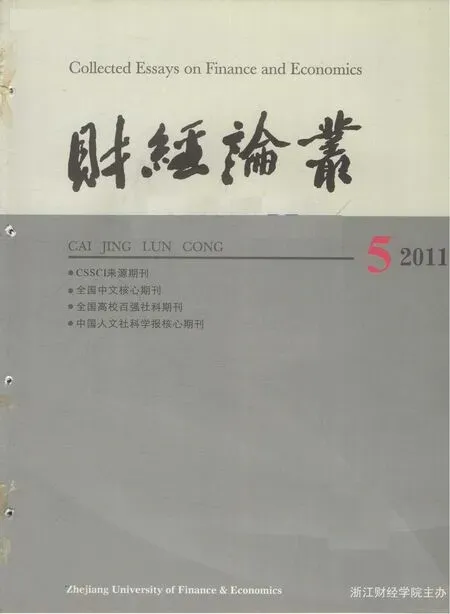金融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效應及省際差異——基于誤差修正模型的面板協整檢驗
盧立香,陳 華
(山東經濟學院財稅金融研究所,山東 濟南 250014)
一、引言和相關文獻回顧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尤其是城鄉收入差距①本文中,除非特別指出,城鄉收入差距均以城市居民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的人均純收入之比來衡量。卻持續擴大,尤其是1998年以來,城鎮居民收入實際增速一直高于農村居民收入實際增速,到2004年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已是世界最高 (李實、岳希明,2004)[1],2009年中國城鄉居民收入比達到3.33:1,如果把城鎮居民的社會保障因素考慮在內,城鄉收入差距將會更大。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從金融發展角度研究城鄉收入差距的文獻也逐漸增多。首先,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率先提出金融發展和收入分配的關系是倒U型的[2]。之后Agihon和Bolton(1997)、Matsuyama(2000)分析了初始財富的分配和信用市場的發展如何通過財富的 “涓流效應”(Trickle-Down Effects)而影響長期財富的分配,預言了金融發展與收入分配之間的倒 U型關系[3][4]。其次,Galor和 Zeira(1993)、Banerjee和Newman(1993)研究表明,在金融市場完善的前提下,金融發展將逐步縮小收入差距。但是,在有信用約束以及對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的投資不可分割的情況下,收入差距并不會必然地趨于收斂[5][6]。另外,Maurer和Haber(2007)則認為,金融服務依然只是針對富人和具有某種政治聯系的企業,從而使收入差距日益擴大[7];Clarke等 (2003)進一步指出,在現代產業部門比重更高,金融發展程度也更高的經濟中,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要高于那些不同時具備 “兩高”
比例的經濟,他們稱之為金融發展的擴展庫茲涅茨效應[8]②根據世界很多國家尤其是一些主要發達國家的經驗,收入分配狀況會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呈現“倒U型”的變化,即所謂的 “庫茲涅茨效應”。。
在實證研究方面,Clarke等(2003)、Beck和Levine(2004)及Honohan(2004),進行了跨國分析,發現金融發展會顯著降低一國收入分配差距,卻未能證實兩者間的 “倒U型”關系[9][10]。近年來,國內學者對金融發展和城鄉收入差距關系從多個角度進行了實證研究,結論并不完全一致。首先,章奇等 (2004)發現金融發展會顯著擴大城鄉收入差距,并且這種負面作用在20世紀90年代尤其明顯[11]。溫濤等 (2005)[12]、楊俊等 (2006)[13]的研究表明,中國金融發展會顯著擴大城鄉收入差距。姚耀軍 (2005)認為金融發展規模的擴大會拉大城鄉收入差距,金融發展效率的提高會縮小城鄉收入差距[14]。其次,劉敏樓 (2006)[15]和萬文全 (2006)[16]認為我國金融發展與城鄉收入差距之間呈倒U型關系。另外,陸銘、陳釗 (2004)研究發現中國金融發展水平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并不顯著[17]。尹希果等 (2007)的研究發現無論是東部還是西部地區,金融發展與城鄉收入差距均表現為非同階單整變量,從而不能認為二者之間存在長期關系[18]。
從上述文獻可以看出,基于中國不同省份的研究較少。由于中國不同省份之間經濟發展的非均衡性顯著,因此必須注重不同地區金融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效應。本文對現有文獻進行擴展和改進,基于面板誤差修正模型 (PVECM)實現面板協整檢驗,進而估計出面板誤差修正模型,由此揭示不同地區的金融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長期影響效應及其短期動態調整效應。
二、指標選取、面板協整模型設定與數據來源
(一)指標選取與面板協整模型設定
1.指標選取
(1)城鄉收入差距指標。本文以表示城鄉收入差距的指標,即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在計算這個比率之前,用各地區的城市消費價格指數和農村消費價格指數分別對收入數據進行了消脹①三大直轄市沒有對城鄉消費價格指數進行區分,其他的省和自治區均用當年的城市消費價格指數和農村消費價格指數分別對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進行了消脹。同時,各個省和自治區的農村消費價格指數自1986年開始才有完整的統計數據,因此,我們研究的時間跨度為1986年-2007年。。
(2)金融發展指標。本文同時選取了金融發展規模指標 (FD)和金融發展效率指標 (FE)。金融發展規模用各省份銀行存貸款之和與其GDP之比衡量,以揭示中國金融發展規模的地區差異;金融發展效率用各省份儲蓄與貸款的比值衡量,以測度金融中介將儲蓄轉化為貸款的效率,這里的儲蓄是指居民儲蓄存款。圖1和圖2分別給出了中國大陸除海南、重慶、西藏以外的其他28個省、市、自治區1986—2007年的金融發展規模和金融發展效率的描述性統計分析。從中可以看出絕大多數省份的金融發展規模和金融發展效率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提高,同時,不同省份的金融發展規模和金融發展效率具有明顯差異,因而不同省份的金融發展水平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是否也具有明顯的差異?為此,本文以不同省份為橫截面個體,將相應變量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組合而形成面板數據,基于此建立面板協整模型,以揭示我國金融發展水平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
2.中國金融發展與城鄉收入差距的面板協整模型設定
本文設定金融發展規模、金融發展效率與城鄉收入差距的面板協整模型為:

如果模型 (1)為面板協整模型,則根據Granger表述定理,面板協整模型 (1)所對應的面板誤差修正模型為 (PVECM)為:

ai為誤差修正速度,反映金融發展與城鄉收入差距的長期關系對城鄉收入差距的短期變化所產生的調節效應。如果ai為負且顯著,則進一步支持模型 (1)為面板協整關系。β1i、β2i反映了城鄉收入差距ID與金融發展規模FD、金融發展效率FE之間的長期關系。φ1i、φ2i反映了城鄉收入差距ID與金融發展規模FD、金融發展效率FE之間的短期調整關系。

圖1 中國各地區1986-2007年的金融發展規模

圖2 中國各地區1986-2007年的金融發展效率
(二)數據說明
本文中1986—2004年的數據未經指明均取自 《新中國五十五年統計資料匯編》,2005—2007年的數據取自 《中國統計年鑒》 (2006—2008),2005—2007年的存貸款數據取自 《中國金融年鑒2008》。本文樣本包括中國大陸除海南、重慶、西藏以外的其他28個省、市、自治區。
三、實證檢驗結果與分析
(一)各變量的面板單位根檢驗
本文選擇三種主要的方法進行檢驗,以增強檢驗結果的可靠性,它們分別是Hadri(2000)的異質面板單位根檢驗、Levin,Lin and Chu檢驗 (2002)和Im,Pesaran and Shin檢驗 (2003)。本文同時應用上述三種檢驗方法對上述變量進行檢驗,結果一并列入表1。由表1可知,在1%顯著水平上,變量ID的Hadri和IPS檢驗結果均顯示變量ID為一階單整I(1)序列,但LLC檢驗結果顯示變量ID為I(0)序列,因此,可以認為變量ID為一階單整I(1)序列;在5%顯著水平上,變量FD的LLC和IPS檢驗結果均顯示變量FD為一階單整I(1)序列,但Hadri檢驗結果顯示變量FD的一階差分值為非平穩過程,因此,可以認為變量FD為一階單整I(1)序列;在1%顯著水平上,變量FE的Hadri和IPS檢驗結果均顯示變量FE為一階單整I(1)序列,但LLC檢驗結果顯示FE的一階差分值為非平穩過程,因此,可以認為變量FE為一階單整I(1)序列。因此,變量ID、FD、FE均為一階單整I(1)序列。

表1 面板數據的單位根檢驗結果
(二)面板協整檢驗與協整向量的估計
1.面板誤差修正模型的面板協整檢驗
基于殘差的面板協整檢驗隱含著一個重要的假設條件:長期誤差修正系數 (變量的水平值)=短期動態調整系數 (變量的差分值),之為 “同要素限制”(Common Factor Restriction)。但是當這一假設無法滿足時,殘差為基礎的面板協整檢驗統計量的檢定力會大幅降低。而以面板誤差修正模型為基礎進行協整檢驗可避免這一限制,而且基于誤差修正模型的面板協整檢驗考慮了截面異質性、截面內的序列相關和截面間的相關性,從而提高統計變量的檢定力。因此,本文采用Westerlund(2007)[19]提供的方法以誤差修正模型為基礎進行面板協整檢驗。Westerlund(2007)的面板協整檢驗共有兩組統計量,每組統計量又各包含兩個統計量。第一組統計量是在假設各個截面的誤差修正速度不同的條件下設定的,其中,Gt統計量是不考慮序列相關的,Ga統計量是考慮序列相關并且采用Newey and West(1994)方法計算標準誤。第二組統計量是在假設各個截面的誤差修正速度相同的條件下設定的,其中,Pt統計量是不考慮序列相關的,Pa統計量是考慮序列相關的。

表2 Westerlund(2007)面板協整檢驗結果
從表2檢驗結果可以看出,Gt統計量在5%水平上拒絕不存在面板協整的原假設,Pt和Pa統計量在10%水平上也拒絕不存在協整關系的原假設。因此,可以認為模型 (1)為面板協整關系,即金融發展規模、金融發展效率與城鄉收入差距之間存在協整關系。
2.面板協整向量的估計結果
Blackburne和Frank(2007)對面板協整向量以及面板誤差修正模型提出了新的估計方法,避免了用Rats編程對面板協整向量與面板誤差修正模型進行完全修正的最小二乘法 (FMOLS)估計的繁瑣過程[20]。該方法提供了面板誤差修正模型的三種可供選擇的估計量:MG估計量 (Mean-Group Estimator)、FE估計量 (Fixed-Effects Estimator)和PMG估計量 (Pooled Mean-Group Estimator)。其中,MG估計量假設各個截面的長期和短期系數均不同,即存在完全的截面異質性;FE估計量假設各個截面具有相同的短期和長期系數,但有不同的截距項;PMG估計量假設各個截面的長期系數都相等,但是誤差修正速度和短期調整系數具有截面異質性。
通過Hausman檢驗對上述三種估計量進行選擇。Hausman檢驗在1%和5%顯著水平下,方程(1)分別拒絕了PMG估計量和FE估計量,故認為采用MG估計量更好,具體估計結果見表3。

表3 Blackburne和Frank(2007)面板協整向量的估計結果
從表3可以看出:(1)只有遼寧、江西和甘肅3省的β1i為負并且均不顯著,其余25個省份的β1i都為正。這一結果表明遼寧、江西和甘肅3省的金融發展規模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起到了抑制作用,而其余25個省份金融發展規模的擴大促進了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而且金融發展規模對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促進作用在一些省份不顯著。其中北京、河北、內蒙古、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四川和青海等10個省份的β1i顯著為正,說明這些地區金融發展規模的擴大對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促進作用顯著。(2)13個省份的β2i為負,而15個省份的β2i為正,說明金融發展效率的提高對城鄉收入差距的長期影響方向不確定。金融發展效率的提高意味著更多的儲蓄轉化為貸款,如果儲蓄更多地轉化為向農村地區的貸款,則金融發展效率提高會抑制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如果儲蓄更多地轉化為向城鎮地區的貸款,則金融發展效率提高會促進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基于此,金融發展效率在不同省份的差異性導致其對城鄉收入差距的長期影響方向顯著不同。(3)不同地區的β1i和β2i有較大差異,說明各地區金融發展規模和金融發展效率對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長期效應不盡相同,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不同地區金融發展水平和城鄉收入差距水平的差異性顯著。
3.面板誤差修正模型 (PVECM)的估計結果與分析
面板協整模型檢驗結果證實了我國各省份金融發展規模和金融發展效率對城鄉收入差距具有不同的長期效應,從Granger協整表述定理可知,這種長期效應對于城鄉收入差距的短期變化應該具有顯著的調節效應,面板誤差修正模型 (2)的估計結果揭示了這種短期調節效應,這種調節效應由估計的ai所刻畫,估計結果見表4。

表4 Blackburne和Frank(2007)面板誤差修正模型 (PVECM)估計結果
ai為負從理論上進一步印證了估計的模型 (1)為面板協整模型。這一結果表明,伴隨著我國金融發展與城鄉收入差距的長期 (協整)關系,對短期的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產生抑制效應。這一結果揭示的經濟意義為:現階段我國應積極提高金融發展水平,促進農村地區的金融發展規模和金融發展效率,以強化對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這種短期抑制效應。分地區來看,北京、河北、內蒙古、黑龍江、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南、廣西、四川和青海等省份的抑制效應具有統計顯著性,這意味著這些地區的農村金融發展對降低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更為重要。其他地區如河南、湖北等,這種抑制作用不顯著,這意味著這類地區短期內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主要依賴于增加農民收入的直接措施,如減輕農民負擔,增加對農業補貼和投入以及提高農民工的待遇等。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我國金融發展規模、金融發展效率和城鄉收入差距之間已形成異質 (各省份不同)的長期 (面板協整)關系,具體來說,除遼寧、江西和甘肅3省以外,其余省份的金融發展規模擴大促進了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同時金融發展規模對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促進作用在不同省份的顯著性不同;金融發展效率的提高對城鄉收入差距的長期影響方向不確定。之后進行的面板誤差修正模型估計顯示,我國金融發展與城鄉收入差距的長期 (協整)關系,對短期的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產生抑制效應。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第一,加大不同地區農村金融改革的力度,促進金融發展規模和金融發展效率在農村地區的提高。在農村信貸投入方面,應大力推行農業保險,積極探索金融工具創新,從而增加對農民的信貸發放;在農村金融市場主體的培育方面,可以嘗試成立更加適合農戶融資的農村金融機構,同時要做好對農村非正規金融的鼓勵和監管,從而推動農村金融市場的正常發育。第二,注重不同地區金融的均衡發展,采取有區別的金融政策,以統籌區域金融和經濟的協調發展,切實有效地發揮金融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改善功能。第三,應注重將促進金融發展水平的長期提高和短期內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政策相結合。長期內促進農村地區的金融發展,逐步改變城鄉金融發展不均衡的狀況;短期內應采取能夠提高農民收入的直接措施,以此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1]李實,岳希明.中國城鄉收入差距調查[J].中國商界,2004,(6):9-11.
[2]Jeremy Greenwood and Boyan Jovanovic,“Financial Development,Growth,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Vol.98,pp.1076-1107.
[3]Philippe Aghion and Patrick Bolton,“A Theory of Trickle-Down Growth and Deveopment”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7,Vol.64.
[4]Kiminori Matsuyama,“Endogenous Inequality”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0,Vol.67,pp.743-759.
[5]Oded Galor and Joseph Zeira,“Income Distribution and Macroeconomic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3,Vol.60,pp.35-52.
[6]Abhijit V.Banerjee and Andrew F.Newman, “Occupational Choice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3,Vol.101,pp.274-298.
[7]Nobel Maurer and Stephen Haber, “Related Lending and Economics Performance:Evidence from Mexico”,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2007,Vol.67,pp.5515-81.
[8]George Clarke,Lixin Colin Xu and Heng-fu Zou, “Finance and Income Inequality:Test of Alternative Theorie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2003 No.2984.
[9]Beck Thorsten,Demirguc-Kunt and Ross Levine,“Finance,Inequality and Poverty:Cross-Country Evidenc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2004,No.3338.
[10]Patrick Honohan, “Financial Development,Growth and Poverty:How Close Are the Link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2004,No.3203.
[11]章奇,劉明興,陶然等.中國金融中介與城鄉收入差距 [J].中國金融學,2004,(1):71-99.
[12]溫濤,冉光和,熊德平.中國金融發展與農民收入增長[J].經濟研究,2005,(9):30-43.
[13]楊俊,李曉羽,張宗益.中國金融發展水平與居民收入分配的實證分析[J].經濟科學,2006,(2):23-33.
[14]姚耀軍.金融發展與城鄉收入差距關系的經驗分析[J].財經研究,2005,(2):49-59.
[15]劉敏樓.金融發展的收入分配效應—基于中國地區截面數據的分析 [J].上海金融,2006,(1):7-11.
[16]萬文全.中國收入差距與金融發展關系的實證分析[J].江淮論壇,2006,(1):30-35.
[17]陸銘,陳釗.城市化、城市傾向的經濟政策與城鄉收入差距[J].經濟研究,2004,(6):50-58.
[18]尹希果,陳剛,程世騎.中國金融發展與城鄉收入差距關系的再檢驗——基于面板單位根和VAR模型的估計 [J].當代經濟科學,2007,(1):15-24.
[19]Joakim Westerlund, “Testing for Error Correction in Panel Data”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December 2007,Vol.69,Issue 6.
[20]Edward F.Blackburne and Mark W.Frank,“Estimation of Nonstationary Heterogeneous Panels” ,The Stata Journal,2007,Number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