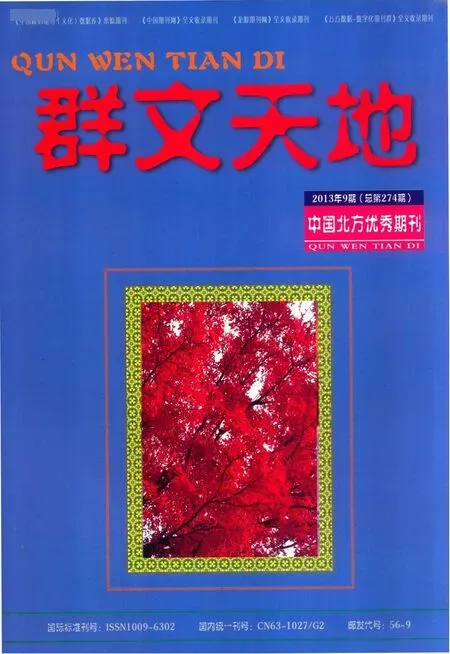明天,青海“花兒”的新優(yōu)勢
■石永
青海“花兒”,這個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在總體上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而與時俱進,不斷改變著自己的面貌,也變換著自己的內(nèi)涵。昨天,她還是羞羞答答,躲在田野林間、深山野洼,沒有觀眾,自吟自唱,不敢見諸于藝術(shù)大堂。雖看似“猶抱琵琶半遮面”,而卻又野氣十足,大放人性的歡歌。今天,她已揭去了遮蓋,換上了時代新裝,走向了城市,步入了“花兒”茶社,展現(xiàn)在有關(guān)的文藝舞臺、電視大賽的熒屏……她的屬性不再只限于情人戀歌,她的展演功能也不只限于自我宣泄和消愁解悶,而成為為社會服務(wù)的文化大餐。她的演唱方式、主題內(nèi)容、演唱環(huán)境、演唱習(xí)俗、詞格以及曲令各個環(huán)節(jié)上都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于是青海“花兒”完成了一次重大的革命,以新的姿態(tài)和新的優(yōu)勢展現(xiàn)在西部乃至全國的文藝舞臺上,立于全國乃至世界的文化藝術(shù)之林。
如今,青海“花兒”正以歌手優(yōu)勢、曲令優(yōu)勢、名人、唱法等諸多優(yōu)勢向著名優(yōu)品牌的大目標前進,前景可觀。
本文從青海“花兒”的昨天、今天所擁有的基本優(yōu)勢及其發(fā)展變化的軌跡,來把握“花兒”發(fā)展的規(guī)律,推察出明天“花兒”的發(fā)展走向和新的優(yōu)勢,探討文化工作者所肩負的歷史使命以及目前所采取的應(yīng)對措施,以推動“花兒”藝術(shù)健康和諧地向前發(fā)展。為構(gòu)建和諧社會,做出“花兒”文化應(yīng)有的貢獻。
昨天,群體參與是青海“花兒”的絕對優(yōu)勢
“花兒”是情人戀歌,演唱者又是勞動者群體,人數(shù)眾多,人人都是歌手,不論是美麗的夏季或是漫漫寒冬,到處都可聽到舒展、高亢、悠長嘹亮的“花兒”的旋律,尤其是翠綠的夏季,麥田寬廣,到處都是民間嗩吶伴和著“花兒”的旋律,男女對歌,此起彼伏,情趣盎然。漫漫長路,江河上下,腳戶哥和筏子客的低吟淺唱或引頸高歌,都傾訴著生活的清苦,對戀手的眷戀。這些職業(yè)行當(dāng)和人群便是創(chuàng)作和演唱“花兒”的佼佼者。他們長期夫妻分居,戀人遠離,生活單調(diào),心情郁悶,天長日久“花兒”便成了他們心中之歌、口中之吟。只要有靈感襲來,情之沖動,環(huán)境允許,“花兒”的詞語便從心底涌動,“花兒”的旋律便從口邊飛出。“花兒”本是心上的話,/不唱(呵)由不得個家”。其情真切感人,甚至獨自一人也唱得如癡如醉。
“花兒”的演唱那只是純屬精神世界的個人行為,不存在服務(wù)、消費等具有一定社會屬性的諸多內(nèi)在理念,更不存在歌手、聽眾,報酬等的社會分工和市場行為的外在因素。
群體參與,形成海洋,是昨天“花兒”的最大優(yōu)勢,它在各個環(huán)節(jié)上的特點可以簡言。
“花兒”的屬性——情人戀歌。不論是歷史“花兒”,生活“花兒”,針貶對弊“花兒”,其主題都離不開愛情。其精品“花兒”的核心內(nèi)涵是“維下“花兒”(呵)寬心哩,/倒把個心牽爛哩。”滾燙的心聲語言發(fā)自肺腑。“一日兒牽,/兩日兒牽,/天每日牽,/把好人憂累成病漢”,強烈的思念戀人之情,不能自已,生動感人。
“花兒”的功能——自我宣泄,消愁解悶,或?qū)ふ覒偃恕?/p>
“花兒”的演唱環(huán)境——田間地頭、山坡林邊、大河筏渡、漫漫長路、民間自發(fā)的“花兒”會,寬廣深遠的大自然的野外環(huán)境,不入村、不入室。
“花兒”的演唱者——田間的勞動婦女、腳戶哥、筏子客、擋羊娃,其他勞動現(xiàn)場的小伙子等組成主體隊伍。甚至小學(xué)生也能來上一句“尕馬兒拉回來!”人人會唱“花兒”。
“花兒”的演唱形式——獨唱、二人齊唱、對唱,無伴奏或嗩吶伴奏。
“花兒”的唱法——民間特有的自然發(fā)聲唱法。
“花兒”的詞格——四句、六句,很少多句。
“花兒”的曲令——地域界限明顯、較少地域之間的交流。
“花兒”的避忌習(xí)俗——家族中和親戚圈中的異性,包括長輩、同輩和晚輩。
今天,歌手是“花兒”的主力軍
隨著社會的進步,時代的發(fā)展,產(chǎn)生情人戀歌的社會文化背景不復(fù)存在,產(chǎn)生精品“花兒”和優(yōu)秀唱把式的職業(yè)行當(dāng)和生活環(huán)境早已消失,田間地頭少有“花兒”飛來,山坡林間清靜寂寥,早已沒了當(dāng)年的火熱場面。現(xiàn)代人的生活和理念距離昨天“花兒”群體演唱的年代又相去甚遠,除了“花兒”歌手和中老年人群和“花兒”有一定的眷戀情感外,大多數(shù)年輕人已不理解或不演唱“花兒”,于是“花兒”的群體優(yōu)勢也就無可奈何地逝去了。“花兒”漸漸地離開了當(dāng)年的演唱者群體。
那么是否能說如今已沒有了“花兒”的故鄉(xiāng),否!故鄉(xiāng)依然存在,而且如火如荼,人山人海。一個方面軍消失了,另一個方面軍卻又異軍突起,那便是眾多的優(yōu)秀年輕“花兒”歌手。
農(nóng)村自發(fā)的民間傳統(tǒng)“花兒”會,城鎮(zhèn)政府行為介入的大型“花兒”演唱會,普遍開花,人山人海;常年營業(yè)的“花兒”茶社歌聲嘹亮,聽眾消費猶酣。歌手們來往于花會之中,穿梭于茶社之間,疲于奔命,搶時間趕場,完成演出任務(wù)。歌手和聽眾,服務(wù)和消費,分工明確,報酬和招待等市場行為融入其中。不論是炎熱的夏季還是嚴寒的冬季,故鄉(xiāng)依然延續(xù)著那洶涌的海洋態(tài)勢。
今天,“花兒”向著革命的縱深繼續(xù)發(fā)展,呈現(xiàn)出現(xiàn)代意義上的“花兒”的時代色彩,形成新的歌手優(yōu)勢,在其他各環(huán)節(jié)上,明顯顯示出與昨天的差異。
“花兒”的屬性——仍然是情歌,但情人戀歌屬性逐漸減弱,向著歌唱時代主旋律和歌唱生活、贊頌社會建設(shè)和開發(fā)浪潮及模范人物的方面轉(zhuǎn)變。
“花兒”的功能——自我宣泄和消愁解悶已不突出,自娛和娛人功能成為主流。
演唱環(huán)境——茶社、“花兒”會、有關(guān)的文藝舞臺、各類“花兒”演唱會、電視熒屏。
演唱者隊伍——“花兒”歌手,逐步向著職業(yè)化、專業(yè)化過渡。民間“花兒”愛好者。
演唱形式——獨唱、齊唱、對唱,小民樂隊伴奏,或電子琴伴唱。
“花兒”的唱法——多數(shù)歌手未經(jīng)專業(yè)訓(xùn)練,自覺不自覺地受現(xiàn)代唱法或民族唱法的影響,形成自己的風(fēng)格,較少見到“原生態(tài)”唱法。
唱詞內(nèi)容——傳統(tǒng)的愛情的精品“花兒”和優(yōu)秀的歷史“花兒”已不多見,更多的是一般流行的愛情“花兒”,還有逗趣、取樂、嘲笑等俗氣“花兒”。
曲令——地域和民族曲令已沖破地域和民族的界限,廣泛交流,成為“花兒”音樂文化中的組成部分。
“花兒”的避忌習(xí)俗——逐步淡化,“花兒”入村、入家。
明天,職業(yè)歌手、專業(yè)演員大放光彩
“花兒”領(lǐng)域的革命向縱深發(fā)展,其結(jié)果必然是歌手以兩支隊伍形成潮流,競相發(fā)展,自成體系,各展風(fēng)采,形成“花兒”更加燦爛的明天。
一方面,民間傳統(tǒng)“花兒”會如火如荼,盛行不衰,“花兒”愛好者云集、唱法新穎,形成季節(jié)性的“花兒”演唱的高潮。另一方面,政府文化部門組織的各類“花兒”會、演唱會,類似于民族文化旅游節(jié)的大型歌手邀請賽、擂臺賽,接連不斷。為展示經(jīng)濟發(fā)展的貿(mào)易洽談會、國際性的各類體育賽事活動的舉行都會伴以各類形式的“花兒”演唱,來展示青海、展示青海“花兒”文化的全貌。因之,“花兒”歌手的職業(yè)化、專業(yè)化、演唱活動的高質(zhì)量,會是明天青海“花兒”的新的優(yōu)勢。伴隨著新的優(yōu)勢的其他各個環(huán)節(jié)上又有新的變化和特點。
“花兒”的屬性——情歌的屬性仍然保留,但其內(nèi)涵的實質(zhì)已明顯進一步淡化“,花兒”既唱時代主流,又贊美各種活動的主題,唱青海風(fēng)物、唱社會發(fā)展、唱新人新事。又有“花兒”唱外事活動,用網(wǎng)絡(luò)語言……“花兒”逐步成為融入時代特色的情歌。
“花兒”的功能——已成為自娛、娛人、贊頌社會主義建設(shè)成就,歌唱新時代的贊歌,為社會服務(wù)。
“花兒”的演唱環(huán)境——1、民間傳統(tǒng)“花兒”會設(shè)在景點,保持美麗的自然風(fēng)光。2、各類“花兒”會專設(shè)大型舞臺,音響、伴奏齊全。
“花兒”的演唱者——1、民間歌手和愛好者,保持民間唱法。2、職業(yè)“花兒”歌手和專業(yè)演員,組成另一支演唱者隊伍。
“花兒”的演唱形式和唱法——獨唱、齊唱、對唱,更為時興的是組合唱法,少有的“原生態(tài)”唱法。
“花兒”的詞格——四句、六句、多句,詞格多樣化。
“花兒”曲令——除傳統(tǒng)曲令外,改編或新編曲令開始出現(xiàn)在“花兒”會上,形成新的“花兒”文化。
“花兒”的避諱習(xí)俗——舊有的避諱習(xí)俗完全淡化,只在邊遠山區(qū)有點保留。
“花兒”的發(fā)展趨勢,展示出燦爛的明天,讓人鼓舞,使人興奮。同時也為我們文化工作者提出了迫在眉睫的任務(wù):如歌手的培養(yǎng)“,原生態(tài)”唱法的保護,組合唱法的聲部編寫和排練“,花兒”歌手的評等定級,管理機制的建立和完善,光碟的出版發(fā)行,“花兒”刊物的創(chuàng)編……這些具體的工作必須要有一個相應(yīng)的機構(gòu)和一批有事業(yè)心的人來承擔(dān),籌措經(jīng)費、開展工作。這樣,我們的工作才會適應(yīng)“花兒”總體發(fā)展形勢的需要。

滕曉天先生的《青海花兒唱青海》,作為《青海花兒話青海》的姊妹篇,一經(jīng)推出,在青海“花壇”再次引發(fā)一場“話青海、唱青海”的熱潮。在民眾審美情趣普遍提高、藝術(shù)眼光日益挑剔的今天,這部“唱青海”何以能再次讓“花兒”界引人注目,依我看,這個話題值得琢磨。滕曉天先生作為一名久經(jīng)“花”海的護“花”使者,一名熟諳“花兒”格律與表現(xiàn)意境的學(xué)者,之所以信心十足地推出這部“花兒”集,除了與時俱進“、老瓶裝新酒”賦予古老韻律以時代氣息之外,他的治學(xué)精神與人格魅力,以及近二十年以來日積月累的社會威望也與此有著不可忽視的關(guān)聯(lián)。進而言之,我們有必要把眼光放在一個比較寬泛的時空內(nèi),去研究這種看似偶然實則必然的文化現(xiàn)象。
二十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經(jīng)濟大潮的沖擊、現(xiàn)代傳播媒體的快速普及,以及國內(nèi)民間文藝研究熱點的轉(zhuǎn)移,“花兒”的研究逐漸進入了近十年的消歇期,而“花兒”資源的開發(fā)與利用方面呈現(xiàn)出的喜憂參半的景象,一時成為廣大民眾關(guān)注的焦點。一方面,“花兒”音像制品大量上市,魚龍混雜,充斥城鄉(xiāng),甚至出現(xiàn)某些商家急功近利,奉迎低俗需求而“惡搞”“花兒”的現(xiàn)象。同時,大量“花兒”歌手紛紛進入城市、足茶園等娛樂場所,在簡陋的條件下實踐著“花兒”的創(chuàng)收功用。這種對“花兒”資源的多重性開發(fā),以及“花兒”群體進入城市,尋求發(fā)展的自發(fā)行為,作為一種文化現(xiàn)象有利有弊,不能一概而論,而缺乏的則是相關(guān)部門正確的引導(dǎo)和扶持。
難能可貴的是,這一時期,仍然有部分學(xué)者執(zhí)著地堅守在“花兒”研究的陣地上,一往情深地耕耘著“花兒”園地。不過,由于各方面的原因,這一時期對“花兒”的理論研究也顯得良莠不齊。一方面“,花兒”理論研究,缺乏新的視角和理論支撐,加上此前的學(xué)者們嘆為觀止的學(xué)術(shù)成就,使得這一時期的“花兒”研究,難以再有新的突破,學(xué)術(shù)界出現(xiàn)相互承襲、舊調(diào)重彈,對類似于“花兒”起源及稱謂等陳舊話題糾纏不清,進行無謂紛爭的現(xiàn)象。(其實,許多涉及“花兒”的常規(guī)性的問題,在此前不久趙宗福先生的《花兒通論》問世后,不應(yīng)再開口水戰(zhàn)。)另一方面,部分學(xué)者另辟蹊徑,挖掘整理“花兒”所包含的深層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