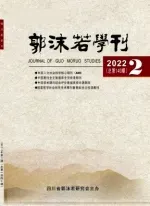是自敘性“小說”,還是自敘性“散文”?——關于郭沫若《雞之歸去來》體裁的辨析
李存光
(中國社科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0021)
問題的提出:小說還是散文?
1933年9月26日,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在寓所寫了一篇題為《雞》的作品,未在報刊發表,直接編入1934年1月由上海樂華圖書公司出版的《沫若自選集》,后收入北新書局1937年12月出版的散文集《歸去來》,并改題為《雞之歸去來》。
《雞之歸去來》直接表露了郭沫若對受欺壓的在日朝鮮人的深切關注和深厚同情,無疑是中國現代文學中涉及朝鮮人的一篇重要作品。這篇作品寫的是郭沫若親身的經歷和獨有的感觸,內容的自敘性毋庸置疑,但究竟是自敘性“小說”(“身邊小說”)還是自敘性“散文”?這個問題看似不大,卻不容小視,很值得研究。
最早把這篇作品作為“身邊小說”看待的是日本的藤田梨那教授。她在《郭沫若〈雞之歸去來〉中的變形抵抗與對韓意識》①和據此文修改調整而成的《郭沫若流亡日本時期的抵抗文學》②中,將《雞之歸去來》歸入“身邊小說”,她解釋說,“所謂身邊小說是指以作者自身為主人公,寫他自已的經歷和感觸的一種自敘性的小說。”[1](P37)藤田教授的論文發表后,韓國學者沿用這一看法,將《雞之歸去來》納入“韓人題材小說”的重要篇章加以論述,比如樸宰雨的論文《三四十年代中國韓人題材小說里的對韓認識與敘事特點:20世紀中國作家的對韓認識與敘事變遷研究》。③
藤田教授從郭沫若宏富的著作中發掘出《雞之歸去來》這篇與朝鮮人密切相關的重要作品,并撰文詳加論述,功不可沒。她爬梳諸多史料,對作品產生的歷史背景、思想淵源、現實依據和作品思想的深廣社會性,逐一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細致分析,材料豐富,說理綿密,令人欽佩。但她把這篇作品作為“小說”解讀,竊以為多有不妥,值得商榷。
郭沫若的處理和中國學者的共識
辨析《雞之歸去來》體裁,首先需要看看作者郭沫若是怎樣處理這篇作品的。
郭沫若在首刊這篇作品的《沫若自選集》序文第二段說:“這兒所選擇的一些是比較客觀化了的幾篇戲劇和小說,為顧求全體的統一上凡是抒情的小品文和詩,以及純自傳性質的一些作品都沒有加入。……我目前很抱歉,沒有適當的環境來寫我所想寫的東西,而我所已經寫出的東西也沒有地方可以發表。在閘門緊鎖著的期間,溪流是停頓著的。”[2](P1-2)
藤田教授根據《序》,對《雞之歸去來》的體裁歸屬,得出了結論:“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那些‘比較客觀化’的作品中加上了《雞之歸去來》。從他的序文看,我們對《雞之歸去來》可以粗略理解為‘比較客觀化’的,不是‘抒情的’,也不是‘純自傳性的’作品。”[3](P37)
郭沫若為什么要將《雞之歸去來》編入自選集并冠于卷首?《雞之歸去來》是不是同集中其他作品一樣屬于“比較客觀化”的、非“抒情”的小說或戲劇作品?
為了搞清楚這些問題,先簡介一下上海樂華圖書公司1934年1月版《沫若自選集》。自選集是應樂華圖書公司之約編輯的,收文12篇,共428頁,卷首是《序》(1933年8月26日作),12篇作品依次為:《雞》(1933年 9月 26日作)、《湘累》(1920作,劇本)、《廣寒宮》(1922作,劇本)、《鵷雛》(1923作,小說)、《函谷關》(1923 作,劇本)、《王昭君》(1923作,劇本)、《無抵抗主義者》(1923作,對話)、《歧路》(1924作,小說)、《行路難》(1924作,小說)、《湖心亭》(1924作,小說)、《聶讔》(1925作,劇本)、《馬氏進文廟》(1925作,小說)。④
這個目錄可以看出:一、《序》寫于1933年8月26日,《雞》寫于1933年9月26日,《序》比《雞》早寫整整一個月;二、除首篇《雞》寫于1933年外,其他作品都是1922-1925年寫的;三、除首篇《雞》外,收文的順序完全是按照寫作年代的先后排列,不區分體裁。
以上這三點,能夠說明一些什么呢?首先,我們發現《序》作于8月26日而《雞》作于9月26日,這兩個日期非常重要,它告訴我們,郭沫若是在選好作品、編好集子并寫成《序》以后,才補入新近寫成的《雞》。因此可以說,《序》中所作的說明只針對11篇作品,與后收入的《雞》無關。《雞》是獨立于其他11篇作品的另一單元。明白這一點,方能解釋為什么在《自選集》中,《雞》在寫作時間、排列順序、作品體裁諸多方面都與集子不協調的原因。
那么,郭沫若為什么要把《雞》放進這個集子并冠之于卷首?當時,郭沫若在國內受通緝,在日本遭監視,“所已經寫出的東西也沒有地方可以發表”。因此,借出版舊作選集的機會,把剛剛寫成的這篇指向明確、愛憎鮮明的新作“塞”進去,使之得以發表;將它置之卷首,是因為這篇作品與按既定意圖編好的選集不協調,只能放在卷末或卷首,將之置于卷首,是無言的抗爭:我仍在寫作,我仍要呼喊。這正如藤田教授的詮釋“就是要向讀者表示被封鎖著的溪流仍未失去它強勁的生命力。”[3](P38)
把《雞》硬加到《自選集》中,是一個無奈的選擇。郭沫若回國后,生存環境大變,因此,隨即將它正式編入散文集《歸去來》(北新書局,1937 年12 月)。后又收入小說、散文、雜論集《抱箭集》(海燕書店,1948年1月)的第五輯即散文集《歸去來》(含《雞之歸去來》《浪花十日》《東平的眉目》《癰》《太山撲》《達夫的來訪》《斷線風箏》七篇散文)。
《沫若文集》是經過郭沫若親自校閱修訂的文集,其第八卷的總目題為“革命春秋(沫若自傳第三卷)”,以下包含的細目為《北伐途次》《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海濤集》《歸去來》。[4]這些作品都是自敘性散文。
再看看被稱為“收集編目最豐富、注釋最準確的郭沫若著作總集”《郭沫若全集》。其中的“文學編”是在《沫若文集》的基礎上編成的,1982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開始陸續出版,共20卷。前5卷均為詩歌,6-8卷是戲劇,9、10兩卷收小說與散文,11-14卷為自傳,15-17卷是文藝論著,18-20卷收雜文。編者的“第十卷說明”稱:“本卷收入作者一九二三年至一九四七年所作小說十八篇,散文三十篇。……‘其他’包括散文八篇。……《雞之歸去來》(原題(《雞》),曾收入《沫若自選集》。”[5]
不難看出,郭沫若一直把這篇作品作為散文(自傳散文、自敘性散文)處理的,《沫若文集》和《郭沫若全集》正是遵循作者的處理精心編排的。
《雞之歸去來》作為散文(自傳散文、自敘性散文)的體裁歸屬,中國研究者眾所認同,從無異議。這里舉出部分相關研究專書和作品選集便足以說明。
一、王昭訓等編《郭沫若研究資料》。書中錄入的上海圖書館編“郭沫若著譯系年”在《雞》后標明“散文“;上海圖書館編“郭沫若著譯分類書目”將《歸去來》列為“自傳 日記 書信”類,顯然也是作為廣義的“散文”處理的。[6](P1069-1078)
二、王繼權、童煒鋼編《郭沫若年譜》。1933年9月條下“26日 作散文《雞》。通過白母雞失而復歸的故事,表現了對受壓迫的旅日朝鮮工人的同情,并預示著人民必將起而反抗。收《沫若自選集》。現收《沫若文集》第8卷,改題為《雞之歸去來》。”[7]
三、龔濟民、方仁念編《郭沫若年譜》增訂本。一九三三年 九月條下“二十六日 作散文《雞》。通過家中養的一只雞‘去而復返’的故事,表現了對流落在日本的朝鮮人的同情。收《文集》卷八《歸去來》時,改題為《雞之歸去來》,現收《全集》文學編十三卷。”[8](P281)
四、王錦厚主編《郭沫若作品辭典》。“散文記敘了作者家養白雞‘去而復還’的事件,……散文采取欲揚故抑,由此及彼的手法,結構清晰,感情真摯,敘議結合,既是作家一段個人生活真實記錄,又是一幅歷史發展照相。”[9](P55)
五、李晶標主編《簡明郭沫若詞典》。書中將《雞之歸去來》列入二、創作(四)散文,在介紹了作品思想內容后說:“作品用了小說筆法,筆觸細膩,重于人物心理刻畫。”[10](P80)
六、多種郭沫若散文選集選收《雞之歸去來》。如王錦厚編《郭沫若散文選集》(現代散文叢書·百花散文書系,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 年,2004 年);李曉虹選編《名家名作精選·郭沫若散文》(學生閱讀經典,內蒙文化出版社,2006 年,2009 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編《郭沫若散文》(插圖珍藏版,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 年);劉屏編《路畔的薔薇》(大家散文文庫,江蘇文藝出版社,2009 年)等。
七、將《雞之歸去來》列為“散文”收入的綜合性選集。如四卷本《郭沫若選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 年);漓江出版社編《郭沫若作品精編》(漓江出版社,2004 年)。
以上資料集、年譜、詞典和選集作為有關郭沫若的專書,編者都是郭沫若研究專家或對現代文學史料素有研究的學者。他們的共識足以代表中國研究者的看法。
談到這里,順便澄清三個細節:
第一,《雞之歸去來》在收入《沫若文集》時,第四部分的文字有幾處小改動。第四部分共五段,其中第三段中的“草葉”改為“草藥”,“事情也就穿破了”改為“事情也就穿了”;第四段中共有四處“風說”,除第二處外,其他都改為“流言”。鑒于引者大都依據《沫若文集》或《郭沫若全集》的文本,故作說明。
第二,以上所舉兩種《郭沫若年譜》都說《雞》“收入《沫若文集》第8卷時,改題為《雞之歸去來》。”這是錯誤的。如上所述,《雞》在收入北新書局1937年12月出版的《歸去來》時,作者就將題目改作了《雞之歸去來》。海燕書店1948年1月出版的《抱箭集》在收入這篇作品時,沿用這個題目,后來的《沫若文集》《郭沫若全集》均據此。
第三,龔濟民、方仁念編《郭沫若年譜》(上,增訂本)在介紹《郭沫若自選集》的收文情況時很不確切。年譜“1934年1月”條說:“同月《郭沫若自選集》由樂華圖書公司出版。《選集》收戲劇四部、小說六篇、論文二篇,均系1920年至1925年間的作品。”[8](P285)這段介紹三處有誤:第一,該集中沒有論文;第二,《自選集》收文的實際情況是,收作品12篇(部),其中,劇本5部,小說5篇,散文1篇;⑤第三,除《雞》作于1933年外,其他11篇均系1920年至1925年間的作品。
作品的特色和辨析體裁的意義
辨證《雞之歸去來》的體裁是不是小題大做呢?非也!這個問題雖小,但關系甚大。如果把這篇作品作為小說,會衍生出種種不小的問題。比如,《郭沫若全集》文學編重版時相關卷就需要調整篇目或重寫編輯說明,現有的郭沫若年譜、詞典需要修改詞條,諸多版本的郭沫若散文選集要抽去這篇作品,等等。當然,這還不是主要的問題。
主要的問題更在于,這將妨礙對作品整體的藝術詮釋,影響對作品內容和細節真實性的判斷,最終降低這篇作品在郭沫若創作中和現代文學有關朝鮮人作品中的位置。
既是小說,就要用“小說”視角打量。小說與散文不是“老死不相往來”,表現手法也有交錯和融合,但是,作為文學體裁的兩大門類,總是有區別的,最重要的區別有兩點,一是小說允許而且應該有虛構,而散文特別是紀實性散文在環境、人物、事件上不能夠虛構;第二,小說主要通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節自身的發展體現作者的傾向和思想,而散文既可敘事,寫人,繪景,也可抒情,議論,可夾敘夾議,可借題發揮,可由此及彼。當然,現代小說的觀念、模式有很多變化,但至少對這篇寫于上世紀30年代的作品應作如是觀。
《雞之歸去來》中的環境、人物、主要情節乃至細節,都沒有虛構,都是實際存在的。全文不足七千字,分為四節。作品中正面出現的人物有“我”、“我的女人”安娜、丈夫在東京某會社做事的S夫人、H木匠的老板娘四個人,以及“我”與安娜的五個兒女中的兒子博、四女淑子、半歲的洪兒三人,村中的朝鮮人只在女人們的談話中提到,一個也沒有出現。第一節寫我家居住的環境和房屋的情況,白母雞丟失;第二節寫白母雞復歸,引起我和妻子安娜的揣測:是誰偷走了雞?為什么又送回來?第三節寫安娜找來H木匠的老板娘辨認歸來的雞,我聽見三個女人猜測偷論雞人時幾次出現“朝鮮人”三個字,由此引發對在日本的朝鮮人牛馬般處境的長篇感嘆和議論,我斷定雞的“去”和“返”是朝鮮人所為,雞的“復返”,是因為偷雞的朝鮮人知道了我家和他們是“一樣時常受日本警察凌辱的人”,義理得了勝利;第四節寫談話的女客走后安娜又告訴我一件朝鮮人“吃人”的流言,我以為這是無稽之談,深懷對“在剝奪者的手下當奴隸”的朝鮮人同情和理解,揭示構成這類流言的主要原因。作品第三節用一千余字篇幅借題發揮,敘述在日朝鮮勞工境遇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傾述作者對他們的關注和同情,并為他們鳴不平。從小說的角度看,對雞“失而復歸”情節的敘寫和幾個人物的描畫,顯然體現不出長篇幅議論中那樣廣泛深刻的思想。在作品中,大篇幅議論,并非勢所必然地來自生動細致的具體描畫,不是通過人物和情節得到表現,而是游離于人物和情節之外硬加上去的“思想”。
難解的是,這些議論恰恰是作品的重心所在,關鍵所在,要害所在,意義所在。去掉這些議論,《雞之歸去來》只是一篇妙趣橫生的記敘身邊瑣事的小文;把議論抽出來,則可以寫成一篇有獨立存在價值的銳利雜感。一方面要肯定作品中議論的重要意義,一方面又無法解釋議論與作品人物、情節的內在聯系,藤田教授也深感這一兩難境地,她說:“用了很大篇幅敘述了朝鮮勞工的工作和生活情況,內容很明顯已脫離了身邊小說的范疇,而且郭沫若的著眼點毋寧是在朝鮮勞工問題上的。”(p38)“雖然采用了身邊小說的形式,但實際內容卻已超過身邊小說的范圍,對在日朝鮮勞工的描寫和問題的揭示已顯示出廣泛和深刻的社會性。我們或許可以說,郭沫若的描寫主題其實并不在雞的失蹤,而是在朝鮮的勞工的問題上。”(p43)小說的人物和故事成了表達某種思想的道具,很大篇幅的題外發揮游離于人物和故事,從藝術上說,這難道不是一篇思想大大超越形象的小說嗎?
換一個角度,從“散文”的視角看,情況就大不同了。困惑忽然開朗,疑竇迎刃而解,上述缺陷成為了優長。作者講述了一個有趣的故事:家養的一只白母雞不明不白地丟失,又莫名其妙地回來。面對這件小而又小的事件,“我”有所感悟,生發聯想,乃至禁不住大發議論,直抒胸中塊壘,是自然而然的。因小見大,由此及彼,借題發揮,不正是散文常用的手法嗎?圍繞雞的“失”和“得”,懸疑由此而生,感嘆和議論因此而起。作者的思想通過議論直截了當地得以表露,作品深廣的社會意義由這些議論而得以確立。如此看來,作品中的兩處議論,不僅不是贅疣,恰恰是整篇作品的精彩之筆,精妙之處。作者采取欲揚故抑,由此及彼的手法,因事抒懷,敘議結合,議由事生,不僅使丟雞事件的原委“柳暗花明”,“朝鮮的勞工的問題”的題旨得以充分表達,更體現出作者汪洋恣肆、無拘無束的思想力和筆力,這不正是郭沫若散文一貫的風格和特色嗎?
作為散文,《雞之歸去來》因其敘寫生動、聯想精妙、內蘊深廣、特色鮮明而獲得諸多選家青睞;而作為小說,恐怕任何一本《郭沫若小說選》都不會選這篇議論勝于描寫、思想大于形象的作品。可見,把《雞之歸去來》納入“小說”行列,反而會減低作品的自身價值,進而降低它在郭沫若自敘作品中的地位和現代文學有關朝鮮人作品中的地位。
最后要說的是,藤田教授在她的論文中認為,《歸去來》這本集子里的《浪花十日》《東平的眉目》《達夫的來訪》《癰》《太山撲》等“從作品性質上看,它們都應算作身邊小說。”(p37)既然題目已明示是記丘東平、郁達夫等友人,亦可歸入“身邊小說”,那么,以此類推,能不能把《少年時代》《學生時代》《革命春秋》《洪波曲》中的若干篇章也歸入“身邊小說”呢?眾所周知,郭沫若的自傳文學卷帙浩瀚,體式博雜,囊括小說、雜文、散文、戲劇各類文體,研究者應仔細區分,不能隨意擴大其中“小說”的范圍,包括《雞之歸去來》在內的《歸去來》中的作品,顯然有別于《未央》《殘春》《陽春別》《落葉》《漂流三部曲》等“身邊小說”。模糊“自敘性散文”同“身邊小說”的界限,其結果只會削弱這些紀實作品的歷史真實性和細節真實性,削弱自傳材料的可靠性和可信性,從而淡化甚至消解消郭沫若自敘性散文的存在和自敘性散文中呈現出的鮮明、多樣、真實的自我形象。這對解讀郭沫若的自傳性作品和研究郭沫若生平傳記,恐非幸事。
注釋:
①韓中言語文化研究第9輯[M].韓國現代中國研究會,2005 年9月.
②《郭沫若學刊》,四川省郭沫若研究會主辦,2007 年第1期。
③韓中言語文化研究第19 輯[M],韓國現代中國研究會,2009 年2月。
④篇名括號中的寫作年代和體裁是本文作者加的。
⑤劇本:《湘累》《廣寒宮》《函谷關》《王昭君》《聶讔》(后改題《聶嫈》);對話:《無抵抗主義者》;小說:《鵷雛》(后改題《漆園吏游梁》)《歧路》《行路難》《湖心亭》《馬氏進文廟》(后改題《馬克斯進文廟》);散文:《雞》(后改題《雞之歸去來》)。
[1]郭沫若流亡日本時期的抵抗文學[J].郭沫若學刊,2007 ,(1).
[2]沫若自選集[M].上海樂華圖書公司,1934 年1月.
[3]郭沫若學刊[J].2007 ,(1).
[4]沫若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
[5]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0 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 .
[6]王昭訓等編.郭沫若研究資料[C].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 .
[7]王繼權,童煒鋼編.郭沫若年譜(上)[M].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 .
[8]龔濟民,方仁念編.《郭沫若年譜》增訂本(上)[M].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
[9]王錦厚主編.郭沫若作品辭典[M].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 .
[10]李晶標主編.簡明郭沫若詞典[M].甘肅教育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