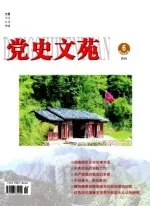論川陜蘇區的土匪問題
馬建堂 茍德儀
(四川文理學院 四川達州 63500)
土匪問題是近代中國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 “匪”字被用作所有為正統社會秩序所不容的異端分子的統稱,有土匪、會匪、教匪、煙匪等眾多名稱。國內外學者對 “土匪”的界定有多種,國內學者蔡少卿認為 “土匪就是超越法律范圍進行活動而又無明確政治目的,并以搶劫,勒索為生的人”。[1](P3)而近代社會,統治階級出于政治對立立場也常常指對方為“匪”,如在一些資料中,國民黨污蔑中共為“共匪”“赤匪”,這種出于政治偏見的污稱是我們必須摒棄的。川陜交界地區是土匪最為猖獗的地區之一。川陜蘇區作為當時中國的第二大蘇區,其創建與革命斗爭對中國革命進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川陜蘇區在創建及斗爭中,不可避免地要對土匪問題進行思考及治理,故而有必要對川陜蘇區土匪問題的概況、產生原因、治理方法、治理效果及對川陜蘇區整體革命斗爭的影響等問題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從而更深刻地認識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國情、民情的認識與把握,認識中國革命進程的復雜性與艱巨性。然而,目前學界對這一問題只在部分著作中有所論述①,尚未有整體、系統的研究,本文擬依靠相關革命史和地方史志資料,對川陜蘇區的土匪問題及其治理進行深入分析。
川陜交界地區土匪由來已久。川陜蘇區建立前夕,川東北、陜南地區土匪問題十分嚴重。土匪四處搶劫焚掠,劫場的事屢見不鮮,土匪劫城更是習以為常,四川“通江、平昌多次遭土匪堵住城門,搶劫一空”,“平昌縣52個場鎮,曾遭匪劫的有85%上,個別場鎮被匪焚毀殆盡”。[2](P15-16)1928年11月,“開江、開縣、大竹股匪千余人洗劫開江縣城”,劫走縣立中、小學師生、居民 200余名。[3](P15)1930年,陜西勉縣“連遭荒年,饑民遍野,土匪蜂起,李剛武、王三春、鐘振華等占領縣城,拆毀縣書院”[4](P18)。川陜交界的寧強、城口等縣匪害為最。如1928年,寧強 “李剛武匪部100多人偷襲陽平關”;次年6月 “李剛武勾結股匪趙元成率匪2000余人攻陷寧羌,大肆搶劫”;1930年11月,土匪王三春“攻陷寧羌縣城,盤踞1月”;1931年8月,大股匪首周樹民等,糾合匪眾3000余人,于15日攻陷縣城;1932年,大股匪何智聰、羅煙灰等常擾縣境,劫擄焚殺。[5](P24)1932年秋,“邊境土匪數百人進入城口縣的高觀、菜蒙、嵐溪、北屏等地搶劫”。[6](P16)
1932年12月,紅四方面軍轉戰川陜交界地區,在川陜邊區黨組織和廣大勞動群眾的配合支持下創建川陜革命根據地。川陜蘇區時期,匪患也極為嚴重,據徐向前回憶,當時川北地區, “土匪猖撅,嘯聚山林,經常打家劫舍,綁票殺人”[7](P253)。 偏僻的地區成為大股土匪巢穴,如“城口、萬源大山里是土匪窩”[8](P399)。 1933 年 3 月,一些被紅二十九軍收編的神團、土匪頭目趁軍隊外出剿匪襲擊了馬兒崖軍部駐地,軍隊領導人和骨干在戰斗中犧牲或被俘后被害,隊伍被打散,給革命造成較大損失,徐向前指出其主要原因是 “隊伍發展太快,成分不純。沒有采取果斷措施打亂建制,進行改造,清除反動頭目的影響”, “必須堅持依靠基本工農群眾的階級路線”[7](P274)。1933年春,城口縣遭 “陜邊土匪千余人竄入縣西高頭壩、冉家壩一帶活動”[6](P16)。 1934 年,大竹縣匪首徐世成“聚匪數百人”,盤踞東、西山中,時出洗劫場鎮[9](P176)。可見,土匪遍地是當時該地區的真實寫照。
川陜交界一帶較大的股匪有王三春、李剛武、袁剛、李茂春、余海清、韓剝皮、沈西亭等,他們長期活動在陜西的鎮巴、紫陽、寧強和四川的南江、通江、萬源、城口縣等地。巨匪王三春是川陜交界地區匪亂的代表,王幼年因家境貧寒,曾因家境貧寒而負債逃至陜西南鄭縣,返鄉后邀集窮苦人民、散兵游勇,組建“鎮槐軍”,開始了綠林生活,曾提出“打富濟貧”的口號,其匪隊迅速發展到2000余眾,槍支近千,編了3個團,主要藏于深山密林之中,廣泛活動于川陜邊區[10](P445-447)。李茂春股匪也流竄在川東、陜南邊境,
一、川陜蘇區建立前后川陜交界地區匪患概況
曾派匪徒200余人攻打設立在通江的川陜省保衛局機關,殺死紅軍指導員及無辜群眾數十人。[2](P148-149)余海清在民初就是南江的大土匪,后被鄭啟和招納為靖國聯軍授陜第二路的一名團長,李朝宣更是糾集通江、南江和漢中的地痞、土匪200余人,在黑巖塘通往漢中的隘口石少臺、雞巷子一帶行劫,一時間“好漢難出石少臺,命大難出雞巷子”。[11](P7)除了幾股大的土匪外,隱踞于深山洞穴的零星土匪就更多了。
土匪肆虐是民國時期各地普遍的社會現象,因而川陜邊區的嚴重匪患成為當時土匪問題的一個縮影。
二、土匪猖獗的原因
川陜交界地區匪患嚴重并不是偶然的,它與本地區各種社會因素有著密切的聯系:軍閥和地主剝削嚴重、政府賦稅繁多、自然災荒頻發,使農村經濟遭受嚴重破壞;政局長期動蕩不平,四川軍閥混戰連年,軍隊招匪、縱匪,大量散兵流為土匪;秘密結社匪化嚴重。在多種因素共同作用下,大量農民不堪重負而破產,被迫進入土匪隊伍,加之本地邊緣化特征,更刺激了土匪滋生。
第一,軍閥、地主壓榨,農民破產為匪。在川陜邊區,地主、軍閥占有大量土地,軍閥推行稅收預征制,肆意加稅盤剝,不少農民破產,被迫加入匪幫。在川北,軍閥、豪紳和地方保甲合成一體,欺壓人民,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且賦稅繁多,1931年時,一些區、鄉的捐稅已預收到了 1972年。[12](P261)陜南鎮巴坪落地區,1927年到1932年地主、富農共10戶48 人,占有土地 587.5 畝,占耕地面積 75.8%。[2](P12)在巴中縣恩陽區旱谷鄉東園村,“地富占田土總面積72.81%。平昌縣江口四戶暴發財主占田地8891畝,其中茍繼先一戶占田地3850多畝,橫跨川、陜、鄂三省,遍及十余縣,并仗恃軍閥范紹增的勢力,開設商號。 ”[2](P12)蘇區進行土改前,南江、長赤兩縣各六個村蘇維埃的典型調查:“占總戶數10.6%,人口15%的地主、富農占據土地 59%。 ”[2](P12—13)1933 年前,通江縣占人口 5%強的地主,占田地 60%左右。[2](P13)故而,在地主的盤剝之下,許多農民被剝奪得“屋里光光,肚里空空”,背井離鄉,境地十分凄慘,“而一無所有的赤貧戶竟占百分之五六十”。[7](P262)陜南漢中、安康的“破產的農民為僥幸免死起間,大批地加入土匪隊伍;土匪的焚掠將富饒地方變為赤貧,轉使更多的貧民破產而逃亡”[13](P11)。因而,農民生活十分困苦,在嚴峻的生存考驗下,許多樸實農民也不得不加入土匪隊伍。
第二,軍隊招匪、縱匪,殘兵為匪。四川自1918年實行防區制開始,軍閥連年混戰,社會經濟破壞嚴重,無業游民不斷增多。同時期,陜西社會也處于激烈動蕩中,陜南人民深受地主摧殘、兵禍之害,軍隊的招匪措施更加重了匪患,殘兵為匪者極多。川陜交界地區破產民眾無法生活,一些人只得鋌而走險,以搶掠為生,于是形成了土匪泛濫的混亂局面。如南江捕獲之匪“匪徒中有供稱,因軍款一元,無法繳納,迫于生計,以致出下策者”[14](P567)。 四川軍閥對土匪多采取招撫利用,在紅軍進入川陜邊時,四川軍閥企圖進攻川陜根據地時,大肆招撫土匪隊伍,如1933年5月,劉湘委任匪首王三春為 “城 (口)萬 (源)游擊司令部第一縱隊司令”,同年8月,徐躍明委任匪首李茂春為“川陜邊區獨立團團長”。[2](P149)最終導致兵匪一家的惡果,而民眾自衛防匪也多是徒勞,土匪的徹底治理只能成為空談,土匪肆虐成為當時社會最為黑暗的一面。然而在軍閥混戰的動蕩環境下,土匪問題始終未能根治。
第三,自然災害影響。1930年前后,川東北、陜南地區出現出現長時期的嚴重干旱,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1931年3月9日,《上海籌募陜災臨時急娠會啟事》稱:“陜西四載之中,顆粒無收,實為中國今日最大最重災區。”[15](P266)陜南,一連三年,“顆粒無收”,寧強、鎮巴、南鄭等地區尤為嚴重。安康、平利、紫陽、嵐皋、漢陰、石泉諸縣,“十分之七地畝,一望荒涼”,“統計漢南三百余萬人民,死亡在百萬以上,尚余垂斃之二百萬災黎”。[15](P268)四川自1920年起,災荒連年,其中又以亢旱最為嚴重,如“1921至 1922年,1924至1925 年,1927 至 1929 年, 皆干燥不雨”[15](P289),1927-1929年,川北諸屬連旱三年,荒情最重,“赤地千里,粒米未收”。據華洋義販會報告書稱:“本省災情最重者為川北二十九縣”,“其中有秋收全無者,有略獲薄收者,更有籽糧尚無著落者。受災人民約有八百萬之眾。”[15](P261)因災荒而加入匪幫的貧農不在少數,1929年旱災時,通江、南江等縣的饑民,“因生活無法維持,群起紛亂,紅燈教不畏槍彈,肆意焚殺、反抗駐軍”,“附之者已不下四五萬人”。[16](P261)宣漢因荒歉“人民饑荒特甚”,“土匪蜂起,搶劫時聞”,又如廣安饑荒,“饑民載道,日聞劫掠之事”[14](P567)。
第四,秘密結社蛻變為匪。川陜交界地區,秘密結社形成較早,各種會道門名目眾多,不少秘密結社組織蛻變為匪,如“神兵” “紅燈教” “蓋天黨” “扇子會”、 “圣母團” “大布團”等。各類會道門被地方軍閥、地主利用,成為危害蘇區人民的反動勢力,會道門到處燒殺搶掠,殘殺紅軍干部和游擊隊,并往往以神水咒符欺騙群眾,脅迫群眾參加,1934年12月,蓋天黨在南江縣平崗鄉起事時就宣稱 “一人不參加殺全家,一家不參加殺全族”,使當地三百多名群眾被迫參加。[17](P127)
第五,川陜交界地區的地理因素。川陜交界地區以大巴山為中心,遠離兩省政治中心,高山林立、山水交錯,政情、民情相對復雜,政治統治相對薄弱的地區,經濟較為落后,邊緣特征明顯,易于形成行政和法制管理的空白點,加之交通閉塞,易于眾多慣匪藏匿,為惡一方。因而該地區成為當時中國土匪問題最為嚴重的地區之一,尤其是的寧強、鎮巴、通江、萬源等縣成為土匪泛濫之地,正如美國學者施堅雅所指出,“正是在中國的地區邊境,地方社會顯得最異常,樣式也最多:在那里,你可以看到非漢族的土著部落、還未完全漢化的小股群居點、進行不法生產活動而法律和稅官又無法約束的自治群體、從宗教派別到煽動性秘密結社的異端團體和土匪”[18](P378)。該地區土匪攻占縣城成為常事,川陜邊境的王三春便是這一地區典型的巨匪,其匪部活動于陜南的寧強、紫陽,四川的萬源、通江、南江、城口等20余縣,其隊伍出沒于大巴山中,為害川陜邊境數20多年,匪眾最多時達四五千人。[10](P445-447)
可見,土匪猖撅是多種因素的結果,其本質無疑是民生危機的體現,“窮入無衣無食、無田地種、無活路做,即被迫去當棒老二,造成土匪災。棒老二不是窮人干的,是國民黨逼著去干的”[19](P411),土匪的肆虐迫使許多農民背井離鄉,逃荒要飯,房無人住,田無人耕。故而土匪危害極深,使大量農民脫離生產,甚至反過來破壞社會生產,嚴重破壞了正常的社會秩序。
三、川陜蘇區對土匪的治理
中國共產黨十分重視對土匪的治理,毛澤東曾在分析中國社會各階級時就指出, “有數量不小的游民無產者,為失了土地的農民和失了工作機會的手工業工人。他們是人類生活中最不安定者”, “如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20](P8—9)。 1933 年 6 月 24 日,《中共川陜省第二次黨員代表大會討論的斗爭綱領》第十條規定,“徹底肅清赤區內的反動民團土匪”[19](P18),明確提出了徹底消滅土匪的主張。1934年10月,中國共產黨川陜省第四次代表大會《關于目前政治形勢和粉碎國民黨 “包剿”的決議》指出,“在中國農村的極度破產和長期的封建統治下,必定發現極多的失業農民走上 “棒老二”式的行動和造成了極深刻的落后封建思想”,對此,黨必須 “在文化斗爭中堅韌的說服落后農民”。[21](P25)對于棒老二、失業流氓的痛苦,“只有共產黨才提出沒收軍閥家財,救濟失業,分配棒老二正當職業和工作”,并必須盡量的影響他們,吸收他們到革命方面來。[8](P354)
為鞏固根據地,蘇區政府“采取軍事打擊和政治瓦解相結合的方針,依靠群眾,消滅土匪”[7](P272),采取了多項綜合措施來保衛蘇區社會安定。
1.進行政治瓦解,爭取土匪自新。川陜蘇區認真分析軍閥統治下的政情、民情,尤其考慮到當時在國民黨的統治下,所以決定“對于流氓地痞、滾刀皮、棒老二等,只要他們改邪歸正,做工務農,一概不殺”[19](P235)。 1934 年 12 月 5 日《中共川陜省委關于對反動團體斗爭的決議》中強調:“對于民團團丁、白軍士兵、棒老二里面的弟兄和流神痞子等,一律歡迎其自首,改邪歸正。”[21](P160)這些政治宣傳對于土匪的主動自新,脫離匪幫,起了重要作用。1933年春天,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傅鐘在通江北200余里的兩河口上面,“將盤據于曲江洞的王三春部職業土匪(棒老二)八十余人,用標語、口號、傳單、書信等方式,通過軟化、感動而爭取投降了”[8](P246-247), 從而摧垮了巴山土匪的老巢。1933年5月,傅鐘命中共地下黨員武志平給陜南西鄉縣黑風洞大匪首袁剛寫信,此前武路過黑風洞時已取得了袁剛一定的信任,信中明確指出“要是不顧大義于紅軍采取對立態度,必定要使他自己首先滅亡”,后來袁剛為保存實力,沒有和紅軍對抗,這封信起了重要作用。[22](P128)
2.開展土地革命,解決人民生計。土地高度集中與地主、豪紳、軍閥手中,是農民破產和土匪橫生的重要根源。川陜蘇區政府把解決土地問題作為根治土匪問題的根本。蘇區政府在土改過程中,注重策略。1934年12月的《平分土地須知》規定:“當過棒老二、土匪、小偷,只要改務正業,有當地窮人擔保,一樣可以分得土地。”[19](P521)同樣,對于眾多的會道門組織的成員,也有分得土地的機會,肅反工作規定:“被脅從加入反動團體或反動武裝組織 (蓋天黨、圣母團、扇子會、木刀會、煙戶團、清共團、義勇隊、自愿隊……等)的雇工貧農中農,只要能改過,一律不究,依舊得到土地利益,其家財不能侵犯,仍受蘇維埃保護。”[21](P170)這些措施不但徹底的解決了根據地人民的生計問題,還有利于瓦解匪幫,促進土匪從良。
3.通過軍事斗爭,消滅頑固土匪。蘇區政府在加大宣傳教育、開展土地革命的同時,對僅靠政治攻勢難以奏效的投靠軍閥的土匪和長期危害人民的反動民團、慣匪,則進行徹底的軍事打擊。在紅軍主力開展三次進攻戰役的同時,后方駐軍和地方武裝廣泛進行了清剿土匪的斗爭,如“在蒼溪、營山、蓬安、長勝、閬中等縣即殲滅土匪3000余人。在陜南、萬源、城口等地殲滅了不少股匪”,并“將長期盤據大巴山的大土匪王三春趕到了鎮巴、紫陽、城口邊境”[2](P114)。 1934 年,紅軍經過多次圍剿,最終將長期活動與西鄉、鎮巴縣的山大王高樹臣匪幫剿滅,殲滅了其部大部分土匪。[23](P13-15)1933年二三月間,紅二十九軍多次打擊王三春匪幫,“一次殲滅匪部三百多人”[23](P45)。
與此同時,蘇區政府還嚴厲打擊了形形色色的反動地主武裝、民團、扇子會、神團以及散兵游勇等。1933年10月中旬,以魏福堂為首的地主武裝,糾集土豪劣紳楊法清和匪首沈尚清等組織“扇子隊”約2000人,盤踞在蓬安縣的銅鼓寨上,并進犯紅軍,被紅軍“消斃該地反動民團和扇匪1000余人,活捉過來 100 多,少數殘匪四處逃散”[2](P230)。 通江反動武裝“蓋天黨”,常在沙溪、洪口一帶的廟壩場、鐵坪等地進行搶劫、暗殺,前后殺害區鄉村干部40多人,燒毀房屋數百間,搶劫民財無數,1934年8月中旬,警衛營“全殲了這股蓋天黨匪幫,擊斃其匪首頭子”[2](P230-231)。 1933 年 3 月 3 日,大池大本團楊子布,三元神團馮良謨,通江神團袁有章共2500多人,進攻紅軍部隊,最終“紅軍擊潰了全部匪徒”,敵人傷亡眾多[24](P47)。1934年2月下旬,神團郗大恩聯絡萬源神團張文學等共2000多人,偷襲紅二九六團某部,茅坪山游擊隊配合紅軍采用口袋戰術, “斃匪四百多名,俘虜三十多人,繳獲步槍、土槍、刀矛三百多件,其余匪徒全部擊潰”[24](P69)。這些措施使土匪無力襲擊地方黨政機關,又鞏固了后方秩序,有力的保衛了的人民的生產生活。
4.建設群眾武裝,提高民眾自衛能力。鑒于紅軍主力部隊到前方堅持作戰,土匪常常偷襲蘇區軍政機關和人民群眾的狀況,根據地積極發展群眾的力量,大力進行地方武裝建設,先后建立了游擊隊、赤衛隊、兒童團、少年先鋒隊等組織,充分發揮群眾武裝的組織作用,這些組織的主要任務就是協助軍隊清剿土匪,保衛蘇區人民群眾生產生活的安全。如《開展游擊戰爭的決議》規定,各縣游擊隊要“配合當地赤衛軍肅清山林散匪”[19](P128)。一般青年要參加紅軍與地方武裝獨立營、游擊隊,“發動游擊戰爭、搜山,到老林中去捉拿棒老二,不容許蘇區內有一個反革命份子”[24](P639)。游擊隊在發動群眾斗爭的過程中,“無限制地號召雇農分子參加肅清一切地主、富農、土匪、流氓、階級異己分子,改造游擊隊的成份,擴大游擊隊的組織”[25](P730)。陜南蘇區先后建立游擊隊164支,游擊隊干部、隊員7000余人,遍布廣大鄉村,1932年,赤北縣游擊隊“主動開展四次清匪斗爭,活捉土匪14名”,1933年又開展四次清匪斗爭,“打死打傷團丁、土匪百余名”[26](P11-12)。1933 年,黃大萬區游擊隊槍決了慣匪高福安,窮苦百姓拍手稱快[27](P308)。1933年10月27日夜,赤北縣赤衛軍發現大批棒老二,將他們“打得大敗逃散”,工農群眾非常痛快[21](P302)。1935年元月,胡寶玉率領游擊隊在中仁寨,“殲滅土匪 100 多人,獲戰馬 10 匹,槍械 100 余支”[28](P10)。蘇區政府重視地方武裝的軍事訓練,以提高其防衛能力。1933年秋冬,剿滅長赤縣大匪首余海清的長赤縣軍區黃指揮長、紅軍柴參謀專門給參加作戰的地方武裝上了 “剿匪課”,“使大家掌握了隱蔽偵察、利用地形地物等必要的戰術技術”[11](P174)。群眾武裝成為了蘇區治匪的重要力量。
5.普及文化教育,破除封建迷信。官紳土豪往往利用封建迷信蠱惑人心,組織起各種反動會道門武裝,如 “神兵” “蓋天黨” “扇子會” “圣母團” “大布團” “紅燈教”等不下數十種。對此,根據地通過群眾識字教育、馬列主義宣傳、政策講解等措施,反對封建迷信,提高群眾文化水平與分辨能力。1934年4月3日,中共川陜省委提出加緊宣傳工作, “揭破紅燈教、神團、蓋天黨、孝義會等的欺騙”,并明確指出: “一切神仙鬼怪的欺騙造謠,都是發財人整窮人的。窮人天天求神拜佛,還是吃不飽穿不暖;發財人天天整窮人,反而有吃有穿。”[25](P789)同時,蘇區政府要求 “要多編印關于科學常識的小冊子,加緊蘇區文化教育運動,辦讀報班、識字班、俱樂部、閱報室、新劇團、列寧學校,多作科學講演,提高群眾的文化科學水平,深入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傳科學思想來養成群眾的正確思想”[29](P348), 從而使群眾認識到了反動會道門的真相,提高了根據地群眾的辨別能力。
在土匪治理中,根據地往往多種措施并用,起到了很好的效果。1933年冬到1934年春,主要就是靠宣傳動員發動了群眾參加地方武裝投入戰斗,“又在戰斗中靠宣傳喊話瓦解敵人和爭取不明真象的群眾脫離匪幫”,最后取得了平息南江的蓋天黨和消滅長赤的匪首余海清的勝利。[11](P113)
四、川陜蘇區土匪治理的影響
川陜根據地深刻認識中國國情,揭露軍閥統治的殘暴面目,實施正確的政策措施,較好地治理了川陜根據地的匪患。
第一,鞏固了川陜蘇區政權。根據地的安定也使紅軍能全力投入到反圍剿的戰斗中,有力地支援了根據地的反“圍剿”斗爭。
第二,建立安定社會秩序,鼓舞廣大人民的生產生活的積極性。如渠縣,蘇維埃建立后,“一面清剿土匪,一面打土豪分田地,解決了農民生活困難,加上肅反殺了一些土匪,從而出現道不拾遺,夜不閉戶的良好社會秩序”[30](P74)。
第三,教育了廣大群眾,壯大了革命政權。由于政策措施正確,眾多土匪脫離匪幫,頑固土匪被堅決消滅。同時,川陜蘇區的土匪治理作為局部地區匪患治理,也給中共后來剿匪斗爭提供了寶貴經驗。
總之,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到近代中國的政情、民情,深入解決近代社會轉變下的民生危機,在川陜蘇區采取政治瓦解、進行土改、軍事打擊、發動群眾、宣傳教育等多種措施并用的方法,有效地消除了民初以來就盤踞在川陜邊境的土匪勢力,使眾多民眾脫離匪幫生活,重新回歸社會生產,甚至加入到革命隊伍中,從而創造性的消除了土匪這一社會毒瘤,促進了社會秩序的穩定和革命的深入開展。○
注釋:
①關于川陜蘇區土匪問題的研究主要有:邵雍著《民國綠林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6-321頁。該著作對川陜根據地土匪的危害與中共治匪策略有一定涉及,但缺乏系統性與完整性。
[1]蔡少卿.民國時期的土匪[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
[2]中共達縣地委黨史工作委員會.川陜革命根據地斗爭史[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
[3]四川省開江縣志編纂委員會編.開江縣志[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4]勉縣志編纂委員會.勉縣志[Z].北京:地震出版社,1989.
[5]宋文富主編,寧強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寧強縣志[Z].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
[6]四川省城口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纂.城口縣志[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7]徐向前.歷史的回顧(中)[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5.
[8]四川省社會科學院,陜西省社會科學院.川陜革命根據地史料選輯[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9]四川省大竹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纂.大竹縣志[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2.
[10]河北文史資料編輯部編.近代中國土匪實錄(上)[C].北京:群眾出版社,1993.
[11]中共南江縣委黨史研究室編.川陜革命根據地南江斗爭史[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12]紅色中華[N].第 121 期,1933 年 10 月 24 日。
[13]紫陽縣志編篡委員會.紫陽縣志[Z].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
[14]呂平登.四川農村經濟[M].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
[15]李文海等.近代中國災荒紀年續編[Z].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
[16]《蜀北災重死亡相繼》,上海《民國日報》,1929 年 7 月 4日。
[17]四川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川陜革命根據地科研組編.川陜革命根據地資料選編[Z].1978.
[18](美)施堅雅.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M].葉光庭,等譯.北京:中華書局,2000.
[19]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選編編委會.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選編(上)[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
[20]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A].毛澤東選集(第一卷)[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1]劉昌福,葉緒惠編.川陜蘇區報刊資料選編[Z].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
[22]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武平志.秦蜀日記[A].中共黨史資料(第十九輯)[Z].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
[23]中共鎮巴縣委黨史辦編.紅軍在鎮巴.鎮巴縣黨史資料(第二集)[Z].1988.
[24]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鎮巴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組.鎮巴文史資料(第 2 輯)[Z].1988.
[25]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選編編委會.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選編(下)[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26]中共陜西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陜西黨史專題資料集(六).川陜革命根據地陜南蘇區[Z].1987.
[27]達縣人民武裝部編.達縣軍事志[Z].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
[28]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陜西省紫陽縣委員會編.紫陽文史資料(第 4 輯)[Z].1999.
[29]紅色號角編委會.紅色號角—川陜蘇區新聞出版印刷發行工作[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30]中共渠縣縣委黨史工作委員會.川陜革命根據地渠縣蘇維埃資料選編[Z].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