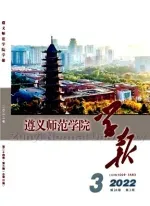從行政決策過程分析媒體的積極角色
梁豐
(湖南大學法學院,湖南長沙410082)
近年來,由于經濟的開放和發展、技術的進步,毫不夸張地說,我國步入了媒體的“黃金時代”,尤其是網絡媒體微博的迅猛發展。行政決策貫穿于社會管理和服務的全過程,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媒體與政府的決策緊密相連。一方面,決策的科學性和民主性牽動著社會的穩定,另一方面,社會管理重心不在管,而在于理,即理順、理通,讓社會各方的訴求通過一定途徑去表達,聲音的有效表達是社會穩定的基礎。因此,本著促進社會各系統良性和諧互動,推動社會管理創新,作為一種逐漸成熟的力量,我國媒體在行政決策過程中能發揮的積極作用將越來越顯著。
一、不同決策階段媒體擔當的角色
就當前國內情況而言,我根據行政決策的過程,試圖歸納出媒體在不同決策階段可能擔當的角色。
(一)行政決策前
1.決策鋪路者
這種媒體角色指的是媒體被充當行政決策機構的有意的鋪路者。每當行政機構準備做出某種決策之前,將會通過其設立甚至控制的一些媒體,有意選擇報道跟那個決策相關的一些東西,而引起民眾知曉以及社會上一些討論。總之,一切的報道都是為決策的制定而鋪路,制造有利于決策實施的輿論環境,是行政機構試圖贏在起點上的通過媒體報道的有意識的行為。決策鋪路者的典型代表就是1978年我國關于實踐是否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而引發的討論。當時是媒體先行,刊登鄧小平的文章,引發討論,然后改革開放這個重大決策的號角被吹響,改革開放的序幕被拉開。
2.決策引發者
此種媒體角色是指媒體為了引起社會對某個問題的關注,報道某方面的信息,從而將一個問題轉變為社會性公共問題,或民眾為了解決某個社會問題,或改變某種負面的現狀,通過向媒體報料,然后媒體報道,設法引起決策者的關注。這個過程在公共政策分析學里面稱為公眾議程或系統議程,與此相對應的另一議程稱為政府議程或正式議程。媒體在此擔當的角色就是在公眾議程和政策議程之間搭建一座橋梁,即通過報道,有目的地去引發決策者關注某些社會問題,成為行政機構決策的信息源,期望甚至迫使其采取某些行動去解決。決策引發者的典型例子很多。如最近故宮失竊案發生后,媒體立刻又報道出故宮里的建福宮變身富豪會所,在公眾為這件事情爭論不休時,媒體再一次曝光承德避暑山莊內即將開營私人會所。這一系列的追蹤報道,都會大大地引起決策者對故宮等著名歷史場館的管理、使用等問題的深入關注,從而推動相關方面新決策的制定和實行。
(二)行政決策中
1.決策協助者
首先,在媒體幫助下,更多同類型、相關問題被發現。通常在某個別問題被媒體曝光后,或者某個政策剛開始制定時,媒體就會接二連三地報道同類型或相關聯的事件,使問題的本質越來越充分地被挖掘出來。如幾次毒奶粉事件包括安徽阜陽為代表的大頭娃娃奶粉事件和石家莊三鹿為代表的結石奶粉事件,原本只是一些個體或在一個地區被曝光出來,后來媒體不斷報道類似的新聞,使民眾和政府認識到,這些問題不只是發生在幾個人身上,也不只是發生在某個省份(廣度),問題的嚴重程度(深度)也要被重新評估和考慮。
然后,媒體通過社會調查,試圖向決策機構提供建設性的意見、建議和參考。以往一直存在著一種決策單向、封閉的傳播傾向,忽視民眾的感受,缺乏民眾的參與,這種傾向的極端是“三拍現象”。因為得不到民眾反饋的信息,決策者無法做出及時的回應和恰當的調整,從而決策者與民眾之間難以實現良性互動。具體來說,政府事先在媒體上對即將出臺的政策方案進行公示,公開征求社會各方的意見,然后再次通過媒體,及時吸納各種有益的意見和建議,不斷完善政策方案。如《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征求社會意見,每天的時評經常涉及此話題,最突出的新聞就是央行專家李稻葵炮轟個稅體制“弱智”,幾天后,新華網就報道全國人大邀請十余位專家對個稅法修正案草案發表意見。這些都會對決策機構提供一個實在的參考,也讓媒體成為決策機構的一個得力的協助者。
再次,通過媒體報道,幫助樹立政府勤政高效的形象。在英國社會學家約翰·B·湯普森看來,傳媒的一個特質就在于象征意義的生產[1]。同時,公共政策分析學也認為,公共政策的有形效果可能十分微弱,其初衷是讓目標群體以為他們關心的問題已經得到解決或者正在解決之中,從而減輕對政府的壓力或者激發起某種精神。但也不是可有可無的形式主義。例如:就業機會均等的政策也許在實踐中難于推行,但卻能使人們相信政府至少在表面上不容忍就業中存在的各種歧視。這些公共政策對于維護社會穩定,使政府獲得人民的支持等方面有著積極的作用①有關論述請參閱陳慶云主編的《公共政策分析》,北大出版社。。
2.決策監督者
二十一世紀以來,我國無論政府和民眾,都越來越重視程序正義。因而媒體在行政機關進行決策的過程中,會著重監督決策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是否有某些環節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也會深究政策制定和參與主體是否具有合法性;以及會就決策的部分內容以及一些實施前的草案或討論稿所顯露出來的問題進行探討,從而對決策機構進行監督,促進決策的科學性和民主性。
(三)行政決策后
1.決策執行推動者
一方面,媒體的報道大大地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權,公民不知情,政策難推動。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因此,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首先,知情權的法理根源在于主權在民,或用另一說法: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因此,人民就被自然地賦予和享有知情權,就有理由通過包括媒體的各種途徑去監督政府的政策執行。然后,知情權的現實依據是:公民要行使各種權利和自由就首先要知曉有關信息,掌握有關情況和證據,否則,就會無的放矢、言之無物[2]。同時,某些執行法規或指令的頒布實施,有部分人卻因為各種原因不知曉,從而在日后自己違反了該規定或法律都不知道。媒體的成長、發展最終發達恰恰就是這種對信息不對稱現象很好的彌補。接著,知情權的保障和完善是民眾從被動臣民至被動公民然后向主動公民轉變的過程,是政府管治從封閉向開放轉變的過程,是“現代國家民主憲政的基礎要素”,也是“防止出現惡劣政府的必要條件”[2]。
另一方面,媒體具有政治宣傳屬性,只是程度不一而已。它受控于國家,是政府管治的工具、傳聲筒,它肩負著傳達政令,使政令暢通的使命,它以輿論導向的方式影響著社會和民眾的行為和心態。當今社會是信息傳播高度發達的社會,材料、能源和信息是現代社會發展的三大資源[3],過去對傳媒的管理辦法很多已經不合時宜。很多時候要求政府必須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通過媒體發布信息,搶占輿論制高點,否則就會陷入被動,不但損害公眾的知情權,而且對決策機構的公信力以及新聞媒體的形象也是一個降格。這也要求媒體必須密切關注新決策的推行。如最近“醉駕入刑”,各地媒體不斷關注此政策的施行情況,不斷曝光一些典型的例子。如音樂人高曉松被判刑、昆明城管人員醉駕被查獲、廣州醉駕入刑第一人被吊銷駕照5年不得重考等事件的曝光,都對政策的宣傳起了促進作用,尤其對社會和民眾起到警示作用。據媒體的后續報道:醉駕入刑實施3日后,廣州醉酒駕駛同比驟降75%;醉駕入刑18天,成都酒駕下降4成①詳情請參閱:大洋網http://news.dayoo.com/guangzhou/201105/06/73437_16505937.htm;《華西都市報》 2011年 5月 19日。。
2.決策實施監督者
現代社會,媒體逐漸成為相對于立法、行政、司法的第四種權力或被稱為權力的“第四極”,是監督政府,遏制權力被濫用,保障公眾知情權的重要工具,甚至是“無冕之王”。媒體的自由度慢慢擴大,積極性空前高漲,它通過廣泛采集和報道社會公眾意見,密切關注著行政決策實際的執行,從而能及時糾正公共決策執行的異化。
從系統論的角度分析,戴維·伊斯頓認為,“行為系統在環境的影響下產生并反轉過來影響環境”。政治系統輸出了權威性的決定、法令或政策后,會給環境帶來一系列的變化,而當環境發生變化后,媒體和民眾就會對政治系統施加正壓力或負壓力,以是否支持和對政治系統提出希望和要求等形式反饋給政治系統。通俗具體地講,就是在決策實施后,媒體與民眾結合,向決策機構反饋自己的意見,包括贊同決策或反對決策。這個反饋過程的本質是利害關系人對利益分配的應對行動,因為公共政策的實質是政治系統的權威性輸出,對全社會利益進行權威性分配②來自戴維·伊斯頓的論述。分配的結果對部分人獲得利益,也使部分人失去利益。得益方試圖形成聯盟,合法或非法地抵制政策終止,損失方試圖施壓和影響決策機構去改革甚至阻止政策執行。
結合T·史密斯的政策執行過程模型和M·麥克拉夫林的調適模型來分析,當決策機構發布和實施政策后,就會對目標群體產生一種緊張(tension),從而會做出適當回應,向決策機構給予反饋,同時,執行者和受影響者之間會通過一種雙向的信息交流和互動達到一種相互調適的狀態。再一次拿“醉駕入刑”作例子。最初,各地媒體紛紛報道醉駕入刑第一人,接著,最高法院副院長張軍給出“醉駕入刑”新解釋,后來,各地有自己的做法和理解。如深圳一次醉駕審判公訴方就明確提出個人言論不能作為法律依據,也不能影響判決,然后有媒體就發文指出醉駕入刑應由人大解釋,而非最高法院。再到后來最高法院將以案例形式發布“醉駕入刑”適用標準,供各級法院參照試用。時隔一日,公安部再透露,在刑法修正案(八)和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公安部門對經核實屬于醉酒駕駛機動車的一律刑事立案。整個過程,都有媒體在不懈地跟蹤報道,監督政策的實施情況。
3.決策行為裁判者
媒體不僅具有政治屬性,還具有產業屬性,且后者的比例越來越大。媒體說到底是人辦的,是人便會有利益,有好惡,這些都會影響到其公正。媒體越來越偏向為一個事件去自主地定性(包括正負),似乎充當了一個裁決者。這當中有其合理性,因為不同媒體有不同的媒體理念和立場,還有其追求的利益;但也有不合理性,媒體的定性不一定客觀,不一定全面,不一定專業,這樣就會使不少受眾感覺被牽著鼻子走。在媒體日益發達的今天,這種對決策行為的裁判行為對社會的影響將會非常深遠。
二、媒體角色的發展趨勢
隨著我國人民利益覺醒和權利意識的驅動,我認為媒體在社會發展的大舞臺上,不同角色出現的頻率和參與的深度都將出現強化的發展趨勢。
一方面,決策引發者和裁判者的角色將不斷增加
今后,我國的媒體將會逐漸告別以往的觀望以及消極被動地向上級部門“請示”以求“尚方寶劍”,逐漸告別等待新聞通稿的做法。當社會問題凸顯時,尤其是面對突發事件,媒體將會及時快捷地報道,從而向政府決策部門提供足夠的信息資源和決策參考,對未進入政策議程的問題,將更有力地推動其進入政策議程,對已進入政策議程的問題,將通過多次報道使之獲得更多關注,而不是把一個鮮活的新聞弄成舊聞。因此,媒體報道的內容和形式將更加多樣化。現在不僅是電視新聞和報紙了,手機和網絡成了媒體傳播的生力軍。如廈門PX事件,當以趙玉芬為代表的105個政協委員聯署的議案被傳統媒體披露后,市民們就通過手機和互聯網傳播信息,進行組織動員;廣州番禺區垃圾焚燒廠選址事件,媒體可謂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還有近來的廣州地鐵九千萬翻新工程,如果沒有媒體不懈的報道和呼吁,地鐵公司是不可能出來回應問題同時并修改翻修計劃的。這些例子都說明,媒體將逐漸變得主動,成為社會問題進入政策議程的觸發機制;將逐漸成為影響政府決策的重要力量,為決策的制定提供多角度的視角和思考。而媒體主動觸發和影響決策的動力在于利益表達,在于各階層為了保護自身利益,為了讓自身利益得到決策部門的重視和回應,通過媒體向決策部門進行影響和游說。對同一個事件,不同媒體會有不同的報道角度和關注焦點,會有不同的篇幅,更會有不同的定性。
另一方面,監督角色的戲份將大大增強
首先,輿論監督性的報道在量和質上會增強,頻率越來越高,覆蓋面越來越廣,批評的力度和深度越來越強。以往行政決策主要靠的是行政系統內部的上級監督,外部監督薄弱。而隨著媒體的逐步發展,信息技術的不斷普及,公民的知識素質和民主意識的不斷提高,反饋和輸入的渠道和質量漸漸得到了改善。尤其在一些沿海發達城市如廣州這樣一個媒體比較活躍的地方,媒體的監督功能給政府的行政決策施加了良性的壓力。就連市委書記張廣寧也通過媒體就2010年廣州亞運期間工程擾民問題向全市市民道歉。在其他制度化途徑還沒有得以完善的情況下,媒體的監督和批評將會對我國政府依法行政,科學民主決策方面起到重大的推動作用。
第二,民眾逐漸與媒體結合成一體,形成合力去監督政府的依法行政。沒有媒體曝光行政決策后的實施情況,有關部門很難會去重視和改進。如廈門PX項目事件中,公眾組成自發、臨時的組織網絡,借助媒體,去反對此項目,而行政機構后來也做出了積極的回應,通過主動引進程序技術、構建對話平臺來化解危機。自從新世紀以來,中國進入了一個社會沖突高發期,“群體性事件”數量急劇上升。1993年全國發生群體性事件還只有0.87萬起,而2005年上升至8.7萬起,2006年更是超過了9萬起[4]。而近幾年執政黨異常重視社會穩定,例如在中央黨校輪訓全國的縣委書記。在2011年2月,胡總書記在中央黨校開班式上,提出要扎扎實實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管理體系,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減少不和諧因素。要從根本上減少群體性事件,需要改革行政決策機制,為長期以來被漠視的社會群體提供參與行政決策的渠道,讓他們通過提升與自身切身利益相關的政策的質量來改變自身的處境[4]。因此,不論從民眾、還是媒體、抑或政府方面考察,都能夠推斷出民眾和媒體結合的這種現象將越來越顯著。或者說,媒體將成為聯通民眾和政府的一座堅實的橋梁。
第三,媒體將成為推動政府信息公開的主力軍。古語云:“宣則成隱則敗。”信息公開的法理依據是,行政公開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之一。有關行政會議、會議決議、決定以及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活動情況應允許新聞媒體依法采訪、報道和評論。盡管我國的一些權力部門已經初步嘗試公開一些政務,同時我國不少熱心公民和組織包括媒體都極力呼吁政府信息公開,但由于現行法律缺乏明確的保障和細化的條款以及可操作的程序,政府信息公開很難落到實處。學者杜鋼建認為,某些媒體的評論文章把要求公布真相的聲音說成是“別有用心”、“居心不良”、“惡毒攻擊”等等,不僅沒有發揮媒體的監督作用,而且喪失了起碼的職業良知[5]。
總之,從根本、長遠來說,媒體的監督、公開有利于迫使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防止暗箱操作,使權力腐敗失去生存的土壤,從而有利于緩解社會矛盾,有利于維護社會穩定,有利于促進社會各方的良性互動。
三、小結
基于上述媒體在行政決策中的角色及其發展趨勢,我們有理由相信,在與行政決策機關、民眾的互動中,媒體自身將發揮一種積極的協作和橋梁作用,最終三方達到互利共贏。即:事前為決策機構提供科學意見,事后追蹤推動和監督決策的實施;對上分擔政府職能,協助決策,對下聯合民眾監督政府;對上傳達民意,對下傳播政策法規。封閉的管理主義治理模式,成本只會變得高昂。而媒體恰恰可以成為決策機構和民眾的溝通者,聯通兩方,引導民眾,創建良好的心理環境,培育和諧的公共秩序;成為社會的安全閥、減壓器,釋放社會內部的戾氣和緩解壓力。
[1] 徐桂權,任孟山.時評作為一種利益表達方式:傳播社會學的考察[J].開放時代.2010,(2):115-132.
[2] 李矗.“兩難選擇”與“自由應對”:試論新聞媒體的公共角色定位.新聞記者.2011,(2):39-44.
[3] 江澤民強調加快我國信息化建設[N].中國青年報,2001-12-27.
[4] 王錫鋅,章永樂.從“管理主義模式”到“參與式治理模式”——兩種公共決策的經驗模型、理論框架及制度分析[A].行政規制論叢[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5] 劉天時.當SARS碰撞中國傳媒[N].南風窗,2003-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