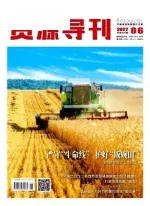報刊文摘
報刊文摘
城市綠化不需要“天價樹”
蘇州有位朱先生,開車遇到意外,沖進了路邊的綠化帶,撞傷5棵樹,分別是羽毛楓、五針松、大葉黃楊球、五針松、羅漢松。沒過幾天,綠化公司給朱先生寄來一張罰單,分別要求朱先生賠償28000、37500、280、37500、31000元,最后雜七雜八算下來,總共要賠13萬元,而且還說這只是按70%的死亡率算的。
此前有新聞說,珠海耗資800萬元,在兩條道路的導流島上,種植了31棵羅漢松,株均26萬元。跟株海的天價樹相比,蘇州這5棵樹,才值十幾萬元,實在算不得什么;而珠海有關部門給自己找的借口,說是在廣州和中山,這樣的樹多了去了。
我就弄不明白,熱帶那些葉子像芭蕉扇一樣的樹,偏就挪到我們亞熱帶來種,結果,死了不少;珠海、廣州、中山這樣的熱帶,卻要種羅漢松這寒帶的樹,結果,難免天價。俗話說得好,人挪活,樹挪死。這還不是簡單地挪個窩,簡直稱得上冷熱兩重天,乾坤大轉移。花錢多,死得快。不就綠化嗎?什么樣的綠不是綠?讓熱帶的樹,回到熱帶去;讓寒帶的樹,回到寒帶去;各得其所,有什么不好?
為避嫌,更為生態,城市綠化的怪相,可以結束了。買樹,應該交由政府集中采購;審查預算,不僅要審花多少錢,也要審一審買了多少樹。尤其是幾萬元一棵,幾十萬元一棵的樹,真要采購,還該有紀檢部門的介入。為了少惹一些麻煩,我覺得,還是老老實實種一點適合綠化的樹,少燒一點錢。城市綠化,不需要天價。(摘自2010年12月14日《中國青年報》)
位偏質劣配套少保障房初現“貧民窟”隱患
北京市民小陳七年前在北京西南片以4200元/平方米的價格買了套80平方米的經濟適用房,雖然處于西南三環之內,但交通并不便捷,“別說地鐵,直到現在整個小區附近只有一輛公交車經過,到最近的地鐵站陶然亭站都要換乘兩輛公交車。”小陳告訴記者。
七年過去了,交通狀況依舊。除此之外,小區綠化率低、附近沒有成熟的商場、醫院甚至學校。“最重要的是,附近沒有好的小學,這讓我們非常擔憂孩子今后的教育問題。”小陳的妻子憂心忡忡地說。
像小陳這樣住上了保障房卻得不到完善“保障”的不在少數。業內專家認為,如果面向中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性住房在交通和商業設施上配套不完善,很容易引發都市“貧民窟”的現象。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嚴金明表示,由于城中心很難找到土地,拆遷成本比較高,所以保障性住房很多情況都建在城外或是郊區。“基于區位的遙遠,周邊配套都不健全是個客觀存在的情況。”
有專家認為,“貧富混居”和“成片開發”均不是解決低收入群體住房保障問題的好辦法,不妨考慮“小片開發、集中居住、分散布局”的思路,既能夠保障低收入群體的基本住房問題,又能防止由于低收入群體居住規模過大和過于集中而產生的社會問題爆發。(摘自2010年12月4日《經濟參考報》)
極端事件折射社會暴戾心理 利益分配失衡致扭曲
“我有的是錢,我打死你們,我包錢給你們!”這句話出自一名穿警服、駕駛紅色馬自達轎車的男子之口,這名男子在駕車撞倒一位老人后,不僅不道歉,反而對老人及其女兒大打出手,引起上千民眾圍觀。同一天晚上,河南省洛寧縣郵政局局長駕車連撞5人之后欲逃走,同樣引得上千人圍觀。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夏學鑾表示,社會上一些極端事件的出現,無疑潛伏著巨大的、未知的、綜合的社會心理危機,這些極端事件雖是極少數,但在社會學上已不再是單純的社會治安問題或孤立的犯罪現象,它在更深層的意義上折射出,在今天的社會情感和社會心理版圖上,出現了一個呈畸形走勢的暴戾心理。有專家認為,當前社會心理的畸形發展,除了體現為極端暴力行為外,還存在一些極端的炫富嫌貧、仇富等心理。暴戾心理和炫富心理則是一對孿生兄弟:一個炫耀財富,一個炫耀武力,都是人文素質缺失的表現。此外,由于公眾判斷是非、價值標準的迷失,導致忌妒心理泛濫成災,繼而發展成仇富、仇官、仇才、仇精英等極端的心理形式。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俊海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這種情況的出現與整體上價值觀的多元化有關,因此產生了諸多心理沖突。此外,利益分配不均衡、收入差距拉大,特別是一些弱勢人群的利益訴求沒有得到滿足,這些情況都會導致心理疾病的發生。
劉俊海說,作為構建和諧社會的戰略部署,從法律上保障社會心理調適系統的建立非常重要。(摘自2010年12月8日《法制日報》)
新版《辭海》為何剔除“父母官”
老的《辭海》及新版《辭源》,都有“父母官”詞目,但解釋得并不完全,沒有明確指出“父母官”究竟源于何時、盛于何時、歷史演變,引證也有孤寡欠足之嫌。
東漢光武帝劉
秀建武七年(公元31年),杜詩為南陽太守,深受百姓愛戴,百姓將之與前代的召信臣相比,于是就有了“前有召父,后有杜母”之說,“父母官”一詞即源于此。這時“父母”一詞已有了地方官的含義,自此廣傳后世。稱官為“父母官”,盛于明朝,風行天下,是明中葉以后的事。
父母官兼具領導與愛護兩種特點:“為民做主”與“愛民如子”。在漢語中,“父母官”還有一種用法,就是指稱“家鄉地方官”。朝廷命官為避嫌,常要離開家鄉異地為官。朝中的大官,極少有祖籍在京城,大多數父母都在京都外的地方。這些官對家鄉官也稱“父母官”。“父母官”的兩種含義、所稱適用對象雖然都是地方官,用法上卻有講究:前者是百姓對長官的稱謂,是對長官的一種敬畏和贊譽,后者是朝中高官對比自己地位低得多的地方官的一種尊稱、自謙表示。縣官不如現管,是希望對方對自己的父母親眷有所照應。
“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以后,公民與政府、老百姓與各級領導的關系,成了主人和公仆的關系,成了衣食父母和兒子的關系。鄧小平說:“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他闡明了這種關系。
說“父母官”,不是當官的把老百姓當作父母,而是把自己當作老百姓的父母,這就顛倒了國家政府領導與公民的關系,有著濃厚的封建色彩。“父母官”是“人民公仆”的對立面,實質是封建特權加草民意識形成的政治怪胎。也許這就是新版《辭海》刪除父母官詞目的原因之一吧。
(摘自2010年12月16日《新民晚報》)
童言無忌
如今出來一項調查,說是在全球21個受調查國家中,中國孩子的想象力排名倒數第一。我不懷疑這個調查的真實性。中國孩子這是怎么啦?到底是哪里出了問題?
不少人把板子打在學校、老師身上。一幅漫畫是這樣畫的:孩子進學校前形狀各異,三角形、矩形、方形的都有,從學校出來后一律都成圓的了。這自然是學校師長施以“規矩”的結果。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嘛。師長施以這樣那樣的“規矩”,跟他們自己的經歷分不開。中小學老師年紀不大,沒有經歷過從前的種種政治運動,可他們的師長、師長的師長卻是過來人,往事歷歷在目,前車之鑒啊。還是規規矩矩,按課本、教學大綱授課,不越雷池一步吧。
家長呢,也有自己的“規矩”。想象力畢竟是很虛幻的,量化不出,瞎想什么。平平安安別闖禍,好好讀書,考個好成績,升個好學校,將來找份好職業,有這樣想法的家長不是一個兩個。
我們的孩子是不缺想象力的,你不規范它、壓制它、扼殺它,而是鼓勵它、培育它、釋放它,讓孩子想說什么說什么,不要先看老師、家長或者什么重要人物的臉色,說錯了想錯了也不是闖了什么大禍。老師、家長也不搞師道、家道尊嚴,動輒指責孩子。這不是學校、老師一方的問題,是家長和整個社會都要面對、都要認真關注的問題,積以時日的努力,還愁我們孩子們的想象力張不開翅膀嗎?
撿到錢交給誰——警惕信任危機蠶食傳統美德
日前,鄭州市民李蓮香在一棟居民樓前撿到1000多元錢。她攥著錢,思考著該把這錢交給誰:如果給小區保安,他們私吞了怎么辦?如果給物業公司,他們不給失主怎么辦?再說,他們又怎么知道誰是失主?“失主”是不是來冒領的?最后,她把錢交到報社,希望失主看到報紙來領錢。
撿到錢你會交給誰?市民李明說,現在撿到錢物不知交給誰好了。如果不是撿到一筆大額財物,很多人不太愿意跑去派出所。長期以來,“撿到東西要交公”是一個模糊的規則,“公”是什么?學生把撿到的硬幣交給老師,認為老師就是“公”;有人把撿到的錢包交給保安,保安就是“公”。至于交給派出所或路邊的民警,很多市民也覺得“不安全”,因為他們從來沒見過派出所發布現金招領信息。
為此,有市民建議,應該建立健全規范的招領機構和相應機制,一方面,可以通過多種渠道,發布招領信息,為失主去尋物提供方便;另一方面,給錢或者嘉獎,保護拾金不昧者的善心。(摘自2010年12月14日《東方今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