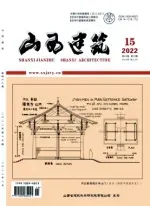論我國城市更新中的文化保護策略
余 俊
1 我國城市更新歷程回顧
建國以來,我國城市更新發展歷程根據目標和內容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
1.1 第一階段:建國初期至20世紀90年代
本階段為以局部危房改造、基礎設施建設為主要目標內容的小規模形體更新階段。建國初至改革開放時期,由于國內特定的社會經濟環境,我國城市的建設和發展是在政策和政府的全面干預下,按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運作的。城市建設以生產性建設為主,舊城更新在“充分利用,逐步改造”的政策下只是局部、小規模的進行危房改造和一些基礎設施建設。
隨著工業建設刺激下的城市逐漸壯大,城市職工住房不足問題日益突出,20世紀70年代后期,各城市紛紛修建住宅,當時主要采取從老城邊緣向中心指向的“填空補實”的方式,進行了一系列標準偏低、配套不全、侵占綠地、破壞歷史文化環境的城市建設,形成獨特的內舊外新的城市空間景觀。改革開放以來至90年代初期,市場經濟體制發育,社會經濟環境的改善為城市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但是計劃經濟發展思想仍然貫徹了城市發展建設基本過程,中國城市更新處于“掙扎停滯”“欲新不能”的特殊時期。這一時期我國城市建設“重生產、輕生活”的思路有所改變,非生產性建設的投資比例逐年上升,采用“拆一建多”的開發方式,無意間破壞了城市的肌理,使城市失去特色。
1.2 第二階段:20世紀90年代以后至今
本階段為在多樣性動力機制推動下逐漸朝向以包括物質性更新、空間功能結構調整、人文環境優化等社會、經濟、文化內容的多目標、快速更新階段。20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漸完善和確立,整個社會政治經濟環境處于大改革的轉型期。社會環境逐漸寬松、地方政府利益主體的逐漸確立、國民經濟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對生存環境要求的提高、大規模的新區建設等等為城市更新提供了較大的社會支持、承受空間和城市物質承接空間。基于此種背景,90年代在更新理論和實踐上都有較大突破,各地城市進行了大規模、快速化城市更新,特別是對一直缺乏更新的城市中心區,更新的規模和力度更大。
這一時期雖然城市空間職能結構、環境等問題得到一些改善,但也產生了大量負面影響。
2 我國城市更新中的文化喪失問題
2.1 領導者和規劃師的認識誤區造成“千城一面”的尷尬局面
一些城市的領導者、管理者對舊城的價值、地位缺乏起碼的認識,對當今所謂“現代化城市”的內涵理解片面。在其眼中的舊城區是“亂、落后、有礙觀感”的代名詞,把舊城區看成現代化風貌的最大障礙。再加上在狹隘的政績觀和急于“舊貌換新顏”的心理驅使,采取商業化運作模式,大規模推倒重建的方式進行舊城改造。和諧、有機、充滿活力、風貌獨特的舊城區代之為“新建筑排排座,高樓林立”的“現代化景觀”。致使原住居民被搬遷、人文社會網絡被破壞、人氣活力喪失、歷代傳承并形成強烈認知的空間特質與肌理被抹殺。最終鑄成地域特色缺失、“千城一面”的惡果。另外,有些規劃設計者自身缺乏關于舊城更新的理論和方法,心境浮躁。規劃設計中把問題簡單化,套用一般區域的規劃設計模式,完成控規或修規的內容即可,而舊城區深層次問題未能涉及,結果是“千城一面”的助推劑。
2.2 舊城區傳統形態和發展格局遭到嚴重破壞
舊城區都有著其特有的肌理和格局,它的特質是由城市發展的歷程決定的。其人口遷徙及構成屬性、生活生產方式與習俗等形成了相對穩定的社會網絡,并經歷代傳承形成了一個城市歷史淵源和文化特征。社會文化特征體現在聚居區的物質空間上,如街市、街巷、院落、建筑等,構成特征鮮明的空間肌理和景觀風貌。
我國傳統城市功能的復合性,能夠極大地方便生產、生活,自然地呈現出濃郁的人氣和內在活力,在一定區域內生產生活表現出自給自足的極強的自我造血功能。而改造中大多以治亂為名,不顧舊城區歷代積淀而來的傳統形態,代之以單純、整齊的功能分區;同時肆意拆毀舊城區中原有的建筑物,代之以粗糙的仿古建筑或者干脆為現代建筑,城市特色蕩然無存。除此之外,大規模、高強度的舊城更新使得舊城區涌入了大量的機動車交通,全新的為機動車服務的方格式道路網徹底打亂了舊城區的城市肌理。
2.3 舊城更新被等同于商業開發,原住民利益淪喪
舊城傳統社區社會經濟網絡的節點是建立在平面舊式低層街坊基礎上,與現代新型居住小區的高密度、高容積率相比相當不經濟,維護式的更新使房地產開發企業根本無利潤可言,因此,開發商多傾向于推倒后高密度重建。
另一方面,城市舊區通常占據著市中心區邊緣的有利區位,隨著城市功能的提升及用地功能的調整與置換,市中心區“退二進三”政策的實施,越來越多的舊區地段被拆建成大型商業設施、辦公樓、高檔公寓及休閑娛樂場所。這種舊城結構性調整的結果經常是以舊城居民失去原家園為代價。
單一的改造目標和片面追求商業功能,致使舊城中的原住民幾乎全部外遷。
在我國舊城更新的歷程中,原住民長期處于極度弱勢的狀態,根本沒有話語權。他們面臨著種種困境,如家園的缺失、謀生環境的消失和社會網絡的斷裂等。
3 城市更新中的文化保護策略
3.1 提高認識,深入發掘和廣泛認知城市文化特色
作為城市的領導者,應該充分的認識到,城市文化特色是城市經濟社會實現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寶貴資源和不竭動力。我們應該站在戰略的角度看待文化資源保護問題,正確處理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文化遺產保護問題,避免把文化資源視為“包袱”的短視行為。
城市文化的延續在于對原有的文化特色自覺地加以保護和繼承。城市文化特色不外乎民族特色、歷史特色和風情特色等幾個方面。挖掘舊城的歷史文化特色時,可通過挖掘歷史事件、名人傳說、文物遺跡等,采用集錦式手法,新建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建筑,納入城市文化整體發展框架。
當然,舊城的文化資源一般都是相當豐富的,應吸取精華,去其糟粕,善于從古代杰出人物中、彪炳千秋的事例中吸取營養,做到古為今用。
3.2 尊重舊城傳統格局及肌理,做到“有機更新”
“有機更新”理論是吳良鏞先生提出的,他認為從城市到建筑、從整體到局部,像生物體一樣是有機關聯和諧共處的,城市建設必須順應原有城市結構,遵從其內在的秩序和規律。
“保護與發展”不是消極地維護現狀,這樣保護不好也保持不了;相反,在“保護與發展”矛盾中應持積極態度,即“以發展求保護”。這就要求我們正確處理好保護與更新之間的關系。
與文物建筑不同,被保護的傳統城鎮體現的是具有歷史文化風貌、適合現代生活要求的建筑環境氛圍。真正應該保護的是建筑的形式、環境的尺度、城鎮歷史形成的道路結構和在街區中能作為文物建筑的建筑單體或群體,即城鎮的形態特征。
保護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將人為破壞了的城鎮形態進行復原,將人為割裂了的城鎮形態進行修補,將人力篡改了的建筑進行還原。而這一切都將是更新的重要內容。沒有更新,自然之手也將使傳統城鎮在歷史的長河中早早地消失殆盡。更新的意義還在于使傳統城鎮的生活常新不衰。基礎設施的更新、建筑功能的更新、居住質量的更新、生活方式的更新這一切是城鎮發展永恒的主題之一,也是傳統城鎮的生命所在。
3.3 以人為本,重視城市更新中原住民的利益
1)延承傳統居住空間組織形態,維護舊區社會經濟網絡。要維護舊城住區社會經濟網絡,關鍵是舊區更新過程中應繼承和發展傳統的居住空間組織形態。在歷史街區或非歷史街區但建筑與社會經濟狀況良好的社區中,鼓勵采用小規模方式,進行自助改建和維修,使原有的空間肌理及社會網絡不致被破壞;在危房簡屋區,拆除重建時應注意延承舊區的空間肌理,通過規劃保留歷史形成的社會經濟網絡節點。
2)進行積極的綜合開發,煥發社區活力。我國傳統社區的商住混合模式已被證實是維持社區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支撐。因此,需要倡導一種新型的舊城更新方式,不是簡單地大拆大建,盲目地以大型商業、辦公樓、高檔住宅等設施取代原來小型多樣化的商業空間以及傳統的商業與居住結合的舊住區,而是要進行積極有效的綜合開發,維護舊城區多種經營的商業氛圍,煥發舊城區的生機與活力。
3)建立面向原住民的社會保護機制。我國大多數低收入原住民對社區的依賴性非常強烈,要維護舊區的社會經濟網絡,必須對舊城住區小規模的自建行為給予政策、技術支持,或保證舊區更新后有一定數量的社區原居民回遷。而要想維持回遷率,必須保證居民的經濟能力要能夠負擔得起重建后的新住宅。政府可以采用扶助的福利性工程為主要手段,通過各種政策傾斜、經濟稅收優惠來鼓勵開發企業投資舊城更新,改建危舊房屋,通過相關的法規來保證更新后的社區中有一定比例的原住民。
4 結語
我們應該以一種聯系的、發展的、全面的眼光來看待城市的更新與保護,而不應孤立的、靜止的、片面的就事論事、形而上學。城市的更新不是簡單的推倒重建,而城市的保護也不是把所謂的“保護區”看成一個與周邊毫無聯系的孤島,將其機械的從整個城市的有機組合中抽離。我們應正確處理好保護、利用與發展、更新的關系,尊重城市的文化特色,充分挖掘城市文脈,讓傳統的舊城在新時代的潮流中繼續散發其獨有的光輝。
[1]陽建強.中國城市更新的現況、特征及趨向[J].城市規劃,2000(5):20-22.
[2]黃亞平,王 敏.舊城更新中低收入居民利益的維護[J].城市問題,2004(15):27-30.
[3]李建波,張京祥.中西方城市更新演化比較研究[J].城市問題,2003(23):58-60.
[4]王富強,周旭丹.風貌建筑保護區改造更新中意象元素研究[J].山西建筑,2010,36(13):3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