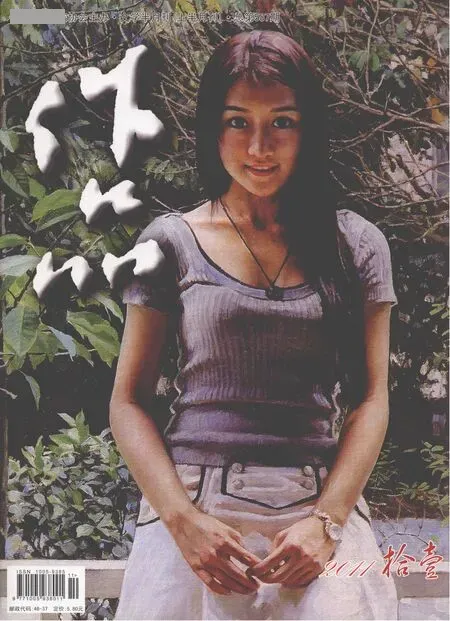現實一種
◎楊 遙

遠方一直吸引我。
在我并不復雜的經歷中,有一段記憶深刻。那是1998年,我陷入一場無望的愛情,我以為這段愛情會像魔鬼的詛咒一樣使我痛苦一輩子,甚至我覺得自己不可能擺脫它。但是這一年的正月初,我的父親被檢查出得了一場大病。情人節的那天,我陪著父親在太原的醫院開始漫長的看病生活。在面對醫院的一張張病危通知單和一個個撒手人寰的病人,愛情這種痛苦一下變得輕飄飄的,我甚至來不及去想它。當父親從醫院出院的那一天,我只是想以后怎樣早日還清父親看病欠下的巨大債務。那個使我痛苦的女孩,再也不在我的生活中占有位置了。由此我得出一個結論,擺脫一種痛苦的最有效方式是陷入一種更大的痛苦。我開始經常思考生與死的問題。
十幾年來,我經歷了幾次親人、朋友、同學的死亡。2002年的一個中午,我握著病了一年多的母親的手,看見她眼睛翻個白眼,喉嚨“咯噔”響了一下,她就永遠地離開我了。馬上覺得死亡離自己如此之近。在我出生的那個村子的一條巷子里,挨家挨戶數過去,竟然每一家都有非正常死亡的人。死亡一下變成非常熟悉和容易的事情。
因為處境,也因為性格,我和現實的關系有些緊張。對于許多像我這樣出生在農村,上了一個三流的大學,又不甘平庸生活的人,在這個時代,可能多多少少都有這種感覺。而且,我對人和事都想得比較理想,在現實面前就會感覺更慘,所以我常常會陷入巨大的絕望中不能自拔。
小說為我打開了一條出路,我經常在小說中為主人公設置種種可能。
這篇小說我想寫一個人對生活完全絕望之后,會怎樣?死掉是非常容易的,但死掉又是太簡單的,美的震撼和對他人的憐憫,或許會使一個人忘掉自己,忘掉一切。可是生活又是多面的,復雜的,你對別人同情、憐憫,伸出援助之手,別人會不會接受,或者方式恰當不恰當?我追問這個問題時,小說又向我呈現出另一種可能,A不需要的,可能B非常需要。但是B需要,就會得到嗎?或者說,給誰的就是給誰的。
我開始寫這篇小說。桂林和越南的美景不時出現在我的腦海,對于我這樣一個生活在北方小城的人來說,南方異域風情的那種巨大誘惑很難抵制,而且我多少還有一些炫耀的虛榮心。我像一個捕撈珍珠的人,不斷砍斷水中的海草,一次次深入下去,我希望自己能捕撈一只巨大的珍珠,而不是收獲一大捆美麗的海草。我在與自己的搏斗中,慢慢潛下去……
這篇小說寫完的時候,我把它放了幾天開始修改。修改完之后感覺不踏實,繼續放著。直到兩個月之后,我又重新修改它。這兩個月,我離開自己生活的小城,到魯迅文學院來學習。生活環境和接觸對象都發生了變化,當我再次拿起它時,它里面有些東西感動和吸引了我,我仔細打磨它,假如它是一顆珍珠,我愿意讓它再光滑些,璀璨些。我把那些多余的冗雜的東西刪去,讓它更純粹些,讓它的光慢慢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