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當代詩人素描⑧
蘇歷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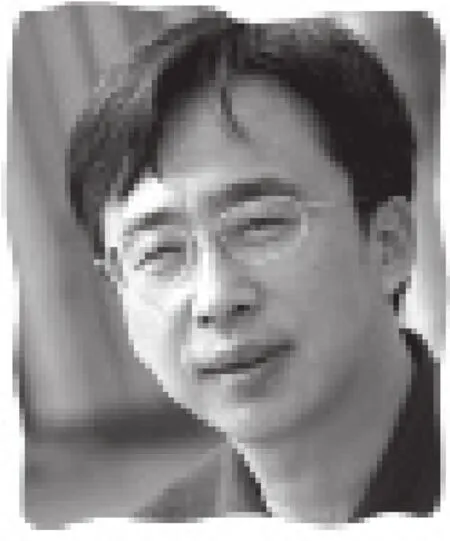
山東日照圣谷山茶場 綠茶/紅茶 特約刊登
許德民:一個生命的失蹤不是新聞
2002年春天,應大學摯友之妻邀請,我去上海參加《生命周刊》在橫山島舉辦的文學筆會。之前我已知道,她聘請的主編鄭潔,就是當年華東師大的學院詩人,也是復旦大學學院詩歌的領軍人物許德民的夫人。所謂筆會其實就是老朋友的聚會,嚴力、許德民、默默、張遠山、李占剛等人一同前往,在長江口的度假村里輕松地度過海派的周末。
我在大學時代就知道許德民和他的成名之作《紫色的海星星》,在學院詩歌昌盛的年代,許德民等人把復旦大學的學院詩歌提升到最高處,許德民和復旦大學的《詩耕地》曾是當時出道詩人耳熟能詳的詩歌符號。之后他與孫曉剛、李彬勇和張小波大打“城市詩”的旗號,曾橫行于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中國詩壇。我在《星星》詩刊曾談到80年代大學生詩潮的盛況,他給我留言時補充到:“80年代初期,也就是改革開放的最初幾年,其實整個主流都呈現(xiàn)一種開放的姿態(tài),解放思想成為每一個行業(yè)的關鍵詞……誕生于那個時代的學院派詩人,基本上是整個時代的詩歌精英……那個時代,在大學里組織社團,組織詩歌朗誦會,呼風喚雨,席卷整個校園,波及全國各大學,參加者幾乎遍及每一個寢室,詩歌真正成為了那個時代的心聲。詩歌是心靈革命的載體,也是承載社會和個人命運的渡船。”
許德民和我想象的不大一樣,我以為他的面孔應該清瘦而堅毅,而見到他后發(fā)現(xiàn)他的臉龐富態(tài)而平和。隨著80年代的落幕,許德民的名字迅速消隱于詩界。交談中我知道他已把藝術的重點轉移到繪畫上,后來我曾去過他在紹興路上的角度抽象畫廊,里面陳列著他近年來的繪畫作品。詩與畫的銜接或許是一個詩人自然的選擇,用畫筆作畫似乎比用筆寫詩更能直接表現(xiàn)個人的思想。
本以為許德民不會再染指詩歌,但在復旦大學百年校慶時,他浮出水面,召集散落在各個領域的復旦詩人,個人拿出價值10萬元的6幅畫,不僅向母校獻禮一座“復旦詩魂”銅雕,還主編了16本《復旦詩派詩歌系列》。“那是一份初戀的感覺,跟隨著記憶”,他興致勃勃地召集歷屆詩社成員重新開始寫詩,并熱衷于復旦VS北大——中國學院派詩歌高峰對決之活動。在我看來,大學生詩潮興盛于80年代,也消逝于80年代,我們可以非常動情地懷念理想主義年代,任何重現(xiàn)的愿望似乎只是一種奢望,畢竟時空轉換,正像許德民自己所言:“在80年代初期,大多數校園詩人都是業(yè)余的,只是詩歌愛好者,而非職業(yè)詩人。學院生活中更重要的事情是專業(yè)學習和前途設計,因此,復旦很多有才華的校園詩人在離開學校后往往就離開了詩歌創(chuàng)作……詩歌只是他們人生途中的班車,抵達目的地,就跳了下去,不再回來。即使留守的詩人,離開校園以后,堅持寫詩只是因為詩歌是一種至愛,是自己的生命方式,發(fā)表與否已經不重要了……在他們的骨子里,詩歌已經儼然成為他們生命的靈魂。即使他們從此不再寫詩、讀詩,但他們的呼吸和心跳的旋律和節(jié)奏都是詩的,都是無法改變的詩的鄉(xiāng)音。”
他的夫人鄭潔曾說:“許德民不是一個善于放過自己的人,不放過自己在時間上的松懈,更重要的是,他不善于放過自己的創(chuàng)造力。”現(xiàn)在許德民致力于抽象詩的探索,他認為詩歌是文學中最接近藝術的文字形式,如果說藝術的最高境界是抽象境界的話,那么詩的抽象就是文字形式的抽象。他對抽象詩的定義是:非語法、非邏輯、非經驗的抽象字組構成形式。抽象詩從字開始,到字組為止。
我無法理解許德民抽象詩的內在意義,但我尊重他執(zhí)著的藝術探索。比較而言我還是懷念他的非抽象詩:“即便是威嚴的大海/也無力保護自己的孩子/在浩淼波濤中/一個生命的失蹤已不是新聞了/我看見游覽區(qū)的小籃子里/海星星被標價出售”。海星星應該生活在浩瀚的海洋之中,它一旦被遺留在退潮的海灘上,逃脫不了僵死的命運,必然成為一種飾品,可能還悲哀地成為一種廉價的飾品。
宋琳:手松開一片死光
潘洗塵約我前往他的住所喝茶,并說宋琳也來。直到把茶喝淡,門鈴才響起來,潘洗塵說:宋小慢來啦!
宋琳之慢,并不是不守時,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他的慢板態(tài)度的體現(xiàn)。所謂慢板生活就是一種恬淡、舒緩而又愜意的生活狀態(tài),并試圖以一種新鮮、啟發(fā)、知性與浪漫的姿態(tài)為基調,用一種接近慢板的節(jié)奏展示出現(xiàn)代人在物質生活的表層下對精神世界的探求。
在中國詩壇上,宋琳是一個特別的名字,他起源于閩東山地,在上海的中山北路度過相對悠閑的時光,上世紀80年代末他到達人民廣場并從那里離開人們的視野。我再聽到他的消息時,他已旅居法國,之后我在《今天》雜志上終于看到他作為編者而名在其中。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曾被派往上海工作,其中一個實習地點就是在華東師大對面的盤灣里貨站,即蘇州河邊的一個小碼頭。那時我有大把的空閑時間,經常去華東師大找陳鳴華等人聊天。華東師大夏雨島詩社是當年中國學院詩歌的亮點,陳鳴華是我相交甚久的朋友,他當時擔任夏雨島詩社的掌門,這個矮個子上海人中規(guī)中矩,沉穩(wěn)且老練。一天他說應該去見見宋琳,我便隨著他敲開宋琳的門,那是我第一次見到留校任教的宋琳。
宋琳清秀英俊,儒雅安靜,他的一手好詩,在80年代大學生詩潮中顯得與眾不同。宋琳早年曾經說過,“詩人的藝術行為不僅是一種自覺運動,而且是一種精神的本能運動。這意味著,只有把良心、道義、責任以及審美傾向等意識中的自覺轉化成本能,才能進入詩的狀態(tài)。”在校園詩人得意于青春期寫作的勢頭里,宋琳是大學生詩人中其作品最早發(fā)生裂變的詩人之一,當年讀埃利蒂斯《勇士的睡眠》曾令他震撼,在《空白》一詩中他寫出炫目的詩句:“所有去過的地方/城市的停尸房里有我的熟人/綽約若處子/可憐的腳涂滿了泥巴手松開一片死光”。
與宋琳見過不久,潘洗塵從東北來到上海進行詩歌串聯(lián),陳鳴華為其組織了專場詩歌朗誦會,而我因故晚到,只能在爆滿的教室外面聆聽激昂的朗誦。會后,宋琳、張小波、徐芳、陳鳴華、傅亮和我,陪同風塵仆仆的潘洗塵來到傳說中的夏雨島上。之后大家各奔東西,宋琳在華東師大的課堂上教書育人,寫出大量現(xiàn)代主義詩篇。
20年后,在2004年北大詩歌中心成立的儀式上,我偶遇宋琳,看到當年一張清秀的面孔已浸染滄桑。他不僅旅居過法國,還曾在阿根廷、新加坡等地長住,期間所經歷的萬事我們無法清楚地了解,但在時空轉換的復雜經歷里,他的喜悅和磨難無疑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他的性情似乎未變,慢板的語態(tài)和慢板的笑容令我頓感歲月催人老,白發(fā)雙鬢生,只是他那雙智慧的眼睛仍舊放射著特有的光芒。2007年我在沈陽小住時,曾結合當時的一項工作舉辦過一場理想詩會,那時我才得知宋琳執(zhí)教于沈陽的一所大學,每月都由北京乘坐夜行火車來沈陽輔導文學系的學生。遺憾的是,活動期間不是他在沈陽教書的檔期。
宋琳在國內始終堅守于教師的崗位。人生有些事情永遠是一種無奈,或是命中注定,但教師這種職業(yè)顯然適合于他。他奔走于京沈兩地,每次車輪和鐵軌的撞擊聲中,都將充分享受自由的歡愉。現(xiàn)在他不僅僅限于使用詩歌的語言,繪畫的嘗試是他釋放思想的另一種更為直接的自由方式。
宋琳說,中國詩人都喜歡往中心擠,可擠到中心一看,里面是空的。在我的印象里,宋琳是始終閃身于中心最遠的地方,卻又被人時時記起的詩人。在勢頭猛烈的80年代,他從不張揚,以至于名字常被人搞錯。宋琳之安靜溫和是一貫的,但他心底的火焰可以熔化時間的鐵鏈,有些大膽的想法超出年齡的羈絆,令我不由得感覺到,時間可以致殘我們的肉身,但決不能衰老我們的心靈。心靈一旦衰老,對于我們來說,就等于死亡已經到來。這是20年后再見宋琳時的瞬間感悟。
宋琳之所以總能頂風冒雪趕來喝茶,最重要的原因當然是老友的情誼和相聚的放松,但另一個原因是他喜歡空間的自由。在外面可以酌量暢飲,或者肆無忌憚地抽煙,直到催促的電話在午夜響起,我們會故意大聲說,走啦走啦,以便更好地維護宋琳自青年時代不變的紳士形象。
交響樂中一般有四個樂章,每章速度各異,而尤以慢板樂章最為動人。宋琳是中國詩歌動人的慢板,他的詩和他的人,一直都在放慢速度,或節(jié)制速度,在藝術和現(xiàn)實中保持一種平衡。每次離開換鞋時,宋琳還會點上一支煙,不慌不忙地延長著告別的時間,或者說是延長自由的時間。
張小波:登山者的預備手杖
2009年4月底的一天晚上,張小波談起《十月》雜志約他詩稿的事情,這讓我心中平生出一種期待,并不是指望他的詩作能在泛濫的詩海中不同凡響,而是這個舉動會讓同時代寫作和出道的人有一種特殊的溫暖感覺。在吉林大學編輯《北極星》雜志時,我們曾創(chuàng)辦過“遙遠的星光”欄目,專門發(fā)表校外詩人的作品。張小波寄來《多夢時節(jié)》等詩作,他奇妙的想象和優(yōu)美的詩句始終被我記得:“無邊無際的寂寞吞噬群山和落日/那么,讓我們聚集起來/騷動起來/登山者在馬蹄形山谷里/留下一根預備手杖/我們莊嚴地接過/探險于一個盛產黃金的世界”。
當年朦朧詩之所以能夠在詩壇上迅速傳播,其中相當重要的原因就是和大學生詩歌的出現(xiàn)和繁榮息息相關。那時詩歌界對朦朧詩的崛起,存在著保守勢力惡毒的圍剿和傳統(tǒng)勢力的攻擊,而對朦朧詩最強有力的理論支持就是來自學院。除了謝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孫紹振的《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之外,在校學生徐敬亞撰寫的《崛起的詩群》,更是激情澎湃,其沖擊力和殺傷力都是從前未曾有過的。一大批優(yōu)秀的校園詩人,他們的生活經歷和朦朧詩的主要人物相似或接近,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擔當起傳承的責任,并各具特點地彌補了朦朧詩的某些局限。備受非議的朦朧詩在中國詩壇上順利落地生根,與學院詩歌的出現(xiàn)和空前發(fā)展密不可分。上海因為許德民、孫曉剛、李彬勇、邵璞、張真、卓松盛、傅亮、宋琳、張小波、李其鋼、于奎潮、徐芳、張黎明、林錫潛、于榮健、鄭潔、陳鳴華、陳東東、王寅、陸憶敏等人的存在,在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中擁有舉足輕重的位置。而張小波的詩歌更多是表現(xiàn)身處現(xiàn)代都市的復雜心態(tài),他以零碎拼貼的城市意象,新奇雜陳的詞匯,折射出人在工業(yè)化進程中的焦慮情緒,其機智清新的詩歌語言突破傳統(tǒng)詩歌的束縛,成為當年大學生詩歌令人矚目的潮頭人物。
在日本留學時,恰逢《中國可以說不》日文版出版發(fā)行,我便買了一本。當時我并不知道本書的策劃人張藏藏就是張小波,后來我才知道這本書是張小波和他的一幫朋友做出來的。張小波說,從1989年到1994年,中國青年在中美關系問題上的心理發(fā)生了微妙變化,如何維護國家利益應該成為首先考慮的問題,這就是《中國可以說不》出籠的動因。
關于張小波書商生涯的傳說存在眾多版本,其實這些并不重要,我只知道他的共和聯(lián)動圖書公司每年圖書銷售碼洋都超過億元。前幾天讀到程寶林拷問張小波的文章,對他新近策劃的《中國不高興》一書提出質疑,并上升到病態(tài)的民族主義高度進行善意的批評。對此書我沒有深入閱讀,無法表明自己的意見,但有一點必須清楚,張小波不僅僅是一個曾經的詩人,更是一個緊盯市場需求的圖書商人,從立場上就不存在爭論的前提。就像刀可以切菜,也可以殺人,生產刀具的人更關心刀具帶來的利潤。
“我不后悔進入出版行業(yè),”談及從詩人到出版人的轉變時,張小波強調,“做公司生存是本,一定要做大做強。”盡管張小波骨子里一直充滿創(chuàng)作的渴望和對精神世界的探索,但他清醒地認識到,在商言商,自己首先要把自己的圖書出版事業(yè)向前推進。張小波至今每年都會幫一些詩人出版詩集,“我一直努力在商業(yè)和理想之間尋找一種平衡。公司做大之后,讓那些優(yōu)秀的詩人和快被社會遺忘的作家通過文本保存的形式流傳他們的作品,這樣才不枉我曾經有過的理想。”這或許是他與詩歌若隱若現(xiàn)的情結聯(lián)系。
有人曾說,上個世紀80年代,城市逐步進入經濟發(fā)展的快行軌道,華東師大地處上海,有七成以上的學生來自異地,他們要在這里度過他們人生中最重要的轉型期,可以說,“外省青年”對都市的感性觸摸,訴諸直覺甚至官能上的某種隔膜與排斥感,成為自此以后校園詩歌寫作的一大主旨,即“城市與人”。我同意這樣的判斷,來自于江蘇鎮(zhèn)江的張小波正是在上海的都市文化里產生過青春期的眩暈,他曾寫過《這么多雨披》一詩,這只是都市生活中的一個日常場景,卻觸動過這位外省青年敏感而新奇的心靈。
張小波出版過小說集《重現(xiàn)之光》,其中怪異詭譎而才情蓋世的文字,連同他散落于各種選本之外的詩歌,都驗證過他作為詩人、作家之優(yōu)秀。現(xiàn)實生活中,他的圖書出版商身份或許更讓他駕輕就熟,那就響應市場要求,多出書、出好書,等到徹底厭倦名車美女再回到本真的創(chuàng)作之中吧。我們離老去尚有距離,萬事都來得及,寫作就更來得及。
傅亮:欲望號街車
一直到現(xiàn)在,我依然保留著大學以來的所有詩歌通信,其中與復旦大學傅亮、華東師大陳鳴華等人的通信非常頻繁。當年剛到上海,我即按照傅亮信中提供的交通路線,去復旦大學看望這位神交已久卻未謀面的朋友。傅亮當時正值畢業(yè)前夕,那天他不在校,他的同學朱光甫接待我,一起到校外的小攤上吃陽春面,并安排我當晚睡在傅亮的床鋪上。
“請不要阻止我心靈的徜徉,不要指責我步履的奔放!/既然是陽光明媚的早晨,我們的思想就不該有任何掩藏。”傅亮出道較早,大學畢業(yè)之前已寫下《我們的秋天沒有眼淚》《欲望號街車》等風靡校園的詩篇。傅亮是個非常率真的上海人,交談時偶有結巴的嫌疑,但進入朗誦狀態(tài),猶如行云流水,流暢且極富感染力和殺傷力。他擔任復旦詩社社長期間,可能是與華東師大夏雨詩社聯(lián)系最為密切的時間,他和陳鳴華經常混在一起,共同沐浴在詩歌的光環(huán)里。我在上海的一年里,經常與他們倆見面,至今我還清晰地記得,在大排檔里,傅亮、陳鳴華和我展開愛情的討論,觀點相左時,傅亮起急,說:“別、別他媽的說了,不、不許再提某某某!”陳鳴華顯得中規(guī)中矩,沉穩(wěn)老練,具備文化官員的綜合素質,現(xiàn)在擔任上海某出版社的社長,每次見面時肯定要說,打電話把傅亮喊來。
經歷過光輝,承受過沉寂,品嘗過甜蜜,體味過無奈。在一家媒體專訪中,他們詳細介紹了傅亮的生活軌跡,把他描述為從校園怪杰到塵世的飄客,經歷了逃課的學生、校刊主編、夜總會老板、服裝節(jié)攤主、游戲節(jié)目策劃、旅行社經理等不同角色。傅亮說,詩需要創(chuàng)造性,所以他在生活中從不喜歡重復。
離開上海后大家各自忙碌,我選擇留學海外,他似乎也徹底離開詩歌。等再見傅亮時,是1997年留學回國在上海期間趕上他的婚禮。他是出了圍城再進圍城。婚禮結束后,我和陳鳴華、韓國強一起在衡山路上的保齡球館滾了一夜的保齡球。那之后,連陳鳴華也難見傅亮,當年的詩歌英雄消隱于民間。
當年傅亮最為自豪的就是成功地把復旦詩刊《詩耕地》從油印升華到鉛印,這本雜志曾走出許德民、孫曉剛、李彬勇、邵濮、張真、卓松盛等眾多的學院詩人。之后我在上海分別見過韓博和任曉雯、在北京分別見過邵勉力和陳先發(fā)等復旦出身的詩人,在他們的記憶里是否還留存詩耕地的印跡,無從知曉。
當年為了節(jié)省費用,傅亮翻遍小報的廣告,終于在崇明島上聯(lián)系上一家價格低廉的印刷廠,他先坐公交車到碼頭,再乘船去崇明,上島后搭乘工廠的便車,晃上一個多小時才能趕到廠里。當時崇明島并未開發(fā),他必須要住上一晚,窗外有各種鳥類奇怪的叫聲,房間里還會爬進來各種各樣的蟲子。待印刷完成,他把散發(fā)著油墨香味的《詩耕地》裝上卡車,坐上副駕駛座,駛向詩意盎然的復旦。經歷過詩歌興盛時期的詩人總會無限緬懷那個年代,對詩歌被邊緣化的現(xiàn)實多少都會發(fā)出無奈的悲嘆,我想傅亮可能體會尤深。他在那個年代里幾乎瘋狂地投入到學院詩歌的建設中,之后他離開詩歌,或者逃離詩歌,是主動回到生活之中,還是無可奈何地放棄曾經燃燒的夢想,有待于直面印證。在《自行車與五香豆》一詩中,傅亮曾經寫道:“他們說/你們成熟了/我們說/不,我們/老了”。有人說,詩人永遠年輕,說這話的人從未理解過詩人的真諦,試想詩人的內心是何等的豐富,它要承載超過一般人的情感,詩人一出生就已蒼老,否則那些分行之文字無法稱其為詩。
在詩歌的欲望號街車上,傅亮最終把自己趕下車去,雖然我有時在想這個可愛的家伙可能在抽屜里存放著自己的詩稿,但他在公眾視野里徹底逃離了詩,做了詩歌的逃兵。
我總是想起傅亮穿著條絨西服外套的樣子,那時他意氣風發(fā),站在臺上朗誦時,曾經感染過許多人。有時在上海的大街上期待與他不期而遇,又怕他變得面目全非。這個復旦學子,逃跑的時候會想到當年慷慨激昂的演講嗎?同時代的詩人大都回到日常生活之中,這讓堅守者時常倍感寂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