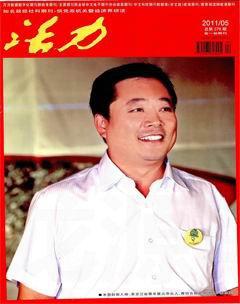淺析文獻紀錄片的功能與使命
高宏飛
紀錄片被譽為人類的“生存之鏡”,但這面鏡子不像新聞那樣稍縱即逝、單薄易碎。它是可以收藏起來傳于后世的。紀錄片的恒久生命力來源于豐厚的歷史價值和文化底蘊。從文化的角度來說,紀錄片是各種影視傳播形態中的“貴族”——是文化含量最高的傳播載體。
那么文獻紀錄片與一般意義的紀錄片有哪些不同呢?單從字眼上說,文獻紀錄片最基本的特征和標準是:具有文獻歷史資料價值的影像作品,是對一個國家時代進程的真實記錄。從更深層次來說,文獻紀錄片需要滿足這樣幾個條件:首先是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其次是有較高的文化價值和藝術價值。文獻紀錄片的三重價值決定了它有如下的品格和特點:一是披沙揀金、清醒理性的歷史深度:二是廣泛而深遠的社會影響力;三是震撼人心的藝術感染力。
在過去的二十年里,我國的文獻紀錄片呈現給我們的正是這樣一面大氣磅礴的“生存之鏡”。從《話說長江》、《望長城》到《毛澤東》、《圓明園》、《大國崛起》,這些不同時期的扛鼎之作,忠實地記錄著我國社會發展進程,反映著社會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的變革,為民族、為國家書寫著一部生動的影像史志。與此同時,社會的發展也推動著文獻紀錄片創作在觀念、內容與形式上的進步與變化,使它逐步由“紀錄時代進程”的宏大使命擴展到對社會深層和歷史細節的深度思考,也讓我們對文獻紀錄片的功能和使命有了更深刻的認識。要完成文獻紀錄片的歷史使命、履行其社會責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處理好以下幾個關系:
一是歷史與現實的關系。文獻紀錄片必須要關照歷史、惠顧現實。這里有兩層含義,首先是拂去歲月的塵沙,還原歷史真實。總結過去,求訓致用,以史為鑒。其次是去偽存真,從歷史的規律性去認識現實實踐中的現象與問題,追尋歷史淵源,鑒往知來,抓住當代社會發展的主流。在這里,歷史是過去的現實,現實是將來的歷史,更進一步地說,歷史是穩定凝結了的現實,現實是流動變化著的歷史。這既是二者之間的聯系,也是區別。說到底,無論還原歷史還是寫真現實,無論是再現歷史風貌還是反映時代精神,關鍵是要樹立一種科學、辨證的歷史觀,即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既不能一相情愿地“厚今薄古”,也不能簡單地“古為今用”。對于歷史與現實關系的把握,決定了文獻紀錄片的生命力。當歷史的規律性、知識性、借鑒性與對整個民族的凝聚性在文獻紀錄片中得以體現時,歷史與現實的關系才是得到了真正準確的理解與詮釋。端正了歷史與現實的關系,文獻紀錄片才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才能經得起人民的檢驗。
二是理性與感性的關系。文獻紀錄片的魅力在于史家的冷靜旁觀與電視的生動演繹。史學的理性與藝術的感性,這看似矛盾的兩種特質,奇妙地結合在一起,構成了文獻紀錄片獨有的風格:揭示規律,一針見血;挖掘人性,絲絲人扣;既能抓住歷史長河的滾滾洪流,又能捕捉到浪花一朵:既不乏思想的深度、理性的剖析,又有細膩的刻畫、生動的描述,理性的思維與感性的表述相得益彰。只有這樣,文獻紀錄片才能真正撼動人心。理性與感性關系的互補,決定了文獻紀錄片的影響力。這需要創作者不僅諳熟歷史規律和電視規律,還要善于將兩種規律緊密結合、并且轉換自如,達到游刃有余的創作佳境,在真實的原則下以充滿力度的客觀深刻和富有質感的真實生動,取得社會效益與收視率的雙贏。
三是雅與俗的關系。從文化的角度說,文獻紀錄片是貴族中的貴族,是主流中的主流。從傳播的角度,文獻紀錄片又是通過大眾傳播工具直接反映社會變遷的文化形態。這說明了一個事實——文獻紀錄片應當是面對大眾的主流文化。它既不是孤芳自賞的陽春白雪,也不是追風覓俗的下里巴人;既不高高在上,也不附炎趨勢。它是對歷史和現實最深入、最直觀的反映和寫照,文獻紀錄片應當是雅俗共賞的。雅與俗的關系,直接決定了文獻紀錄片的格調與品格。文獻紀錄片的創作者保持清醒而冷靜的頭腦,明辨美丑、分清是非,旗幟鮮明、堅守方向,不人云亦云、隨波逐流。
除此之外,文獻紀錄片媒體功能的實現與影響的放大,還需要仰賴文獻紀錄片創作者的文化自覺。文化的自覺是源自內心的使命與責任,也就是心懷天下的憂患意識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過去的二十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社會經濟飛速發展的黃金時代。我們是幸運的,置身一個偉大的變革時代,親歷了中國社會的發展,并且能以文獻紀錄片為載體,忠實地記錄了變革中的中國以及對過往歷史的還原。而不曾間斷的紀錄實踐,也豐富、完善著我們對于文獻紀錄片的認識。讓我們看到了這面精神之鏡折射的光亮是如何驅趕了黑暗,啟迪了大眾的心靈。
盡管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文獻紀錄片的功能各有側重,但有一條原則始終不變,那就是——不媚俗、不趨炎、獨立思考、真實記錄的傳統;以及為時代立傳,為歷史存真的使命。這種神圣的使命與責任最終決定了文獻紀錄片的品格——真實,客觀,深刻,嚴謹。同時也意味著它的創作之路是一條光榮曲折的荊棘路。它與生俱來的歷史使命、深刻的歷史文化底蘊,如同我們頭上的星空與心中的道德一樣神圣而崇高,讓我們永遠為之敬畏。
(編輯永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