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讀互動
編讀互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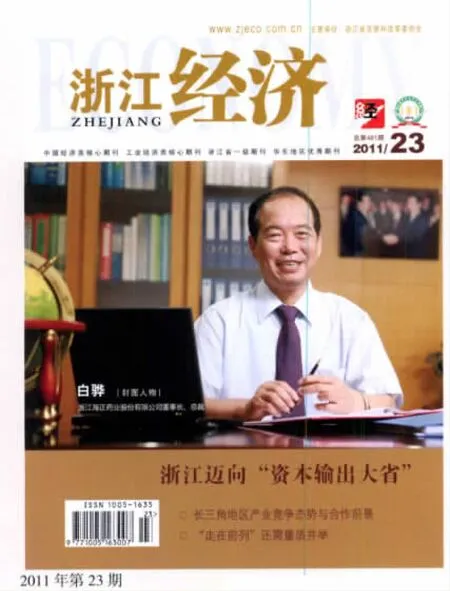
境外投資助推轉型升級
在浙江邁向“資本輸出大省”的新時期,必須從全省經濟轉型升級和可持續發展的全局出發,找準境外投資與浙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舉措的有機結合點,因勢利導,充分發揮境外投資對于經濟結構調整和轉變發展方式的積極作用。
少談些人均,多看點不均
中國社科院日前發布《產業競爭力藍皮書》,稱按照2011年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已經成為中上等收入國家。從數據上看,中國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論斷是可信的,但關鍵是人均中等偏上收入后,有多少人因不均而被人均了呢?在我國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的今天,我們尤其不該忽視,中國仍然有1.5億人生活在極度貧困中,2.3億農民工得不到基本的社會保障……這些證據都提醒我們,綜合財富并不一定代表一般家庭財富。雖然我國人均GDP已超4000美元,但人均可支配收入至今離2000美元仍有相當距離,也就是人均創造的一半以上的GDP,并沒有掌握在公民手中,分配機制的問題不言而喻。
(鄧昌發)
稅收越減越多根源在哪?
2011年“減稅”成為年度稅收關鍵詞。個人所得稅調整、營業稅改增值稅、資源稅改革及車船稅微調,仔細來看,這些稅制變動都透著“減稅”的意向。實際上,“減稅”并不是新鮮話題。早在2004年就開始在全國實施結構性減稅,然而,七年多過去了,無論是企業還是個人,大都沒有感覺到系列減稅所帶來的稅負減輕。目前我國稅負過重,已成為亟須解決的問題。為此,我國要控制總體稅負規模,參考同類國家的稅負,通過立法的方式,硬性規定為GDP的一個比例;同時,更要控制稅收增長速度,譬如,硬性規定每年的稅收增長速度要與GDP同步,以實現政府與企業、個人之間稅收利益的合理分配。
(吳睿鶇)
公益型國企不該拿競爭性薪酬
國企改革未來之路在何方?有觀點認為,國企“只做公益不掙錢”,是一種改革的倒退。這樣的擔心其實早了一點,更應該關心的是,那些被確定為公益型的國企,到底肯不肯做公益。按照國資委的定位,公益型國企“社會效益高于經濟效益”。可現在公益型國企,動不動喊虧本。公益型國企高昂的成本里,難道不包含有高管的競爭性薪酬嗎?國資委既然明確了石油石化、電網、通信服務等領域企業,是公益型服務企業,并且強調“防止企業利用壟斷地位損害公眾的利益”,那就應該對高管的薪酬作出限定。任由國企高管特別是服務型國企高管拿競爭性薪酬,必然加大企業成本,必然傷害公眾利益。
(毛建國)
高速停收費切莫成孤例
上海市建交委日前出臺收費公路清理整改方案,方案提出明年滬嘉高速公路停止收費、停止向市內外車輛收取道路通行費等。一直以來,高速公路免費對國人而言無異于奢望,連取消二級以下公路收費都步履蹣跚。滬嘉高速公路停止收費,打破了高速公路必定是收費公路的“中國式”鐵律。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當政府財力有限時,“貸款修路、收費還貸”模式曾為中國公路建設和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然而,彼一時,此一時,現在收費公路的弊端日益顯現。滬嘉高速公路早已收回投資,按照正在進行的全國收費公路專項清理工作的要求,理應轉為免費公路。只不過,“理應如此”的何止是滬嘉高速公路。
(晏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