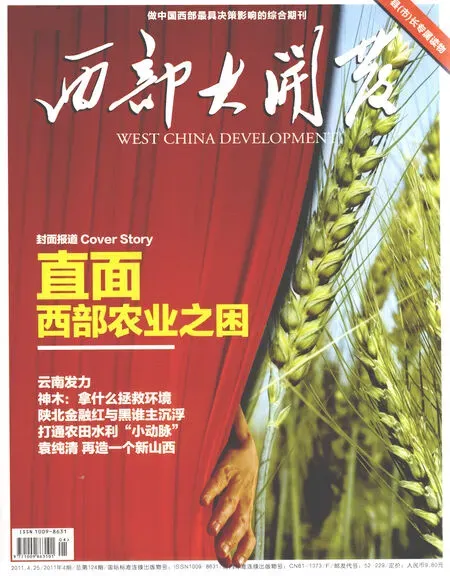看重慶“三進三同”
◎文/世寶
看重慶“三進三同”
◎文/世寶

春日,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張遼(化名)特意抽出些時間,派人把四川美院一個來自貧農家的女生接到重慶市中心的解放碑,請她在星巴克喝了一杯咖啡。
女生剛進大一,從大學城到市中區的公交車費2塊,也覺得奢侈,因此一直待在大學城里從未出行。張遼是重慶一位廳級官員,女生是他在“三進三同”活動中“結窮親”的農戶子女。
張遼從沒想到,在這個國家走向“全面小康”的年代,還有人會為2塊錢的車費發愁,“這讓我深為震驚”。
在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倡導下,重慶的黨政官員從去年3月起全面開展“三進三同”,即讓張遼這樣的官員們進基層、進村子、進農戶,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
“制定這項制度,是為了突破干部與群眾聯系方式的官僚化、聯系渠道的狹窄化、聯系手段的唯物質化,推動機關干部走下高樓、接上地氣,在與群眾同甘共苦中觸及靈魂、錘煉黨性。”重慶市“三進三同”辦公室表示。
當然,和唱紅歌、傳箴言、“紅色衛視”等各種薄熙來式的重慶新政一樣,把25萬官員“趕”下鄉的活動,也引起了各種爭議。
“不要整天圍著富人轉”
九龍坡區委副書記潘平是最早一批“三進三同”的官員。他所到的鄉村巫山縣平河鄉朗子村,位于三峽庫區深處,在那里,部分分散居住的村民連吃水都很困難。
對于官員們的到來,村民們小心翼翼又不冷不熱地接待著。直到有一次,在“同吃”時,潘平把老鄉掉在桌上的一小塊臘肉夾起來吃掉,農家人才認為他真是“自己人”。
這次體驗,讓中青班的學員“非常震撼”。重慶市委黨校教授蘇偉認為,它在處廳領導干部與基層之間,找到了一種最佳的銜接。
這種形式很快得到薄熙來的肯定和推廣。2010年3月,重慶市委下發《關于在全市機關干部中開展密切聯系群眾“三項活動”的意見》,使“三進三同”走入常態化。
“要招商引資,發展經濟,但絕不能嫌貧愛富,整天圍著富人轉,淡忘了黨的宗旨,疏遠了困難群眾。”薄熙來2010年元旦在合川、北碚看望慰問貧困戶時說的一些話,被視為對“三進三同”思路的詮釋。
薄熙來說,重慶縮小貧富差距的壓力很大。當干部的要“結窮親”,多交幾個窮朋友,多到貧困戶去走一走,更多地了解群眾的實際困難,要做到“設身處地”,“感同身受”,與他們心連心。
根據這一要求,重慶市委要求全市機關干部每年一周、新提任領導干部和新招錄公務員在試用期內用一個月時間,參加“三進三同”。且每年定期回訪1到2次。
4.體驗高尚、遠大的精神境界。任何偉大的思想家都意味著人類的思維方式和精神境界達到了極高的維度,人類歷史和精神發展的歷程,是以偉大導師的頭腦和著作為路標的。高校思政教育的目的不是讓學生記住一些“現成的知識”和條條框框,而是讓學生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方法和邏輯,進而提升大學生的精神素養和人生境界。在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中,大學生可以從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事業和人格那里感受“為全人類而工作”的恢弘大氣和精神高度,感受“有許多敵人,但沒有一個私敵”的光明磊落和坦蕩胸懷。
組織部對下鄉的官員提出一連串“不準”——不準事先踩點,不準層層陪同,不準特殊接待,不準敷衍應付,不準縮短時間。并規定每天向同住的農戶支付食宿費25元。
最為關鍵的是,將“三進三同”效果作為任用干部的考核指標。
怎樣“同吃”?
數以十萬計的官員開始住進偏遠的鄉村。
在田間掄起鋤頭翻地或插秧的,可能是市政府的秘書長,是某市級部門的局長、主任,或區縣的書記、區長,好些是農民一輩子都見不上一面的“大官”。
市委要求與農民結窮親,科級干部結一戶,處級兩戶,廳級三戶。據統計,有20萬干部結了50萬戶“窮親”。
“三進三同”要求官員們到最艱苦、最邊遠、最基層的貧困村,入住貧困農民家,不能入住條件好的農戶,不能住村干部家,不得以任何形式增加基層和農民負擔。
這對一些30到40歲之間,平日養尊處優的官員是一個挑戰。
“三同”中的“同勞動”,官員們很快能夠適應。而“同吃”時,則遇到了問題。
重慶市地稅局兩位女性官員入住的農戶家,是張姓的老夫婦兩人。張大爺成天叼著煙,煙灰到處撒。在晚餐時,一大截煙灰像撒胡椒面似地撒滿菜盤。而大爺端湯上來時,兩只臟兮兮的大拇指深深泡進湯里。兩位女士不禁驚叫起來……
“大多數干部最后還是能克服,并幫助農民們改掉一些不好的習慣。”市委組織部在總結報告中稱。
吃力的“同住”
“同住”要求下鄉的官員只帶隨身換洗衣服進入農家。
“其實現在農村情況還是比過去好,老百姓大多能把鋪蓋準備得干凈,有的農民還把自己好點的床讓給官員睡,自己睡住破的木板床。”市“三進三同”辦公室一位人士告訴記者。
但是有的人城里住慣了,擔心有味道;還有的村子的廁所建在豬圈旁,用化肥袋子當門,有的干部很不適應。為此,一些官員一度“住不下來”。
為糾正“住不下來”,合川區委組織部在2010年3月請了20名大學生擔任調查員,對進村的人員情況進行電話全覆蓋調查。有時一晚要兩次打電話到農戶家里,要求與干部本人通話。
這一招,讓“同住”官員的入住率達到85%,第三天達到100%。
“最后大部分人住下來了,被農民的純樸所感染,自己也發生了轉變。”
“重慶市委一位常委在一次會議上告訴我們,他‘結窮親’后,去年救助貧困家庭就花了1萬多元。”蘇偉告訴記者。
爭議聲中
事實上,“三進三同”并非新發明,在1960年代的“四清”運動中,就有黨政干部與貧苦農民“三同”的要求。當時甚至規定“三同”干部“四不準吃”——不準吃雞、魚、肉、蛋。薄熙來的父親、開國元老薄一波在回憶錄中對當年的“三同”有不少記載。
自薄熙來2007年12月就任重慶市委書記以來,這座山城在外界眼中變得越來越“紅”。許多重拾老傳統的做法引發爭議。有人擔心這會將這個正雄心勃勃地進軍西部金融中心和IT制造業基地的城市,“拉回到政治運動年代”。
但在重慶掛職的清華大學教授崔之元認為,重慶的探索有其價值和意義,“三進三同”肯定對干部有觸動作用。
“共產黨干部是該聯系窮人還是富人?或者窮人富人都要聯系?重慶要求都要聯系,但反對傍大款,大力提倡結窮親,這種聯系群眾體現了執政黨政治路線問題,是執政黨解決如何贏得民心的重大問題。”蘇偉說。
重慶社科院研究員丁新正認為,“三進三同”這種最高層與最基層的直接互動方式,是在實踐一種新型的社會管理方法。
重慶作為西部唯一的直轄市,不僅具有西部的特性,也有很多的獨特性,大城市、大農村、大庫區、大山區、少數民族地區疊加。同時全市農村的面積和人口比京、津、滬三個直轄市總和還多,全市有15個貧困區縣,貧困人口多達113萬。
同時,重慶農村正經歷著重大轉型,其經濟社會結構以及與農村相關的人口、土地、農業、教育、情感、訴求、愿望等都出現了諸多變化。
“如何面對和處理農村發展中的復雜、重大問題,了解基層的想法,‘三進三同’無疑是躬身實踐,了解基層,做好基層管理的有效載體。”丁新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