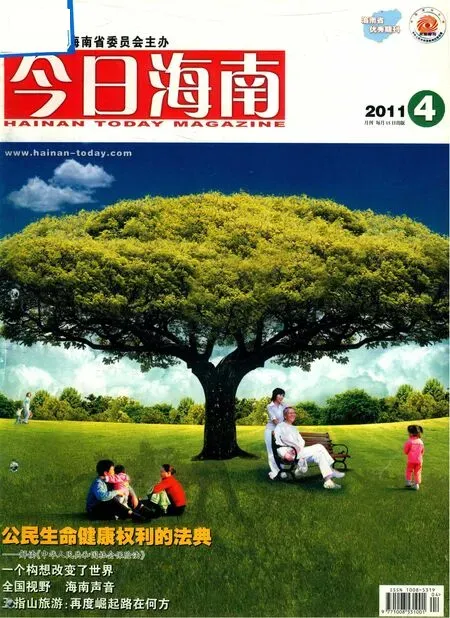公車改革幾多難
——從回望澄邁車改說起
□本刊記者 王秋虹
公車改革幾多難
——從回望澄邁車改說起
□本刊記者 王秋虹
多年來,有關公車改革的話題一直不絕于耳。今年的全國兩會上,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2011年將“規范公務用車配備管理并積極推進公務用車制度改革”,“嚴格控制黨政機關車輛購置及運行費支出原則上零增長,切實降低行政成本”。3月4日,財政部印發《黨政機關公務用車預算決算管理辦法》,首次將公務用車納入預決算管理,再加上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黨政機關公務用車配備使用管理辦法》,這一系列動作再次引發了社會和公眾對于公車改革的熱議,使得有關公車改革的各種爭論和探討再次被推到風口浪尖。
公車整治放到了國家政策的層面,政府有關公車改革的決心可見一斑。公眾當然有理由對治理公車腐敗問題抱有積極的期待。然而,一個現實問題是,從上世紀末開始,我國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就先后進行了公車改革試點。但十幾年來,這項改革并沒有真正破題,一直在爭議中走走停停。
1997年,廣東省首開我國公車改革試點。1998年9月,國家體改委制定《中央黨政機關公務用車制度改革方案》,部分中央機關進行車改試點,同時,浙江、江蘇、湖南、重慶等省市的部分地區,也啟動車改試點。2004年成為全國性公車改革的高峰年,北京、廣東、上海、浙江、江蘇等地當時都曾試點公車改革,引發輿論強烈關注。但這些公車改革的嘗試與探索,最后的結果幾乎無一例外地走向三種:要么在爭議中擱淺,要么退回到改革前的狀態,要么處于前兩種狀況之間,“騎虎難下”。
海南省澄邁縣車改或許是全國車改的一個縮影。作為海南省第一個“吃螃蟹”的市縣,澄邁縣從2004年11月開始率先對公務用車制度進行改革;2005年7月,在公車改革前期取得了良好的經濟、社會效益的基礎上,澄邁又在全國率先進行了公、檢、法部門的公務用車改革,如今已過去6年有余。在第一年的轟轟烈烈過去之后,如同全國的公車改革相繼悄悄擱淺一樣,澄邁熱熱鬧鬧的車改,也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澄邁車改的成敗得失,迄今鮮被提及。
一難 車補標準難界定
國內進行公務車改革的試點地區,往往采取的通用辦法都是貨幣化補貼的方式,即給公務員發放“公務活動交通包干費”,又稱“車補”。但是,車改從一開始,爭議最大的就是車補標準。“車補”應該按什么標準補、補多少成為公車改革最需要解決的課題。
直到目前,全國也沒有一個統一的車補標準。據了解,2004年時,海南省澄邁縣公車改革的公務交通補貼費標準是按照“職務+級別”的辦法來核定的。其中,按“職務”的補貼標準為,縣級正職每月2400元、縣級副職每月2000元;一級局(含鎮)正職1600元、副職1000元;二級局正職1000元、副職500元。按“級別”的補貼標準為,正縣級800元、副縣級700元;正科級600元、副科級500元;股長350元、科員和辦事員250元。
據澄邁縣公車改革辦公室副主任姜維高介紹,從2009年下半年開始,澄邁縣又增加了“私車公用”的交通補貼,其標準為副處級以上500元、正局級(正科)400元、副科級300元、副科級以下不補。這樣算下來,車補最高的正縣級領導干部每月可領交通補助3700元,而科員和辦事員補助最低,僅250元,二者相差14.8倍!
無獨有偶,2004年出臺的珠海市市直機關的車補標準則為:正處級3000元、正科級1700元、科員和辦事員700元、職工300元,最高標準與最低標準相差10倍;2005年出臺的昆明市的車補標準是正處級1500元,正科級1000元,科員、辦事員月500元,工勤人員300元,最高與最低標準相差5倍……
每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人均收入均不相同,車補多少、如何切分才算恰當沒有一個科學標準衡量,致使公眾對其頗有微詞。“車補是否等于變相加薪”的質疑聲幾乎是車補的雙胞胎兄弟,從車補甫一出現就如影隨形。另外,海南省委黨校副校長廖遜說:“車補按行政級別發放,凸顯了官本位意識,不一定有利于政府職能的轉變。而且不同的工作職責,需要外出乘車的機會有很大差別。”
“實際上,有很多跑基層的科員反而交通花銷比較大,所以,他們要求提高車補待遇的呼聲是相對而言最強烈的。”澄邁車改辦有關人員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據記者了解,澄邁縣車補費用的最高水平已高出其工資水平。而姜維高介紹,在今年澄邁“兩會”上,有不少委員和代表還提出,因油價逐年看漲,目前的車補已不夠用,要求整體提高車補待遇。可在廣東兩會上,廣東省政協委員林秋城提供的數據顯示,每輛出租車的工作效率為公務用車的5倍,可運輸成本僅為公車的13.5%!
姜維高說,雖然沒有具體的統計數據,但車改之后,實際上每年用于車改的補貼及相關開支的“絕對數增加了,因為車改覆蓋面廣,幾乎所有的公務員都享受到了車補的待遇”。

據國家發改委調研顯示,公車使用有三個“1/3”,即辦公事占1/3,領導及家屬私用占1/3,司機私用占1/3
車補到底多少才夠用?對于這個問題,連續7年在全國人大會議上疾呼公車改革的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全國人大代表葉青給出了“1000元”的答案。從2003年起,他開始踐行“一個人的公車改革”住在武漢市郊區的他根據平時用車的情況總結出,除開出差費用不算,自己每日公務用車平均開50公里左右。“以前的補貼是每月500元。2007年以來油價躥升,單位把補貼漲到1000元,一年共1.2萬元足夠。”葉青說。
另外,昆明市在2010年新一輪車改中,將車改標準定為每人每月400元,這是經過近3年對公車購置、運行費用的調查計算得出的平均數字。并且,為了防止一些公務員不把這部分錢用在公務上,這筆車補費用并不是發到每個人手里由個人支配,也不按照級別高低來分配,而是根據工作需要,由單位統一支付因公發生的用車費用。
二難 監督管理難堅持
除了車補標準飽受爭議之外,各地區在公車改革后,一些公務員“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做法更讓人防不勝防,頭痛不已。姜維高對這些情況一一舉例:有個別干部為了節省費用,或者借用沒有車改的企事業單位的車輛使用,或者要求工作對象派車接送;有些兼任政府部門下屬企業職務的干部棄自己私車不用,無論公私事都使用企業的公車;曾經貼在公車上方便公眾監督的標識,或老化后自然脫落,或干脆被人為撕掉,致使公眾無法行使監督的權利。
更有一個特殊的現象是,在一些已經進行了公車改革的試點,公車數量出現死灰復燃之勢。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自2004年澄邁進行公車改革以后,迄今為止,又“新增”公車70輛左右。這“新增”的70輛公務用車從何而來?姜維高說,它們大部分來源于“上級劃撥”。
公車改革暴露出的諸多“后遺癥”為何沒有相關部門來監管?據了解,很多地區都在推行公車改革時成立了公車改革辦公室專門負責車改事務,是它們沒有發揮應有作用,還是另有原因?
“像很多地區一樣,當時為了推行車改,多是臨時從各單位抽調人手成立了公車改革辦公室,但并沒有具體明確這個車改辦的權力究竟有多大,抽調來的人手又往往都是身兼多職,各自有各自的崗位和工作,不能統一在一個固定的辦公地點工作,加上多年來的人事變動等等,沒有形成一個由專職人員組成的專門機構。雖然這樣的組織結構在車改過程中曾經調整過,但僅限于‘皮毛’,根本上沒有變化,于是造成了現在難以監管的局面。”姜維高說。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工作人員苦笑地說:“除了車改辦,難有哪個部門會主動要求接管這種‘麻煩事’了。”
有關人員還告訴記者,除了本刊記者的這次采訪,已經有很多年都沒有哪家媒體前來過問澄邁車改的事情了。
最難 革己之命難如刺股
據姜維高分析,以澄邁現在的狀況來看,車改既沒有繼續推廣,又不能停止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以澄邁現在的財政實力,仍然可以支撐得住車改補貼及相關開支;二是考慮到如果中止車改,除了要重新購置公車之外,當初車改的方案是鼓勵公務員貸款購買私車,而如今有很多公務員的購車貸款還尚未還清,這不光是一筆資金的浪費,還會增添很多不必要的麻煩;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因為‘上面’沒有指示,我們‘下面’不好有其他動作。”
“上面”沒有發號施令,“下面”就不能有所作為,在這“上面”與“下面”的博弈中,公車改革成了一件“難事”。
葉青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歷經十多年公車改革之所以斷斷續續、難以為繼的實質是,公車改革損害的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這些受益者,即使他原來的利益不是很合理,但一旦利益受到影響,他還是覺得被侵犯。另一方面,這些受益者同時又是公車改革的決策者,要他來改革自己的既得利益,這個很難。”
葉青說,從已有的各種改革嘗試來看,公車改革均是在政府單方主導下進行,各級政府本身既是改革的對象,又是改革的主體,是改革政策的設計者、執行者,同時還是改革效果的評估者,完全掌握改革的話語權,作為改革監督者的社會和公眾則缺少話語權,更缺少實質性的政策設計過程中的討論與參與。在缺少有效外部制約和監督的現實背景下,政府“自己革自己的命”,改革的難度可想而知。
“中國的車改是‘革自己的命’,如同持錐刺股,要下手前難免遲疑,難免不忍。”海南師范大學的一位歷史學老師從不同的角度解釋了公車改革難的原因。“但若真能一咬牙一狠心,這事就成了。”
3月25日,溫家寶總理在國務院召開的第四次廉政工作會議上說,將開展公務用車專項治理,抓緊研究推進中央國家機關公車管理使用改革,今年拿出改革方案,在一些部門試行。記者獲悉,目前,中紀委已經著手制定公務車改革指導性意見。
公車改革幾多難!此次國家層面的親手推動,能否推動公車改革的車輪破冰前進?“很期待。”面對記者的采訪,很多人都不約而同地說出了這樣一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