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曲四章
吳安臣
幽曲四章
吳安臣
壓 迫
我在監考。我面對著無數的背,整個考場中學生的后背都對著我,我感覺潮水向我襲來。帶著脅迫,我從無聊中感知到寧靜的可怖。我的身體仿佛失去了一層保護,在空氣里無端地沉淪,感覺在空氣里撞擊,思維的凝滯和開放全在空氣里。一種虛空來自學生考試時寫字的沙沙聲。這種感覺仿佛在哪里有過,我努力回憶著。終于在思想的黑暗處綻放出一絲亮光來。
那時正讀大學,一次我去參加演講比賽,生平從沒見到過那么多的臉,所有的人都滿懷期待地望著我,甚至還有校園電視臺記者的鏡頭對著我。我把那份背得滾瓜爛熟的講稿拿在手心了,拿出后又覺得不合適,接著我把它放回兜里,但是等額頭上的汗珠沁出時,我卻又發現不拿講稿我會渾身發抖,于是我又把講稿拿出來,突然我又意識到拿著稿子上臺要扣分的,雖然你沒看,但是至少顯示出你的底氣不足,于是我又把稿子放回去。那些等著打分的評委像觀看猴戲一樣,把手抱起來,看我到底要干什么。我感覺手心里的汗已經泛濫了,那份講稿稍不留意就會變成紙漿,我甚至能聽到水滴落在地板上的聲音。
我就像欺騙所有期待的眼睛和耳朵一樣,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兒,我覺得我在犯罪。我甚至還看到負責攝像的那位記者已經把鏡頭對準了我,我看到攝錄的紅燈閃爍著,但是我居然不會開口說話了,這簡直就是對他的戲弄,我看他把攝像機拿起又放下。無奈的他,我想那刻他只想沖上來揍我一頓,但是那么多的人都被我愚弄了,也不差他一個,所以我甚至也能聽到他骨節響動了幾下,最終他還是忍了。
我看了看他們的眼睛,只想這樣開頭,我太緊張了,我要爆炸了,但是我不能這樣說,那樣所有的人更會覺得他們受到了愚弄和傷害,也許從此就會把我當作一個非正常人來處理。我感覺自己像《圍城》里的方鴻漸一樣尷尬和無奈,我哆哆嗦嗦地又把講稿從衣兜里拿出來了,惶恐地看了一眼,就一眼,我的心差不多已經跳出了嗓子眼,我感覺自己是此次演講賽中最拙劣的選手,我不清楚自己講了些什么,總之我看到評委的臉和我一樣通紅,特別是那位在場下給了我無數指導的老師,我把他的臉已經丟光了,仿佛所有的目光已經集中在他的后背上一般。當我哆嗦著把“我的演講完了”幾個字說完時,我覺得自己馬上要被眾人的目光解體了,我像一只倉皇的地鼠逃向座位,至于同桌的那位說了些什么我根本沒心思去聽,我想沖出演講大廳,但是我想如果我真的出去了,那么我將再次成為眾人注目的焦點,于是我像羅馬競技場上的奴隸等待我對面虎視眈眈的獅子退場一樣,感覺所有的目光之箭壓向我。事情過去很多年了,凡是參加過那次演講賽的人都會記著我,于是他們在見到我時增加了一樣談資,于是這么多年來我一直活在一件往事的尷尬里。
轉眼我走上了工作崗位,往事終于被一些人忘記了,或者他們已經厭倦了再去重復那些陳年舊事。但是新近的事卻又以另外的形式在我的腦海里籠罩著我。
繼父得了大病。以前我倆的關系很僵,但是作為人子我不能不使出渾身解數來救他,臨到手術簽字了,我的手抖得十分厲害。村里人在繼父的不斷解釋中認為我是一個不孝子,手術如果出現意外,那么我要負全部責任,假如繼父發生意外,那么村人肯定認為我這個繼子沒盡力。
自從繼父被推進手術室我就在外面的走廊上徘徊了,我試圖用書來平靜自己,但是我覺得這些文字的東西,像一些無意義的符號,腦子里是繼父衰弱得如風中枯草的模樣。我如何減輕我的心靈負擔,思考了半天我毫無辦法,嘴里又苦又疼,連日的奔波把我也弄得形容枯槁,我在昆明的大街上像一具干尸一樣地走動,人流在我的前后左右洶涌,聲音從四面八方迫近我的耳鼓,我為什么會在這座城市里?我經常發出這樣的疑問,我真的不喜歡這個地方,自從我來到這座城市兩星期以來,它已經殘忍得把我的口袋翻了個底兒朝天,每天幾百塊的醫藥費把我逼向絕境,拿起電話來感覺我的手伸向的是虛空,這座繁華的城市我找不到幫我的人。我像游魂一樣又回到我的家鄉,還是那些窮哥們幫了我,但是等我把錢真正拿到醫生手里時,我新的擔心又誕生了。
我在走廊外徘徊,不斷地有病人從手術室被推出來,家屬們迫不及待地沖向那輛手術車,夾著淚痕,夾著輕聲的呼喚,我也木然機械地沖向前,但是我一次又一次地退下來,像潮汐的無意識涌動,我頹然地坐下,站起;站起,坐下。時空仿佛已經停止了,在那8個小時里我覺得這座城市已經陪著我停止了轉動,我的腦中沒有了一切,空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擠壓我,我退著向后,我抱著頭逃遁,我眼前不斷閃現血肉模糊的繼父的形象,我的手又開始顫抖了。
我的恐懼像來自醫院的特殊氣味,我把頭伸向窗外大口地呼吸一口氣,但不經意間就看見了外面灰白的天空,那死氣沉沉的天像大病未愈的臉,我趕緊關上窗子,拉緊衣服,靠墻根坐下,走廊里只剩我一人了,燈光已經亮了,慘黃!燈光下我覺得身影在變異,不規則地投射在地上。黃昏的來臨像鬼魅一樣不期然而猝不及防,我的嘴唇焦干,感覺一股一股的煙正從心底躥上來。終于見到繼父了,在手術床上的他面色蠟黃,說實話那分鐘我只想說聲上帝保佑,我的心仿佛走出了黑暗的甬道來到了明媚的陽光下,我和他的關系可能從沒這么親密,我俯身問他疼嗎?但是醫生阻止了我,他們說他的身體太虛弱了,所以手術時間長了些,比起一般的這類病人要長出好多,我想說就是這長出的幾個小時,我的心靈已經走入煉獄。感謝上蒼垂憐,也慶幸繼父挺過來了——人生中的大苦痛,我則經歷了人生中的苦痛歷練。
經歷一場生離死別一樣我覺得自己空前堅強起來。于我來說,人生中似乎沒有能超越這次苦痛的了。
人生之路漫長,也許就是在這一段又一段的苦痛壓迫中我們才慢慢走向成熟,心靈之舟負載的所有折磨和疼痛都是對靈魂的洗禮,沒人喜歡,但是你總會遭遇。無人能幸免。

葉永青 喜悅 布面丙烯 200×200cm 2007
假 象
我的生活充滿偽飾,也許不應該這樣說,因為我不是演戲的,我生活在真真切切的世界上,但是面具后我總覺得自己在欺騙自己,我呈現給別人的都是一種假象,我的一切裸露在面具里,我本真誠的人,說話辦事給人的都是表里如一的印象,所以即使我偶爾在別人面前表現的不是我自己,他們也只會瞬時驚詫一番而已。
我的老同事,他們從我原先工作的地方來。我們高談闊論,我裝出在城市飽經世故、曉暢一切的樣子,他們很是相信我說的。一天我們一起出去辦事,因為我來城里有些時日了,于是他們想當然地認為我對那些大街小巷熟悉得不得了,偏偏要找的那個地方甚為隱蔽,很不起眼,我們一伙人坐在出租車里,我坐在和司機并排的前座,作為向導我似乎要比司機更熟悉這座城市的地理一樣,我領著他們轉了很多圈,最后連我自己也糊涂了,轉哪去了?蛛網密織的巷子,同樣高聳入云的高樓,讓我感覺有點眩暈了,司機有些不耐煩了,他對于我這領路的失去了耐心,雖然時間每過去一段我們總要付給他錢,但是他急躁萬分,仿佛我們要赴的是火線,最終我們一伙人不得不從車里出來,陽光把我的眼睛刺得生疼,偌大的城市我隨時充當的還是那個迷路孩子的角色,我尷尬地笑笑,說幾天不來,這片好像增加了許多高樓。
其實誰都清楚,大樓不是一天兩天就能聳立起來的,但是這蒼白的謊言總能讓我虛弱地活著。他們眼里的我和真實的我完全是兩個人,他們寄予我的期望越多,失望也就越多。我本就是從鄉下的天空飄來的一粒稗子,不可能對于城市的肌理那么清楚。有人說女人天生沒有方向感,其實我也缺乏方向感,我甚至對著徐徐西沉的太陽傻想:這太陽怎么還懸在南方就下沉了,城里的方向難道和鄉下不同?原來是我迷失了方向,根本就是同一顆太陽落向同一個地方,是我的感覺發生了錯位罷了,可是這些我都不敢讓別人知道,知道了,別人會笑話的,一個大男人居然會犯這種錯誤,那簡直是不可饒恕的,于是我愈來愈會偽裝,最終就愈不像我自己。
記得那天我在翠湖邊上繞了很多圈,腿幾乎都瘦了一圈,我從下車的位置走,按正常時間十分鐘就能到我朋友那,他從接到我電話時就到門口張望,直到一小時后他才見到我,他說這一帶治安好的嘛,我還以為你遭遇搶劫了,我們這你來過幾回了?我說我的確迷路了!他說不會吧?來前你吃了迷魂藥了?我說我眼里這樣的樓太多了,每幢都是一個模子,我眼睛都看花掉了,我數著門牌找來,差點被保安抓了去,他說我像溜墻根撬鎖的。他將信將疑地打量我,最后說,天啊!這種錯誤你都會犯,把你丟亞馬遜叢林里看來你只有等死了?!我說,估計我在亞馬遜活不了一個時辰,在一個中型城市我都難以生存,不要說在熱帶雨林了。我的神經脆弱得像焦糊的紙,經不起什么折騰的。
以前的朋友往往以為我是一個百事通,什么都會來問我,但我知道的實在有限。朋友打我電話說他要買一臺電腦,在下面買貴不說,缺乏參謀,我是這方面的專家,我說專家?!你封的啊,我只不過比你多用了幾年電腦而已,啥時成專家了,他說甭管什么專家不專家,我就信你了,我把錢拿給你,你一定要幫我買!后來他果然把錢給了我,我也就冒充專家去幫他買了一臺,總之那是品牌機,人家不是賣一天兩天,里面沒有什么“水分”的,但是電腦拿到家就出問題了:網速慢,桌面打開半天不顯示……無數的問題出來了,怎么辦?問我這“專家”啊,但是對于癥狀的解決,我又不在電腦跟前,只能無關痛癢的說了很多對策方法,毛病依然無法消除。朋友說我以前覺得你對電腦挺內行的,特別在城市里,對于這些不是小菜一碟,我說我不是什么狗屁專家,你硬要我買,問題出來了吧?你自己愿意舍近求遠跑省城來,倆人理論半天,不歡而終。他懷疑我的能力或者眼力,我呢倍覺冤枉,在他眼里,我既然每天都對著電腦,就應該是專家學者,而事實上我只會操作,不會那些“修理”方面的東西,妻子也埋怨我。我說招誰惹誰了,出力不討好,妻子說,哪個叫你每天裝作什么都懂的樣子,你給人的印象就是那種上知天文,下曉地理,中間還研究著空氣的人。天啊!這種欺騙性的印象,居然是別人給我下的結論。
有很多時候,我在思考像我這樣的人在這個城市究竟還有多少,究竟什么誤導了我們要在很多時候裝作什么都懂的樣子,其實是生活!整個社會都在召喚全知全能的人,不然什么“點子”公司不會出現,在人才招聘上,要我們精通這,精通那,其實我們究竟對于這紛繁的社會知道多少,鬼才知道!我們懂的東西局限于我們有限的認知,我們的視線里假象尤其多,我們的迷惑伴隨我們漫長的一生,所有呈現在我們眼前的不是你眼睛看到的全部,還要用你智慧的心靈去判斷。
這些就像我參加的一次報社招考中出現的邏輯判斷題,是謬論還是正確判斷,答案在內心深處。我們很希望自己生活在假象之外,但是現實就是樊籠,我們無法逃離。假象依然存在著,于是我們看到的似乎是一個危機四伏的社會。
轉 身
一轉身全世界都變了,所以古人才會說,“再回頭已是百年身”!人生軌跡就此改道,跌入往事的我們會發現所有的轉身成了追悔,轉身間愛人走遠,親人離散,紫陌紅塵,紅顏青絲染白霜,童稚少年成老弱,人生在轉身間如飲隔世的蒼涼。有時我們因不得已而轉身,有時我們因錯誤而轉身,輕輕的一個動作,微小的一個舉動,我們已來到幸福的門外,再去推那扇我們轉身后才發現的幸福之門,卻看到那門已經生銹;那個心儀已久的女子,你用整個生命去愛的人,囿于你的羞澀,你沒開口,轉身離開,你發現她也是那么愛你,可是你們都選擇了轉身;我們摯愛的親人在我們轉身遠離的時刻,被埋入時光的深處,我們無奈的手做出的是凄涼的呼救。這世界很多時候不容許我們轉身,我們沒有回旋的余地。
記得我小的時候頑劣異常,那時的我不知道什么是我要遵守的,什么是我應該懼怕的。我偷鄰居家的桃子,趁著暗夜在高高的樹上攀爬;我領著一伙我的死黨拔了那可惡異常的老太婆家的莢豆;夏天到來,盡管父母一再叮囑我不能到水塘里去,但我依然在里面馳騁縱橫,不亦樂乎;最后我和村里大我幾歲的二流子成了朋友,伙伴側目,大人搖頭,一時間我似乎成了人人覺得不堪的人。那個下雨的午后,我和他去村子西面的破窯燒蠶豆。這次燒蠶豆,嚴格意義上說,改變了我以后的人生道路,假如那時我還為自己負責,想想將來,但是那時我沒有要為自己將來負責的打算,那時尚屬懵懂無知啊。
其時,我母親帶著我一人在云南,繼父在河南,繼父的姐夫,也就是我的大姑父在他唯一的兒子遭遇車禍后,打算把我接到昆明去接受最好的教育。因為我的這位姑父當時在云南省供銷社工作,云南省供銷社那時是個富得流油的單位——這自然跟我國特定歷史時期的國情有關。他有這個能力給我接受最好的教育,他會把喪子之痛后的全部愛轉移到我身上,甚至還準備把他的第五個女兒嫁給我。我們間是無血緣上的半點牽連的,這就好像榮華富貴一下子堆積在我面前一樣。那天母親把我在昆明要穿的衣服洗得干干凈凈,折好放好,我回來就可以和大姑父上車去昆明了。但是那時我正和那個所謂的二流子大朋友忙得熱火朝天,蒙蒙細雨里燒蠶豆的香味粘住了我的腳步,我想不出這世上還有什么會比燒蠶豆更有趣的。假如我轉身回去了,不吃什么狗屁燒蠶豆,那么我以后也就不會遭遇一系列的人生磨難了,但這世上沒有“假如”,只有事實,既定的事實,無法改變的現實。大姑父等了一下午,因為急著趕時間,他開著車走了,那一走把我人生軌跡拖得變了形。直到今天他還在說我,因為現在我們都在昆明。但我能在昆明,是我兜了很多圈子,吃了無數苦頭才來到這的,如果當初跟著他來,那我就順理成章地成為地地道道的昆明人了,也許我也就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小市民,但這倒不是我希望的。母親在那時不是咒我,而是“嫁禍”于燒蠶豆和那個大我很多歲的朋友,雖然這二流子朋友而今已長眠于地下。而我絲毫不怨他,我在多年以后把一切歸于命運的安排,我就是多災多難的命,像唐僧取經一樣,不遭夠那么多難,似乎難成正果,但想想命運之神究竟在哪誰說得清。
后來我讀了高中,那時我在河南的商丘,古時稱為歸德府的地方。生活的艱苦不說了,生活了十多年我居然還是一個黑人戶,在高考來臨前我回了云南。那時和繼父的關系異常緊張,家庭困難,所以按莊戶人家的邏輯我應該回家砍柴拉石頭掙錢娶媳婦,過平常日子,但是考慮到我自己不是那塊料,文弱書生一個,我不打算做個莊稼漢。我和繼父的關系開始冰凍,我去麗江打工時他寫信給我,叫我去當兵,離開他了,他仍然不放過我,我感覺到窒息,人生的路該由自己選擇,他為什么就要時時安排我呢!我堅決不去,連信也懶得回他,現在想想也許他的想法是對的,如果我去部隊,憑著我能寫點小東西,在那兒或許就有了更廣闊的天地,因為我從小就想當兵。小時候我在青島看到海軍時我還央求母親給我買了一套海軍服,穿起來甭提多神氣了。干什么事你首先要感興趣,興趣可是最好的老師,但是為了和繼父賭氣,骨子里的那點倔強讓我頭也不回。再后來由于交不起學費,上了師范學院,成了自己做夢都沒想到的老師,一不小心,育人六載。當老師有當老師的樂趣,現在我的學生遍布昆明各個大學,這或許也是一種欣慰,但總覺得和兒時的理想差之甚遠。轉身的錯與對我實在說不清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在那些錯誤的地點,不,地點也許從來沒錯,只是我們站立的地方錯了,于是我們再來一個錯誤的轉身,一切再也無可逆轉。
記得前幾天在《遼寧青年》上看到一篇文章叫《你敲門了嗎》,故事說一個來自農村的、才華橫溢的少年,他無可救藥地愛上了班里一個氣質高雅、美麗脫俗、家庭背景很好的女孩,女孩也十分仰慕他的才華,倆人一直保持著那種純潔的友誼,但是誰也不愿捅破那層窗戶紙,男孩出身農村由于自卑,女孩則因為矜持。女孩在畢業前的一天告訴男孩,她家里人都出去了,暗示了男孩,男孩憋在心里的話終于有機會表達了。但是男孩按照女孩給的地址找去,按了很多次門鈴,卻沒人來開門,于是他傷心地離開了,認為女孩只不過隨口說說而已,自己怎么就當真了呢!很多年后已為人妻的女孩告訴孑然一身的他,那天是她家的門鈴壞了,她忘記告訴他了,他只要敲敲門,而不是轉身離去,那么心儀已久的女孩將屬于他,幸福之門將不會再關閉,轉身間紅塵中他少了相伴的知己,也多了一位傷心的紅顏。一個轉身,愛人們從此南轅北轍,冥冥中似乎總有聲音在喊,轉過身來啊!只可惜世間多少傷心人沒有回頭,卻只會哀嘆。
來到陌生的城市后,天天疲于奔命,家的概念似乎淡了,父親重病,回了三趟家,每次轉身離開總抱著幻想,總以為他會好起來的,最后一次看到骨瘦如柴的他,我有種預感,但我沒有在預感下留下陪他,他不知能否挺到我再次回去看他?已經無法言語的他做著手勢,那個手勢或許就是挽留,但是我為了工作離開了。那個轉身帶著多少殘酷的意味哦,我至今無法衡量,壓在心上隱隱如巨石般,彌留之際我沒能在身邊,入棺時我沒能看看他,于是從此陰陽殊途。我無法原諒自己,每個我的心能騰出清閑的日子,我總要燃一炷心香遙祭他,彌補我曾經的轉身之過,療我內心深深的傷。
莫轉身,可我們還是頭也不回,甚至義無返顧;莫轉身,但我們還是固執己見,甚至自我辯護;莫轉身,而我們仍然勇往直前,甚至錯誤獻身。紛繁塵世,諸般迷障,理智轉身,莫在轉身后嗟嘆,莫在轉身后呼喊,上蒼耳背,聽不到這些。轉身是自我的選擇,謹慎點,小心點,彼岸的花香自然就會飄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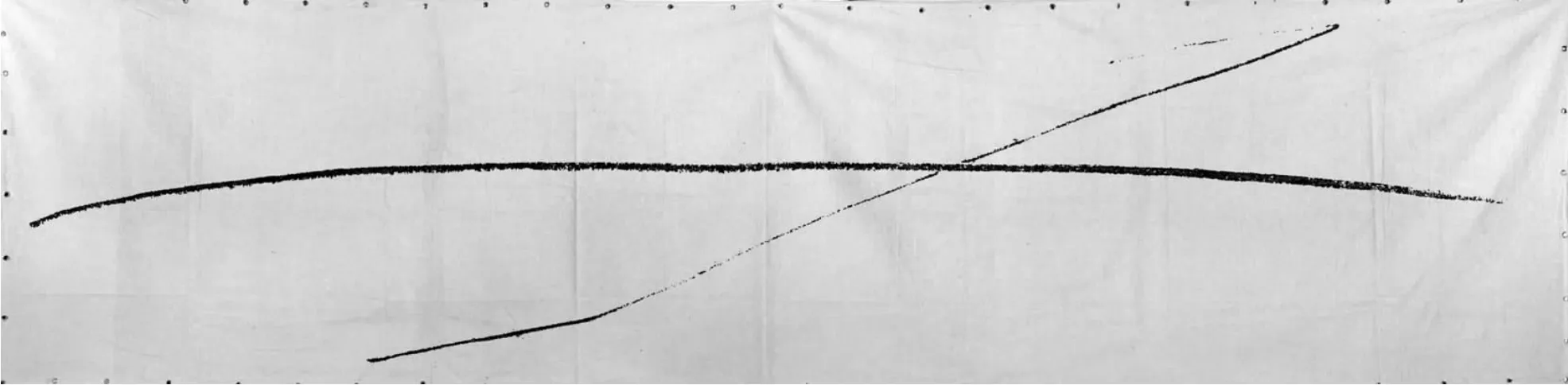
葉永青 姿勢 版畫 150×600cm 2007
黑 暗
我想每個人的內心都有一條黑暗的甬道,我們一生都在試圖從甬道中突圍出去,所以我們犯了錯誤。所謂的錯誤其實就是黑暗的外在顯示,有些人甚至走向了極端,比如詩人顧城。這位外表文弱白皙的天才詩人,你無法想象他會向自己的妻子舉起利刃,那可是結發妻子啊,但他終究砍下去了,黑暗將他自己也送入了極端:他也死了,歸入永久的黑暗中去了。人們無法理解左右這位天才詩人的“惡魔”是什么,連我這位很不愛詩的人也為此感到震驚;海子臥軌自殺了,從詩歌之神的手里接過死亡令牌后,他從我們的視線里永遠消失了,在內心黑暗的驅動下,他不顧親人的悲慟和絕望,把身體交付給冰冷的鐵軌,他解脫了,后人卻無法解脫,很多的人還活在他的詩里,尋找著他臥軌的答案;三毛隨荷西去了,在遙遠的撒哈拉,她把和荷西的愛情經營得像熱情的沙漠,也許在她的生命中不會再出現另外一個荷西,抑或再找不到活著的理由,連民歌大王王洛賓也無法給他歌聲之外的另一半,于是他走得匆匆而決絕。
走入極端的他們依然在黑暗里徜徉著,而我們呢,我們內心那塊陽光照不到的黑暗角落呢?它在哪里?它在哪左右著我們?我們不清楚,黑暗不是因為夜的來臨,是我們內心總有背陰的地方,我們無法告知別人,因為它在我們身后,在適當的時候它會潛入我們的內心隱蔽起來。我們寶貴的軀體總是在黑暗的包圍中輸給所謂永恒的靈魂,這一切人們慣常的說法是“無常”,這個無常鬼躲在冥冥中。其實冥冥就是我們內心的某個角落,無法抗衡的命運似乎永遠游離在我們之外,真正的卻是駐扎在心靈里,于是心理學家說我們要突破自我。其實我現在才明白,那個自我就是內心那個黑暗的角落,突破說白就是向黑暗宣戰,可惜很多人窮其一生都無法突破自我。

葉永青 畫鳥 布面丙烯 200×150cm 2008
小的時候很怕黑,天一黑更甚,那時還沒有電燈,煤油燈的光源總是覆蓋不了多大的地方,而且把人的影子拉得很長,那些長長的影子比我們的身體大出幾倍,起初也許我們的怕就是那些拉長的影子造成的。加上大人愛講鬼故事,嚇唬哭鬧的我們,于是我們在黑暗中噤若寒蟬。那時村西的山坡上埋了許多人,大人們就發揮各自的想象力說那些鬼會在晚上出來狂歡,和人過節一樣,那時不明白鬼為什么要那么高興,出于恐懼,也不敢問大人為什么鬼要天天出來狂歡,難道鬼認為自己和人生活在不一樣的世界是一種解脫?經常有晚上出去放田水的人會碰到鬼,甚至連我舅舅都說他在村西的三觀殿下見到了鬼,當時那鬼向他借火,我問鬼借火干嘛?舅舅說能干嘛,吸煙唄!哦!我似乎明白了,覺得這鬼也是個煙鬼呵!不然怎么敢跟人借火。但是我又問,不是說鬼怕火嗎?舅舅的回答似是而非,你說半夜三更的,哪個人會在那荒郊野地里,而且我剛把火把湊過去,那鬼打了個唿哨,倏忽就不見了,你說那不是鬼是什么?而且人怎么能在崎嶇不平的河道里跑那么快?小小的我實在想不出還有什么東西如此迅捷,于是就姑且相信世間有鬼。
鬼是黑暗來臨之后,在人們似乎進入夢鄉的時候才開始活動的,這鬼界和人世間一樣有好有壞,比如向舅舅借火的可以稱其為無傷人惡意的鬼,而有些鬼則像世間的惡人,它會處處與人作對。
大人們在我們恐懼的基礎上告訴我們,晚上,特別夜深的時候,有人叫你的名字,千萬不能答應,一答應,你的魂兒就會跟鬼一起去了,鬼讓你坐轎,也就是把你丟在刺蓬上;領你往墻上撞;讓你往井里跳……好家伙,這些可差不多全是致人死命的舉動啊,這鬼真是可惡!但是我們又對他們無可奈何,活動在黑暗里的他們有超乎人類的偉力。于是小時候自然而然地怕黑,大了以后才知道這些都是生理上的懼黑,其實我們不可能在白天把所有的事情做完,很多事情還要在夜幕降臨后來做。譬如走夜路,我一個人有一次走了很長一段夜路,那段路據說有很多鬼出沒,但是為了回家我還得走,最終我克服內心的恐懼走完那條路,沒碰到鬼,慢慢地我發現其實外界的黑暗給我們造成的恐懼遠遠不抵內心的黑暗,走不出內心的黑暗,我們將永遠陷在自我的泥淖中無法自拔。隨著年齡的增長,見識的增多,那些生理上的黑暗恐懼逐漸遠離了我們,困擾我們內心的黑暗卻越來越多,大面積地在我們的心里延展著。
高考結束,我落榜了,我是平時師生認為的優秀生,平時的榮譽讓我負載了太多的期望和責任,能考上是自己的榮耀,也是別人的安慰,考不上別人失望都在其次,無法原諒自己才是致命的。那段時間我把自己關在黑暗里,我似乎感覺到黑暗已經籠罩了我的世界,我似乎能聽到胡子生長的聲音,幾天下來我蒼老了一大截。接著我只有外逃,我到那個沒有幾個人認識我的地方躲藏了起來,后來我發現無論我躲在哪里,我終究無法躲避我內心的黑暗,終究無法突圍出去。暗夜里程海湖在晚風吹拂下,撲向岸邊,發出巨大的空響,躲在工棚里的我總感覺自己被什么淹沒著,想到未來的不可知,前途的不可測,人生航道中種種的艱險,我從來沒感到過如此滄桑和失落,整個世界都在陷落,最后我成了孤島,孤島則陷在永恒的黑色海水里,漂流到哪兒都是黑暗。最終我戰勝了黑暗,因為我還要用高考證實自己,最終漂流讓我找到了停泊的港灣。
第二次黑暗襲來是在我進入教育崗位的次年,那年我和電視臺談妥,臺里同意接收我,當時我的理想也就是當一名翻譯或者記者,能進入電視臺我也算夙愿得償了。然而我們的上級領導不給簽字,不能按正常調動手續意味著我就要出去打工,餞行的飯也吃了,人卻沒走成。一個學校鬧騰得沸沸揚揚,一個小小的鄉鎮幾乎都知道我要出去,但是最終沒有出去成,那段時間總覺得自己像過街的老鼠,這種奇怪的感覺讓我的工作激情幾乎降至冰點,談了多年的女朋友在這時也和我發生最為激烈的“戰爭”,我不是那位能一葦渡航的達摩,無法渡自己到彼岸。內心的黑暗像洶涌的海水嗆得我靈魂顫抖,最后是那句“既來之,則安之”的古話救了我,人生的種種不如意似乎總能擊垮我們,于是在自我的安慰與療救下我度過了人生的第二次黑暗。
從生理上的黑暗畏懼感到心靈上的黑暗畏懼感,其實每走一步我們都在成熟,黑暗無處不在,但是最終它都要潛入我們的內心。用我們的智慧雙手撥開那厚重的窗簾吧,讓窗外的陽光灑進來,再拿起那潔凈的拂塵撣去隱匿的黑暗,我們的心一定會充滿光明。
驅除黑暗似乎有史以來就是我們的大事,而今還是,將來更是,因為人類越發展,自我的障礙就越多,我們內心的黑暗也就越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