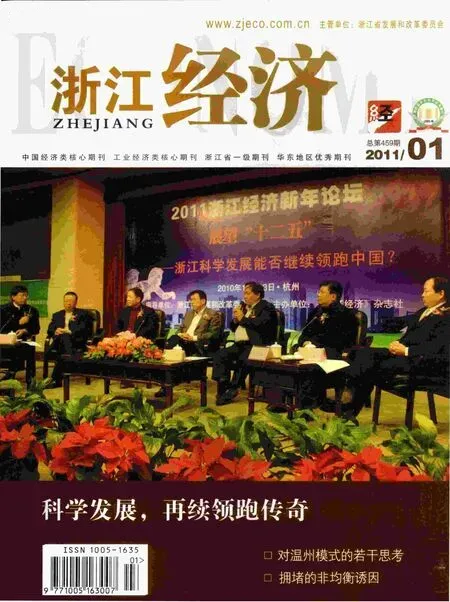關于制定“十二五”規劃若干問題探討
文/常修澤 丁凱
關于制定“十二五”規劃若干問題探討
文/常修澤 丁凱
【緣起】一位地區的同志說,規劃的“規”乃是二人見談,規劃的“劃”古漢語就是“畫”。前不久,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常修澤教授在廣東省中山市與中山市發展和改革局副局長丁凱同志就“十二五”規劃的若干重要問題作了交流。
如何把握“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層次和內涵
丁凱:“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個命題,應該說是中國的理論界和決策部門以及廣大人民群眾共同創造的一個概念。記得1995年中央曾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后來十七大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今天強調“加快發展方式轉變”,請問應該如何準確理解?
常修澤:2007年,我在一篇題為《中國發展模式論綱》的論文里,曾界定了“經濟發展方式”的三個層次:“窄方式”、“中方式”和“寬方式”。第一是“窄方式”。所謂“窄”,主要指“要素投入結構”,過去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和低效益”,所謂“三高一低”的粗放型增長,現在要倒過來,變為“三低一高”:“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益”。就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主要是由“粗放型”轉到“集約型”發展上來。
第二是“中方式”。除了“要素投入結構”以外,再增加兩個結構,一是需求結構——國家的經濟發展著眼于哪種需求,過去更多的是依賴于投資和出口,以后要轉變到以消費為導向,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協調發展這樣一個方式上來;二是供給結構或者說產業結構——過去比較偏重于用第二產業來帶動,以后一、二、三產業要協調發展,特別是要注重發揮第三產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的作用。
丁凱:吳敬璉先生最近撰文指出,用“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和出口)的說法分析經濟,來自于凱恩斯主義理論,這一理論認為經濟發生不平衡的原因是總需求不足,因此,就用擴大需求的辦法來解決。只要能夠把需求擴大了(常常是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短期調節手段),就能夠把增長的速度拉起來。但這僅僅是一個短期分析的框架,并不一定適合做經濟的長期分析。從長期來看,經濟發展還是要靠市場的綜合調節。這個觀點恰恰提示了加快轉變發展方式的迫切性。
常修澤:第三是“寬方式”。是超越經濟發展方式,一種“總體的”發展方式轉變,包括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生態等等,范圍更為廣闊。我現在正寫的《第三波轉型論》,研究未來幾十年中國的“轉型”問題,大體定位就在這一層次上。
丁凱:回到“十二五”上來,您覺得應該從哪一個層面來把握內涵?
常修澤:根據目前中國的階段以及世界新的發展動向,現在提的經濟發展方式,我建議定在“中方式”與“寬方式”之間,即在前面講的三個結構——需求結構、供給結構、要素投入結構的基礎上,再擴充三個,分別是城鄉結構、地區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這三個結構,既是社會發展問題,也是經濟發展問題。
丁凱:這樣,就可以從六個方面來理解“經濟發展方式”:從需求結構看,從主要依賴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增長轉向擴大內需比重,使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從供給結構看,從主要依賴第二產業帶動轉到一、二、三產業協調帶動上來,重點是要充分發揮第三產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的支撐作用;從要素投入結構看,從主要依賴物質資源投入促進經濟增長轉到依賴自主創新和科技進步上來;從城鄉結構看,在推進工業化和新型城市化過程中,推動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走向城鄉一體化;從地區結構看,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從收入分配結構看,加快推進收入分配制度的結構性改革,努力提高居民在整個國民收入中的比重,盡快扭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
未來“第三波轉型”基本方略是什么
丁凱:“轉型”是理解當代中國的關鍵詞,這既是一個歷史進程,又是一個當前語境。現在提“轉型”,至少有“小”、“中”、“大”三層含義:一是“小轉型”,就是指“體制轉軌”,即從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二是“中轉型”,即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分領域的轉型,比如,在經濟領域,遲福林教授就提出未來五年中國經濟面臨四大轉型,即從投資主導向消費主導轉型、從工業化主導向城市化主導轉型、從私人產品供給向公共產品供給轉型以及低碳經濟轉型。三是“大轉型”,就是您近年提出的“第三波轉型”思想,也就是涵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以及生態環境制度五個方面的“整體或全方位發展模式轉型”。
常修澤:“第三波轉型”只是自己的一家之言。從邊緣轉向前沿、由隔閡轉向交融、由不可持續到可持續,這是人類文明的期待。我的基本看法是六句話:告別邊緣,告別隔閡;走向復興,走向融合;興而不肆,融而不阿。
丁凱:“人本”理念是您的《人本體制論》一個核心思想。“十二五”規劃建議指出,“十二五”時期要“順應各族人民過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由此出發,您對未來幾年轉型發展有什么看法?我知道去年您曾撰寫過一篇題為《新階段中國發展基本方略探討》的研究報告。
常修澤:出于清晰、簡潔,我拎出八個字四個關鍵詞:“人本、綠色、創新、協調”。所謂“人本”,就是一定要把握把人的發展作為整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核心。整個國家的發展和改革要以人自身的發展作為一個核心問題,作為一個基本的指導性理念。所謂“綠色”,主要是針對當前世界面臨的氣候變暖以及國家所面臨的環境壓力,發展低碳經濟,建設低碳社會,實現綠色發展。可以通過技術創新、產業結構調整、環境政策調控以及資源環境產權促進環境保護。所謂“創新”,就是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由“加工基地”向“創新高地”轉變。所謂“協調”,應該尋求內(需)外(需)、產業、區域和城鄉四大協調。
丁凱:未來十多年,將是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重要時期。新能源和環境保護投資空間很大,如果能夠適時推進資源要素價格改革,改變過去傳統能源價格偏低、環境成本難以計入企業成本的做法,就可以使新能源和環境保護投資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常修澤:必須強調的是,當前發展方式轉變滯后主要是體制機制問題。由于這些改革的滯后,發展方式轉變在多方面尚未有實質性突破,某些方面的矛盾仍在不斷積累和深化。
丁凱:加快轉變發展方式,單單局限于經濟領域很難突破,必須把經濟增長、社會需求與政府轉型結合起來。
常修澤:我在那篇題為《中國下一個30年改革的理論探討》文章中曾提及,這個全方位的改革包括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環境制度五個方面,類似于奧運“五環”。總的價值取向是人的解放與全面發展。之下,“五環改革”中的每個“環”有各自的中心: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是經濟市場化;政治體制改革的中心是政治民主化;社會體制改革的中心是社會和諧化;文化體制改革的中心是價值先進化和多元化;環境制度改革的中心是生態文明化。在新階段改革操作過程中,要抓住“五環改革”之間的“交匯”性,各方面改革能夠協調配套,使之一體化;要增強“五環改革”的動力,超越利益集團的羈絆,注意防止“權貴”和“民粹”兩種現象,特別是“權貴”問題。
丁凱:我想起去年金融危機時候您講過的一句話:“加大投資解近憂,深化改革除遠慮”。
對地方“十二五”規劃編制有何建議
丁凱:當前進入“十二五”規劃編制謀劃的關鍵時期。目前,各地都在緊鑼密鼓地開展規劃編制工作。應該說,近年來,規劃體制是有所改革的,逐步建立國家、省(區、市)、市縣和總體規劃、專項規劃、區域規劃構成的三級三類規劃體系,但同時,地方尤其是市縣一級的五年規劃普遍存在內容空泛、針對性不強、重點和特殊不突出、操作性較差等問題,亟待加以改進。對此您有何建議?
常修澤:編制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尤其是地方的五年規劃,我主張規劃中要講“三種話”:第一種話是“全人類”的話,就是認清“人類文明”的大趨勢,例如國務院領導在聯合國講的有關“人”的發展趨勢;把握國際環境變化,如美國向太平洋戰略轉移、貨幣戰爭、氣候挑戰以及印度等國的崛起與競爭等。第二種話是“北京話”。這既是指了解國內環境的變化,也指貫徹落實中央的精神,從國家重大戰略取向的調整出發,來謀劃“十二五”規劃的戰略思路。第三種話是“本地話”。在一定意義上說,全人類的話和北京話都是標準模板,一個規劃編制的成功與否,更多決定于本地話說得好不好,決定于能否契合本地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實際矛盾和具體問題。要學習毛澤東同志《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方法和思路。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曾提出過一個著名的“三段論”研究思路:“不但要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還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戰爭的規律,還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抓住具體矛盾、特殊矛盾和主要矛盾。如恩格斯說的“這一個”,而不是“那一個”。
(常修澤: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教授、博士生導師;丁凱:東北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廣東省中山市發展和改革局副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