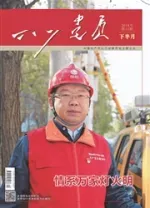黨外官員回歸
黨外官員回歸

假如發生在60年前,這條新聞不會像今天這般引人關注。
3月底,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公布了一條人事任免信息:甘霖已擔任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副局長,劉凡不再擔任副局長職務。甘霖是致公黨中央常委,劉凡是民革中央副主席,兩位非中共人士,在副部級職位上完成新老交替,并不多見。
從新中國建立之初占據中央人民政府的半壁江山,到“文革”后期無一人擔任部委正職,再到2007年致公黨中央副主席萬鋼與無黨派人士陳竺先后被任命為科技部部長與衛生部部長,黨外人士伴隨歷史的波浪而沉浮,如今逐漸重回政治舞臺的中心。
短暫的春天
因為在戰爭年代作出過巨大貢獻并享有崇高威望,新中國組建初期,宋慶齡、李濟深、黃炎培、傅作義等眾多黨外民主人士成為新政府組建時無法回避的人物。
近代史學者章立凡曾撰文描述當時景況: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京召開。在出席新政協的662位代表中,共產黨員約占44%,工農和各界的無黨派代表約占26%,各民主黨派的成員約占30%,基本上實現了中共的“三三制”原則。
在新政權逐步成長的初年,黨外人士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章立凡的父親章乃器參與了第一屆政協會議和新政權的組建。這位著名的民主人士是中國人民政協會議第一屆全委會常務委員,也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政務委員。長期從事經濟、金融工作的他不僅成為中央財經委員會委員,還于上世紀50年代初擔任中央人民政府糧食部首任部長。1957年,整風“反右”運動掀起,這一年,章乃器被打成右派并撤銷職務。他的命運自此轉折,數年后的“文革”更使他跌入人生的低谷,被剝奪財產、被打成重傷、妻子被打死。直到1980年,他病逝3年以后才獲得正式平反。
章乃器的命運幾乎是許多民主黨派人士命運的縮影。黨外人士的政治春天隨之結束。
兩個重要的文件
“文革”結束后,我們國家政治經濟逐漸復原。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有一部分黨外人士進入國務院和地方各級政府擔任領導職務。但是,黨外人士參政的總體困局仍未能突破。
真正的改變始自1989年。那一年,中共中央下發《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以下簡稱“14號文件”)。文件首次明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參政黨”這一詞匯也首次出現。
“14號文件”極大地推動了黨外人士參政議政的發展,并使之開始走向制度化軌道。在文件發布之前,國務院只有3名黨外人士擔任實職,隨后幾年,迅速發展至將近20人。
2005年,黨外人士迎來了另一次重要的轉機。這一年,中共中央頒布《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以下簡稱“5號文件”)。
在黨外人士參政方面,“5號文件”有非常細致的規定。文件提出,包括縣以上的地方政府到國務院有關部委領導班子都要選配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并明確規定“符合條件的可以擔任正職”。
在具體職務方面,“5號文件”規定為“重點在涉及行政執法監督、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緊密聯系知識分子、專業技術性強的政府工作部門領導班子”。
副職現象的復雜性
自從“14號文件”頒布之后,黨外人士參政的數量便穩中有升。經過這些年的發展,黨外官員尤其是副部級以上高官的總體狀況基本穩定。比如在國務院系統,除了萬鋼與陳竺兩位部委正職官員之外,還有10余名擔任副部級干部的黨外人士。這其中,包括水利部副部長胡四一,農業部副部長張桃林、國家統計局副局長徐一帆等人。
從這份名單不難看出,黨外高官分布廣泛,但仍然難以擺脫“副職現象”和“科教文衛現象”的桎梏。不可回避的首要原因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是當下中國的政黨制度,一把手多為中共黨員是制度必然。但與此同時,作為黨外人士參政長期存在的問題,副職現象背后隱藏的是黨外干部成長的巨大障礙。因為黨外干部的提拔大多是由副職到副職,直接跨過了不少層級,因此形成了一個黨內罕見的現象:火箭式提拔。不少黨外干部因此缺少實際的鍛煉,進而難以挑起正職的擔子。
2010年,中央針對此問題出臺了《2010—2020年黨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訓改革和發展綱要》(以下簡稱《綱要》)。專門就黨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訓工作頒布《綱要》,這在中共統一戰線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事實上,雖然民主黨派參政的巔峰是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但是當時民主黨派在政府任職僅集中在中央和省級政府,在基層力量十分薄弱。如今的黨外人士參政,則是要從基層開始培養,形成一個金字塔的結構。黨外干部的教育培訓,主要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共識教育,二是能力教育。
事實上,隨著這些年來社會矛盾的加劇,尋找共識逐漸被視為中國下一步如何發展的一個前提。而黨外人士幾十年后的重新回歸,無疑是執政黨尋找共識的一種努力。
(文/蘆 垚 據《瞭望東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