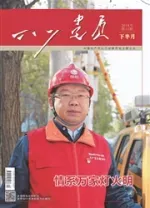十大極具影響力的中共同路人
十大極具影響力的中共同路人
《瞭望東方周刊》編輯部經討論,并用多種方式征求讀者意見,再經張少琴(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林少雄(上海大學教授、博導)等十多位專家學者評議,推出“十位極具影響力的中共同路人”。

廖仲愷 推動國共第一次攜手
對國共首次合作,廖仲愷起到了不可磨滅的推動作用。廖仲愷認為,“想要打倒帝國主義,非與共產黨親善不可。”他認為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是國民黨復興的關鍵。他信守兩黨的共同綱領,在重大政治問題上和共產黨人取得一致。
1924年1月28日,國民黨一大審查《中國國民黨章程草案》,一些代表在右派的慫恿之下,動議討論限制國民黨員加入他黨,實際上是反對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廖仲愷在大會上作了旗幟鮮明的發言,極力主張同共產黨合作。他指出:“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本黨一個新生命。”
張學良 巨款接濟紅軍
1935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的瓦窯堡會議上,成立了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由周恩來擔任書記,專門從事對東北軍的統戰工作。從1936年4月到12月,張學良接濟紅軍的款項共達76萬元。這些接濟,對處境困難的紅軍來說,無異于雪中送炭。
“西安事變”發生后,張學良在被蔣介石囚禁的困境中,仍然要求部下繼續維護同共產黨的友誼。他說:“我為國家犧牲了一切,交了一個朋友(指共產黨),希望各袍澤今后維持此一友誼。”
魯迅 共產黨的知己
陳獨秀贊賞魯迅的才能,說對魯迅“五體投地地佩服”;魯迅則認為李大釗儒雅、質樸、誠實、謙和,對李大釗因信仰慘遭軍閥政府殺害深表憤怒,在為《守常文集》寫的序言中,盛贊李大釗的革命精神,稱其文集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
1931年,魯迅結識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這是魯迅書贈瞿秋白的對聯,可見兩人之間友誼深厚。
在魯迅結識的共產黨人中,還有陳賡。在與魯迅的交談中,陳賡隨手畫了一張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形勢圖。這張圖魯迅一直保存,他甚至準備寫一部作品來反映紅軍戰斗情況。
黃炎培 可靠盟友
辛亥革命時期,毛澤東聽過黃炎培的講演。一句“讀書不是為了做官,而是為了學到人家強國的本領,為民族效力”,使青年毛澤東深受鼓舞。抗戰時期,在重慶,黃炎培與周恩來關系最為密切,常邀請周恩來到他辦的“中華職業學校”講演。黃炎培稱贊周恩來:“乃天下難得奇才也。”
1945年,黃炎培等人組織成立了民建,民建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可靠盟友,為新中國成立立下了不朽功勞。
霍英東 為中共做香港護駕人
抗美援朝期間,在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全面禁運、港英當局武力“緝私”的情況下,霍英東在香港組織了頗具規模的船隊,為祖國運送了大量急需物資,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作為香港最著名的愛國人士和實業家之一,他為確保香港平穩過渡、順利回歸和長期繁榮穩定作出了突出貢獻。
何賢 無論如何都要同共產黨交往

澳門特區首任行政長官何厚鏵的父親何賢有“澳門王”之譽,為澳門的穩定和繁榮作出了貢獻。何賢說:“要搞好澳門人的生活,要令澳門生意繁榮,無論如何都要同共產黨交往。”1954年,他當選為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
史沫特萊 中國共產黨的辯護人
1936年,美國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在中共地下黨員劉鼎的安排下到達西安,等待被邀請前往延安。“西安事變”發生5天后,史沫特萊在與周恩來進行了簡短的交談之后,開始每晚在張學良的司令部進行40分鐘的英語廣播,概述當天西安事態的發展,并報道有關內容。西安的廣播,使史沫特萊被貼上了“中國共產黨的辯護人”的標簽。她的《中國紅軍在前進》等專著,向世界宣傳了中國的革命斗爭,成為不朽之作。
斯諾 他是一個象征
1936年7月15日,毛澤東正式邀請斯諾到他的窯洞里談話。經過撰寫、翻譯,斯諾發表了后人看到的唯一的由毛澤東自述的《毛澤東自傳》。1937年10月,他的《紅星照耀中國》出版。他和他的著作以巨大的國際影響,成為中國共產黨真誠友人的象征。
斯特朗 “紙老虎女士”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生中6次訪問中國,都是在中國革命的緊要關頭。她有一個“紙老虎女士”的綽號,因為就是在與她的談話中,毛澤東首次提出了“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
庫恩 告訴西方世界“一個真實的中國”
羅伯特·勞倫斯·庫恩在中國廣為人熟知的身份是作家,而他其實是一位國際投資銀行家。2005年,庫恩的著作《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成為中國國內暢銷書。2009年,他關于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新書《中國30年:人類社會的一次偉大變遷》問世。
庫恩常被稱為“當代斯諾”,但他并不認可這個稱謂。他一再強調,他只是想告訴美國人和西方世界“一個真實的中國”。
(文/蘆 垚 據《瞭望東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