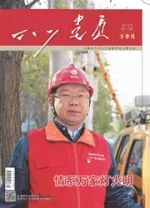六十年前的『中國道路』
六十年前的『中國道路』
1949年11月16日,新中國剛剛宣告誕生一個半月,就舉辦了一個國際會議——世界工聯亞洲澳洲工會會議。劉少奇以會議主席團主席的身份,在開幕式上首次提出了“中國道路”的概念,并概括了這條道路的基本公式:(一)統一戰線;(二)共產黨領導;(三)武裝斗爭。
劉少奇斷言,這一道路不僅在中國適用,對世界落后國家和民族同樣適用。劉少奇告誡與會亞洲各國代表,重要的問題是要建立革命的軍隊。但是,除蘇聯代表團外,與會代表多半是以合法的身份,經過合法的渠道,從資本主義或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來的。公開號召各國代表回國后開展武裝斗爭,推翻帝國主義和本國統治者,讓這些代表聽得膽戰心驚。不少代表紛紛表示異議甚至批評,會議的決議也完全沒有響應中共的號召。
然而,斯大林在得到報告后,認可并力推“中國道路”。斯大林迅速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來推動亞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包括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人走“中國道路”,即實行武裝奪取政權的方針。1950年1月,莫斯科先后對日共和印共的斗爭策略提出公開批評,要求日共和印共開展武裝斗爭。
這一波推廣“中國道路”的熱潮,因斯大林去世戛然而止。中共也先后勸止了東南亞各國的共產黨和分裂組織反對本國政府的暴力行動,一度全面推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力圖與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政府發展外交關系。然而,改變“輸出革命”的方針,并不等于改變了“中國道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觀點。當蘇共中央領導人赫魯曉夫全面提出“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和平過渡”的政治外交方針之后,毛澤東對這些新的蘇聯領導人的不滿也逐漸溢于言表。中蘇兩黨意識形態的分歧逐步加深。
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中國把聯絡和援助的目標全面轉向了各國激進的小組織,采取接進來、送出去的方法,在中國內地建立訓練基地,傳授中國革命的理論、經驗以及武裝斗爭的技術和戰術,再援以金錢和武器,送他們回去開展革命。
改革開放后,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對外奉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停止了對開展武裝斗爭的緬共等組織的支持。
(文/楊奎松 據《同舟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