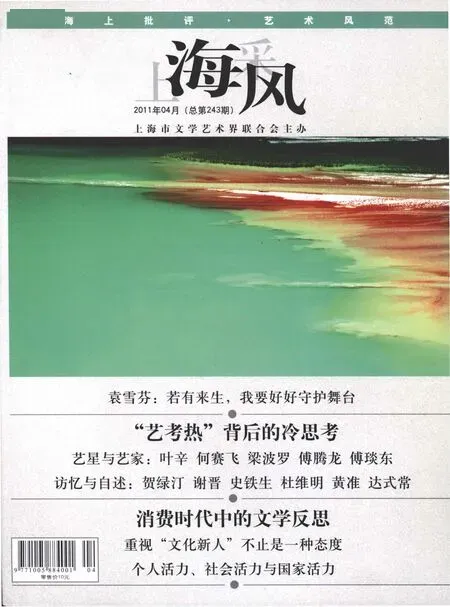錯位的藝術教育
——“藝考熱”背后的冷思考
文/本刊記者 胡凌虹
錯位的藝術教育
——“藝考熱”背后的冷思考
文/本刊記者 胡凌虹

武珍年:
電影里各色人物都有,招生時也應該講究平衡,漂亮的要招,但是長得不太好卻有才的“歪瓜裂棗”們也需要。這樣才能很好地配置人才資源。

榮廣潤:
真正好的藝術教育是要“教”“練”結合,要注重文化素養的好的熏陶和培養,通過反復的練習讓學生掌握技巧,同時讓學生明白后面的美學原理和必備的藝術修養,同時在整個學習過程中要激發學生的天性和創造力。

趙寧宇:
當表演教育上升為一種學歷教育之后,就必須遵從大學教育的規矩和規律。而這種規矩和規律,是由大學教育中為數更多的知識講授型的專業形成和決定的,而非表演藝術以及其他實踐性藝術——和知識講授型的專業比起來數量少得多,范圍窄得多,聲音小得多——所決定的。因此,大學教育對于表演教育,形成了諸多不利的影響。

陳丹青:
藝術學院應該招一些瘋子,而不是那些成績優秀的好孩子……我們不能單憑英語分數就把一個孩子粗暴地拒絕在門外。對一位想當藝術家的青年,今日的考試是不折不扣的荒謬和侮辱。

劉大鴻:
現在的藝術類招生,表面上看非常嚴格,很數字化,很公平,而本質上卻一塌糊涂,學生的個性和創造力被抹殺了,很難招來真正有才華的學生。
春寒料峭之時,龐大的 “藝考大軍”不遠千里、不惜代價擠上“藝考”獨木橋,其熱烈程度堪比國考。而同樣與國考類似的是,夢想照進現實者寥寥,大部分考生成為了“陪考”,淘汰的原因各異,其中不乏頗受爭議的評判“標尺”。
藝考奇觀
“每到冬天,藝考生們就考瘋了,從南到北,從西到東,全國各地的考生們坐飛機乘火車趕往北京,各個院校也都在北京設攤搶生源,蔚為壯觀。今年也是如此。我們同濟大學電影學院在北京電影制片廠設了點,全國共招26名學生,北京考點最多也只有五六名,可報名的考生竟有2000多名。很多院校規定若要調整面試時間,需要加付50元,可眾多考生還是紛紛掏錢,因為他們大都報了好幾個學校,忙著趕場子,有些同學一下子趕10到20個場次不等,不同考點考試時間重合在所難免。”知名導演、同濟大學電影學院電影制作系教師武珍年(此次幫助表演系招生)向筆者介紹不久前的招生情況,“我還清楚地記得我們考場的最后一個考生,一張灰白灰白的臉,疲憊地坐下,拉桿箱往旁邊一放。她剛在青島考完就坐火車直奔過來。這類拎著箱子直接趕來的考生不在少數。此中,家長有陪,也有不陪的,凡陪同的無不大小行囊拎著背著,在寒風中等候著,那顆緊張的心全拎到了嗓子眼;沒有來陪同的也是手機全天候開著,隨時接孩子遠方來電,茶飯不思,日夜不眠;一次在考場,我們就看到一個落榜的考生和他的母親抱頭痛哭,那副揪心的摸樣,讓在場的考官無不難受地趕緊躲避,不然,自己的那顆心也將隨著啼哭而要碎裂了……啊,這真是一場情感的大廝殺哪!”武導說完這段話,禁不住長嘆了一聲。
“我已經去過江蘇、北京等地,然后來到上海,一個多月來共考了17場,都快變成全國巡演了。”一名山東的藝考生說。他從春節前就開始進入考試狀態,而一個多月連考17場的頻率并不算高,為了使藝考更有把握,不少藝考生都采取了“全面撒網”的策略,藝考線路遍布大江南北,打“飛的”、坐十幾個小時的火車成為了一兩個月內的常態。
2011年春寒料峭之時,可以用“轟轟烈烈”一詞來形容正緊鑼密鼓進行著的藝術類考試。據報道,北京電影學院今年只招生488人,但報考人數約2萬人,比去年增加7000人左右;其中,今年減招至30人的北電表演系,報考總人數已達4392人次,這意味著99%的學生成了“陪考”。上海戲劇學院2011年招生計劃數為469人,其中,全國共有3006人爭奪表演系50個招生名額,錄取比例達到60:1;而今年的主持專業有2138人爭奪20個錄取名額,錄取比例達到100:1。此外,中國傳媒大學700個招生計劃也吸引到全國兩萬多人報考,比去年增加了2000多人;中央戲劇學院計劃招收591人,其中本科招291人,而本科招生網上報名超過14000人。可見,藝術類考生高考錄取率遠低于普通類高考的錄取率。“如果參加普通高考是走獨木橋,那么參加藝考相當于‘走鋼絲’。” 一位考生家長如是說。

為了走這根“鋼絲”,很多考生與家長反目,甚至以離家出走相威脅,最終父母不得不妥協。為了增加考試“籌碼”,很多家庭不惜重金,有考生單獨請專家一對一輔導,10天就花了上萬元。央視的一項調查稱,在北京的藝考培訓大軍中,90%以上是外地學生,這些學生中有三分之二在高三下學期到北京參加考前培訓。按最低平均每月3200元計算,一個學生半年培訓下來,僅學費就要花兩萬元。而用在購買學習用品、租房、生活開支等方面的費用,更是一個不小的數字。
照此看來,藝術學院的考官們應該興奮不已,那么多的考生向藝術“投懷送抱”,不畏路途艱辛,不惜奢投金錢。然而考官們卻紛紛感嘆,考生的有效數量一年不如一年。據悉,部分藝考高校不少專業的初試淘汰率高達50%以上。這種現象的出現,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很多成績不佳的考生把文化分數線低的藝考當成上大學的敲門磚和救命稻草,他們并沒有做充分準備。但是,也有業內人士指出,“藝考”中諸多奇特的條條框框把一些專業優秀的考生也拒之門外。
表演系盡招帥哥美女?
一到各大院校表演系招考時,眾多紙質媒體、網站都用“美女云集”來描述。表演系招收的都是帥哥美女,那些外形條件不太“給力”的考生成功的幾率很小,似乎已漸成共識。
“這絕對是個誤會。”很多相關人士辯護道。北京電影學院表演學院院長陳浥解釋,電影表現的是生活,生活中什么人都有,考官對形象雖有一定的選擇標準,但完全基于電影制作的需要,而且更看重學生的信念、想象力、激情、表現力等藝術素質和人文素質。然而,縱觀北電、上戲、中戲等院校各級表演班的合影,哪張上不是一溜串的帥哥美女?“完全基于電影制作的需要”,恐怕才是真正的關鍵點。以前,中戲、上戲的表演系,主打戲劇表演,然而隨著舞臺劇的相對式微,影視劇的蓬勃發展,很多院校的專業方向已改成了“戲劇影視表演”。如今當演員的哪個不想去拍影視劇?即便編制在話劇院團,但凡有條件、有機會,都想著法兒跑往影視圈,因為成名快,片酬高嘛。因此,學生以后能否成為影視明星,也成為藝術院校表演系招生的“潛標準”。一些院校表演系招生時,從初試開始,就有一臺攝像機跟蹤拍攝,到了三試時,考官面前就會放上一臺大屏幕的監視器,方便考官從鏡頭里考察考生。鏡頭一拉近,演員的面部輪廓、表情一下子被放大,考生稍有缺陷,立即暴露無遺。上戲表演系主考教師洪彬認為:“做演員的,長得好看不是罪。我們招的是演員,形象漂亮,讓觀眾賞心悅目,有什么不好呢?”在后工業化時代,審美標準日趨單一化,“是否好看”已經成為幾乎所有院校表演系評判考生的重要標尺。據說,為了搶奪那些“第一眼”帥哥美女,各校的主考老師往往會給予各種明示與暗示:“只要你文化過關,我們肯定要你。”然而,也有考官替那些專業能力強卻長相不佳而遭淘汰的考生鳴不平的。
“去的話,估計也難上,你就當多一次體驗吧!……”放下電話,武珍年轉過頭跟筆者說,“剛打電話過來的是一個跟我很熟的考生,他告訴我北電的面試沒有通過,問我還要不要去中戲試了。他肯定沒戲,我早就跟他說過。一米八的個子,氣質也非常好,上次他到北京來找我,穿著很得體,對色彩非常敏感,比同齡人要成熟,而且跳舞好得不得了,那個柔韌度,形體老師也很稱贊,但是——”武珍年話鋒一轉,嘆了口氣:“不可能錄取,他太胖了,有260斤。你不知道表演系的標準里有著一些約定俗成的觀念,形象上要端正。如果你有缺陷,我們在面試時會在形象欄里標注,什么鼻子太長、大小眼、朝天鼻子、斗雞眼、招風耳、沖下巴、大腮幫、歪嘴巴等等,這些都不太可能錄取,更何況這個考生太胖,不要說二試、三試,就連初試一旦出現一定是質疑聲大噪:‘你來干什么?!’。有時我也會自責,干嘛這么評論人家,都是父母給的相貌,父母絕對不可能這樣來評價他們的孩子的,因為在父母的眼里哪怕是殘缺的孩子都是最可愛的,最美麗的。而我們卻這樣地‘評價’,你有什么權利?!可是沒有辦法,就是要五官端正哪,就是要你去挖掘孩子的缺陷。設想一下,當年的姜文如果用這樣苛刻的標準要求他,現在就沒有一個大明星了!他的那個招風耳,小豆眼,就必定把他擋在考場之外,其實當年的北電就沒有錄取他,而是后來中戲的張仁里老師據理力爭要下他的。盡管有案證明,但這個標準已經成為約定俗成的東西,一個不變的常理。你不能說它沒有一定道理,電影上沒有帥哥美女確實不行,但問題是有些特殊的特別的人才也因此被拒之門外,這就可惜了。每次面試時,我內心都很糾結,但是沒有勇氣去打破這個規則,這成為了一條硬杠杠,誰都很難逾越。”
北京電影學院教師隋蘭在微博上寫道:“我們很認真嚴肅地對待自己的工作,手里掌握的生殺大權決定的是一個孩子一生的命運,這份德行我們絕不敢輕視,有的考生內在素質好,外形差,明知道他過不了還是讓他進三試,多給他一次展示自己的機會!有的形象真好就是不會演,我們就耐心地啟發希望她能開竅!”言語間對形象的偏好非常明顯。很多老師并非刻意,但“首先要挑形象好的”已經成為思維定勢。
各個院校的表演專業招考內容中大都有語言、聲樂 、形體、表演等各方面的考核,講究的是綜合素質。北電表演學院院長陳浥強調招生絕非帥哥美女“選秀”,更不是挑選“攝制組”要的人選,更看重的是考生的藝術素質和人文素質,然而在北電2011年招生簡章報考條件一欄中赫然寫著“報考表演專業考生雙目視力均應在5.0以上(經佩戴隱形眼鏡矯正4.8以上,新視力表);男生身高不低于1.72米,女生身高不低于1.60米;無肢體畸形,體表無疤痕、紋身、胎記及皮膚病;報考表演專業的考生,參加專業考試時,一律不許化妝;報考表演專業進入三試的考生,須參加專業體檢(表演學院自行安排)”等須知。而在上戲的招生簡章的報考條件一欄中有“身體健康,無生理缺陷,無色盲、色弱。表演專業要求體形勻稱,五官端正,口齒清楚,普通話較標準,兩眼裸眼視力一般不低于0.8”等要求。可見,藝術院校已經白紙黑字地告知,暫不論你們有多少表演天賦,如果你長得太矮、太胖、太瘦、五官不端正、是色盲、色弱……就要有點自知之明,不要來報考了。
武珍年認為:“電影里各色人物都有,招生時也應該講究平衡,漂亮的要招,但是長得不太好卻有才的‘歪瓜裂棗’們也需要。這樣才能很好地配置人才資源。而且一些‘歪瓜裂棗’往往因為某些欠缺,會加倍地努力,表現更加出色,走得也更遠。”

“兩課”考試是對藝術的侮辱?
“招生時我根本就是傀儡——我無法決定我要什么學生,當老師那7年,甚至連考生也見不到,外語政治不通過,考生沒資格到我面前瞧一眼。他們只有一個選擇,就是花爹媽的錢,買張火車票到北京考試,然后再買一張火車票,打道回府。”陳丹青感嘆著回憶道。當年他是以英語零分、專業高分進入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系研究生班的,然而二十多年過后,他的后輩們卻沒有了他當年的幸運。
2000年,在盛邀之下,陳丹青回國加盟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本想“一展拳腳”卻處處受牽制。2000年5月,全國首屆藝術學院博士生招生在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舉行,這也是陳丹青第一次招生。二十四位各地考生中,五名入圍,然因外語不過關而擱置。院方為支持陳丹青首次招生,允許以博士課程訪問學者名義,招入五位學生。2001年,五位訪問學者完成博士論文選題,轉為正式博士生,可因外語考試再度失敗,不得不結業離校。之后的幾年,無論是博士招考、還是碩士招考,大部分考生們均在“兩課(政治和外語課)”上敗下陣來。
“專業前3名永遠考不進來,因為外語達不到那個分數。藝術學院應該招一些瘋子,而不是那些成績優秀的好孩子……我們不能單憑英語分數就把一個孩子粗暴地拒絕在門外。”陳丹青憤怒地感嘆道,“對一位想當藝術家的青年,今日的考試是不折不扣的荒謬和侮辱。”
為了給火爆的藝考降溫,2009年教育部將藝術類本科文化課控制分數線提高了5個百分點。這一改革帶來的直接變化,是藝考招生各專業方向文化課錄取分數線的明顯提高,各院校錄取500分至600分甚至更高分數段的考生數量在不斷增多。一些學校還深入重點高中、示范高中開展宣傳,吸引優秀生源參加藝考。以北京電影學院為例,其今年本科專業考試的28個專業方向中,按文化課成績錄取的專業方向占到了25%以上,而單純按專業成績錄取的專業正在減少,按專業成績與文化課成績綜合排序錄取的專業在增多,有的專業則是在專業合格基礎上,完全按照文化課成績排序錄取。此舉一大理由是,藝術需要天賦,更需要文化素養。這很有道理。問題是,現今的填鴨式教學與更多地拼背功的文化課考試能考量出多少的文化素養?“‘兩課’成績被統稱‘文化課’,簡直太荒謬了!外語能力指什么?紐約乞丐,滿口英語。‘政治’指什么?孫中山說,‘政’,眾人之事也,‘治’,管理眾人之事。如果我們認同此一定義,美術系大學生都要從政么?”陳丹青質問。
“我參加過一次學校美術類本科招生專業課打分,籃球場那么大的一塊地方,擺著上千張畫,老師看幾眼就過去了,通常在幾秒鐘之內,一個學生的命運就被決定了,根本就不當一回事,考生水平又這么差,怎么能當一回事?之后我也就再也不參加招考了。”上海師范大學美術學院教授劉大鴻坦言。在他看來,現在的藝術類招生,表面上看非常嚴格,很數字化,很公平,而本質上卻一塌糊涂,學生的個性和創造力被抹殺了,很難招來真正有才華的學生。“以前的話,是先寄自己的作品,我當時考浙江美術學院時寄了很多作品,老師一看就知道我的整體水平,就給我發了準考證。考試時,我的色彩成績一般,但是我拿出了平時的習作給考官看,她一看覺得,其實還不錯的,只是考試沒發揮好,就把這個情況帶回去,放入了好的一檔。可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藝術類招生是很靈活的。此外,當時除了要考素描、色彩,創作也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比如給你一個題目創作。但現在很多學校都沒有這項內容了,要么考真人頭像、石膏像,要么是靜物、色彩,大家都知道是這幾樣,考前班就好辦了,一種模式訓練,不再像以前那樣更注重創作。”在劉大鴻理想中,最好的招考方式應該是,把優秀的老師推出來,做宣傳,真正想學藝術的學生應該是擇老師應考而不是沖學校應考;老師則應該到考生家里去,翻一翻以前的作品,看看家庭環境,聊聊天,這些年來干些什么,怎么過的,為了驗證,再畫個東西,測試一下水平,就可以決定是否招生了。
美術類、表演類考試中的“標尺”只是藝考眾多“標尺”里的典型,在這些“鐵面無私”的標準下,很多“偏才”“怪才”被擋在了高等學府之外。
“藝考”只是藝術教育的“排頭兵”,在經過各種“標尺”丈量后,順利邁進夢想中的高等學府的學子們,依然需要面對各種考試、各種規章制度、各種評價標準……
一格一格育人才
“走進教室,發現孩子們都是一路考試過來的傻孩子,表情茫然。聽說我教油畫,有些孩子也想跟我學。但是油畫這玩意兒今天畫完,明天會干掉,上午畫完了得下午接著畫,好比慢慢燉一鍋湯,熄不得火。可是等我下午習慣性地走到教室去查看時,發現教室里沒有人,只剩下一兩位外國留學生,中國學生都走光了,因為下午的課早排滿了——政治課、英語課、體育課、電腦課等等。第二天上午孩子們再抹開顏料畫,顏料全干了,全部重頭收拾——沒有辦法,課程名目冠冕堂皇,反而美術學院的美術課,最次要。”陳丹青說道。
“回憶二十多年前,至今我不記得在學兩年間校方講過什么科研與教學:上課頭天,我們圍著靳先生團團坐好,他就說:‘文革’過去了,大家靜下心來,不搞運動,不搞教條,好好搞學術。什么是學術呢,靳先生忽然伸出右手掌,一句一句道:你們看,手!皮下面是肉,肉里面是筋,筋里面是脈絡,是骨頭。你畫這只手,就要畫出皮、肉、筋、脈、骨!……
有一天,林崗老師忽然叫我出教室:‘丹青啊,就像你當知青那會兒大膽畫,你怕什么呢!’他在過道的暗影里很殷切地對我說,急得眉毛皺起來。是的,在學兩年,我能記得的教誨就是這么幾句話。藝術教學是什么呢,藝術教學就是幾句話——雖是幾句話,還看誰在說。”陳丹青有些深情地回憶道。
在劉大鴻看來,現在藝術教育最主要的問題是全部行政人員加“半瓶醋專家”把所有資源都占了。1985年劉大鴻到大學任教,當時一個教授配兩個助教,“不知猴年馬月教授們都成為了光桿司令,助教紛紛獨立上課,一個教授要請人幫忙,得自己掏錢。單用表格就可令教授們團團轉,舉手投降,苦不堪言。代之而起的政工輔導員群體卻占了很多位子和資源,他們把所有的利益都抓著,怎么辦考前輔導班,怎么錄取,專門有人搶這碗飯,控制完招生把一年級的學生拉到新校區,封閉一年,考進來的學生本來就很傻,結果到了那邊以后又傻一年,二年級回來以后,一時很難恢復,三年級又要去找工作,四年級就要畢業了。我碰到過一些蠻有靈氣的學生,等畢業時什么也不是了。而且大部分的學生看問題都很偏狹,認為畫畫就是畫瓶子、罐子、人體,如果你出個題目,學生就有怨言,覺得藝術就是天馬行空,有命題就不能接受,就不藝術。”
“所有的教學都被教務處規定好了,在時間、地點、課程內容、教學階段等等細節上,全都預先嚴格規定了,排在表格里。我看不出我的‘主觀能動性’在哪里。我不再是我,只是頂著教授的帽子,按照表格的安排,帶帶研究生,好像在放羊。”不愿在體制內混飯吃,也不想違背自己性格的陳丹青于2007年憤然離開,而處于類似困境的劉大鴻則選擇了做體制的“釘子戶”,持久“抗爭”,實踐他的“單位美學”。

劉大鴻的雙百工作室
在美術學院,傳統教學模式以培養寫生能力為主,考量的是如何把人畫得像,技術性的成分占了很大比重。因不滿于這種刻板的教學模式,劉大鴻與上師大油畫系主任黃啟后在著名畫家戴敦邦的啟發下,于2002年成立了“雙百工作室”,開始了不同于常規美術教學大綱的藝術實踐。“雙百”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意圖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綜合素養。很快教學上就有了成果,劉大鴻帶領畢業班學生創作的《新上海百多圖》《新點石齋畫報》《新良友》等系列得到了廣泛肯定,成為了美術教育方面的成功范本。然而“雙百工作室”教學理念的成功,大大觸及了傳統美術教學模式,也引來了身邊不少同行的爭議與微詞。2003年,雙百工作室的02級油畫本科班被硬劈成了兩個班,原因在于學院院長不滿工作室的獨特教學法;2006年,雙百工作室本科學生遭遇“論文門”,全體被判為不及格,原因在于指導老師劉大鴻要求每個人以四年的專業學習實踐活動為基礎寫作,真實體現自己的理論水平,而在這個要求下學生撰寫的論文被院方認為,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論文,不具備應有的觀點和學術性。劉大鴻對此“絕對不認同”: “一個美術學院的本科生,哪有能力自己寫出有學術價值的論文?還不是要去抄襲?等于是嚼人家嚼了一百遍的饃。”他認為對創作藝術的人來說,文章寫得真遠比寫得“學術”更重要。最終,隨著眾多主流媒體的廣泛報道,校方不得不介入,重新審查論文,并讓學生過關。然而,這只是短暫的勝利,抗爭之路漫漫修遠。
“我已經兩年沒有被安排課程了。”日前,在雙百工作室劉大鴻無奈地向筆者抱怨道,轉而又有些振奮地說,“但我有自己的辦法,就是把自己牌子掛上,自己上公開課,看你們怎么辦?”被邊緣化的劉大鴻選擇了“自立門戶”,他在透明玻璃圍起的美術學院一樓大廳展廳內樹了一塊牌子:劉大鴻與雙百工作室。“我喜歡這種透明的、開放性的空間,只要愿意,誰都可以進來翻書、看畫,有誰愿意跟我學畫,我也隨時愿意指導。學藝術其實就應該這樣,需要大量閑聊、溝通,談自己的感覺。只可惜現在真正想學藝術的學生越來越少,一個班也就一二個。很多學生好奇但是不敢推門進來,可見學生學藝術的欲望有多少。不過,我還是希望,年輕人,能救一個是一個,哪怕沒有一個學生找過你,但是他每天路過,看過某個場景,可能會對他以后的成才有幫助。”劉大鴻感嘆道。即便前面的路似乎越來越艱難,他表示依然會堅守在大學這個“單位”里尋找新的創新的可能。
升為學歷教育后藝術教育的錯位
“當表演教育上升為一種學歷教育之后,就必須遵從大學教育的規矩和規律。而這種規矩和規律,是由大學教育中為數更多的知識講授型的專業形成和決定的,而非表演藝術以及其他實踐性藝術——和知識講授型的專業比起來數量少得多,范圍窄得多,聲音小得多——所決定的。因此,大學教育對于表演教育,形成了諸多不利的影響。”中國傳媒大學影視藝術學院導演表演系教授趙寧宇指出了藝術教育“束手束腳”的一大根源。
“大學教育的體系從各方面來看都是好的,但有一個致命的問題:一元化。人類的社會生活形態是多元化的,人類的生存技能是多樣化的,培養教育人類的大學自然也應該是多元化的。一元化,必然造成用張家家規管李家事的錯位。所有熟悉大學教育的人都熟悉這些詞匯:實驗室,實踐性課程,課件,考試AB卷。對于理工科或者普通文科來說,這些教學概念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但是應用在表演教學上,就有些令人啼笑皆非了:這些概念基本上不適用于表演教育和若干相關的藝術教育。表演教育和實驗室有什么關系?表演教育的全部都是實踐性課程,如何作為稀缺物單獨標注?表演教學哪里用得上課件?表演考試沒有試卷,又何來AB卷;不是命題答題的考試,而是技能檢驗的考試,又怎樣出得來AB卷?如此等等。問題還不僅僅在于這些管理用語的不恰當,而在于對于大學表演教育的認識和定位的偏差。這就是一元化的后果,事實上,完備的教育體系應該具備多元化的量化評估方法,管理上的滯后實際上還是觀念上的滯后,這種滯后對于表演教育質量的影響是很明顯的。”
上海戲劇學院前院長榮廣潤也有類似的觀點:“其實藝術教育存在著兩種誤區,一種是把藝術教育等同于普通大學的教育,忽視藝術教育的特殊規律。培養藝術人才不光是讓他‘懂得’,還得讓他‘進去’。演員口齒清楚,這需要他臺下不知道念多少遍繞口令才行,形體能力需要每天早上六點鐘起床來練功才能保持。藝術教育有特殊規律,這也是為什么藝術院校要一對一或者小組上課。”趙寧宇認為,表演教育的教學進程很難用固定的教學大綱和教案上的文字來說明,因為表演藝術不能用文字來說明,而只能看‘行動’的結果。在教學大綱和教案上,可以體現出每一個科目、每一個階段、直至每一節課上教授的內容,但是這些內容并不能固定。每一個學生的情況不同,具體的訓練方法都不一樣,如果按照條文整齊劃一的同樣訓練,最終什么人才也培養不出來。這就是表演教育的特殊性,“因材施教”是表演教育的第一原則。但是,由于大學學歷教育的條條框框要求,第一原則很難貫徹,這也是表演教學水平下降的原因之一。
在榮廣潤看來,藝術教育的另一種誤區在于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過于忽視文化素質的培養,另一種是過于忽視對創新能力的培養,很多老師都希望手把著手教,甚至是你學我老師的樣子,結果學生技藝上不錯,但是創造能力不足。“真正好的藝術教育是要‘教’‘練’結合,要注重文化素養的好的熏陶和培養,通過反復的練習讓學生掌握技巧,同時讓學生明白后面的美學原理和必備的藝術修養,同時在整個學習過程中要激發學生的天性和創造力。現在我們的藝術教育中‘單打一’的現象還是比較普遍,能成為明星的人并不少,能成為大藝術家的人很少,這也是藝術教育的一大誤區。”

對于教育體制的諸多弊端,不滿者眾多,但抗爭者寥寥,各種批評只是風中的雜音,飄過即逝,對于日益龐大的體制而言,如隔靴搔癢。究其原因,背后的產業鏈、趨利主義的社會環境成為了“幫兇”。
何來培養大師的土壤?
“有天賦的人總是被那可嘆的分數拒之門外。想象力是無法培養的,而藝術最最需要的想象力早已被我們‘偉大’的‘應試教育’扼殺光了,那些考試真正公平嗎?”陳丹青痛斥道。在他看來無視教育規律與成才規律的考試制度、教學制度,徒具形式,反而削弱了藝術學生的人文素養。“考生中有幾個真正鐘愛藝術?這個時代的人缺乏夢想與追求,找個好大學,找個配偶,生孩子,再讓孩子接受應試教育,渾渾噩噩過一生……學院的教條主義培養出一撥撥所謂美術工作者,但誰是藝術家?”
事實上,這不僅僅是藝術家培養的問題,也是整個社會有創新力的杰出人才匱乏的癥結所在。藝術教育的問題只是整個教育體制頑疾的部分表征。
“回過頭來看,這么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 2005年溫家寶總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學家錢學森時,錢學森曾發出這樣的感慨。近些年來,大眾也在詢問:除去那些自我炒作、媒體鍍金的所謂“大師”外,真正的科學大師、文學大師、經濟學大師等在哪里?泱泱大國為何久久培養不出諾貝爾獎獲得者?
讓我們先來看看大師們誕生的土壤:錢偉長數理化加起來才25分破格進了清華大學, 臧克家數學零分進了青島大學。早年的清華國學院有一個傳統,每個星期六導師們都會跟學生有一個“同學會”,包括王國維、陳寅恪、梁啟超這樣的大師都和學生一起交流、一起分享。學生們也可以隨時進入導師的辦公室、工作室請教。
再看國外,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約翰·納什早已是聞名世界的大牌科學家,然而正當他的事業如日中天時,得了嚴重的精神分裂癥,而納什所執教的普林斯頓大學依然容納了他。于是,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生和學者們總能在校園里看見一個奇特而沉默的男人在徘徊,偶爾在黑板上寫下數字命理學的論題。他們稱他為“幽靈”,他們充滿愛心地想,這個“幽靈”是一個數學天才,只是突然發瘋了。如果有人敢抱怨納什在附近徘徊使人不自在的話,會立即受到警告:“你這輩子都不可能成為像他那樣杰出的數學家!”正是這樣一個寬容的環境,讓納什逐漸恢復健康,繼續鉆研,并于199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然而當時空轉換到現在日新月異的中國,一條條標準線以堂而皇之的“公平”面貌將一些特殊考生拒之門外。這是不幸,但有時也是幸運。試想倘若韓寒不退學,老老實實地考上某大學中文系,規規矩矩地上著除專業以外的英語、計算機、思想政治等諸多課程,并試圖門門優秀拿獎學金,就一定沒有作家韓寒了。而教師們呢,在各種考評制度下,忙于應付的是各種表格,對學生的培養也轉換成了對于課程的負責。于是,很多老師上完課課本一夾再不見蹤影,哪會耐著性子聽學生無休止的追問?珍惜時間寫論文評職稱才是上策。
“今天的社會現實與文化狀況,何似當年?而當年可貴可學的一套,都給廢了,譬如擇優錄取業務尖子,便是教學良策,雖遭‘文革’批判,八十年代恢復高考,也還走老路,立馬生效,問題出在九十年代,尤其是新世紀以來。”陳丹青感慨道。
價值趨同的大環境是教育體制頑疾的溫床
錢學森指出:“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針對中國教育體制的頑疾,已有不少批評性和建設性的文章,然而教育系統的改革卻始終如“老牛爬坡”,究其原因,這背后有著龐大的利益鏈的牽制。
譬如,在“藝考熱”高燒不退的背后,是連年來高校藝術類專業招生不斷擴大,而在招生計劃擴大的背后,則有辦學的利益驅動。據估計,全國半數以上的高校均開設有藝術類專業。在一些辦學經費緊張的地區,低投入高產出的藝術類專業更是成為一些高校賺取學費收入的捷徑。
而擴招的結果是,連名校表演系畢業的學生們,大部分都在跑龍套或轉了行,能成為明星的屈指可數。“十幾年前藝術院校比較少,全國范圍的藝術教育主要分兩個層次,一個是國家一級的,是文化部直屬的的學校,包括上海音樂學院、上海戲劇學院,全國一共9所,培養的是全國最高水平的專業藝術人才;另一個是各省各大區一級的,這部分藝術學院培養的是省市一級的最高水平的藝術人才,畢業后基本采取分配等方式,當時學校的數量不多,但就業不成問題。現在的問題是,1998年以后,進行了擴招,很多學校沒有很充分的資源、條件去進行藝術教育,但是覺得考生不少,這個市場似乎是塊肉,大家都來辦。好處是學生的就學機會多了,帶來的問題是學生多,就業難。其實我們藝術人才的選擇標準不應該降低,市場基本上也不會無原則的擴張,以前畢業1萬人,現在10萬人,就業當然成問題了。加上‘潛規則’等不公平因素,就業就更難了。”榮廣潤分析道。
此外,與“招考”利益鏈同謀的還有興旺的“考前班”市場。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副教授杜慶春在微博上建議揭開藝考利益鏈條,只引得寥寥兩三人回復。原因在于,很多學生畢業后以教輔導班為生,這已經成為循環經濟了。更有一位學生家長透露,培訓班學不到什么本事,主要是為了拉個關系,而這筆開銷比考前培訓費用多得多。對于老師主觀意愿比較突出、組織也不如高考那么嚴密的藝考招生,每個環節都能成為培訓班、中介以及家長惦記著去運作的“缺口”。可見,目前看似嚴正公平的種種規矩、標準卻成為了營私舞弊真正的根源與溫床,成為了利益本質的最好的“遮羞布”。
于是,“可以考慮讓影視專業取消藝考了!” “像限制買房一樣限制藝考!”之類反對聲寥寥。在教育體制的頑疾面前,千千萬萬學生、老師集體噤聲,或被“洗腦”為應當如此,在不得不適應、且努力適應了體制之后的他們會群起來捍衛這種制度,這也是體制的厲害之處。雖然也厭惡不滿,但是比起重新洗盤定位,之前的努力付之東流,他們更多選擇的是忍受。
“國中繪畫現狀在當代文化情境中的進退失據,乃構成美術教學的困擾與兩難。”這是陳丹青當年請辭的一大動機,當時卻被輿論故意忽略了。那么,當代文化是怎樣的情景?資本、金錢成為了隱形指揮棒,“藝考熱”的高燒不退背后充斥著對于藝術的異化以及功利化的思想。
一部影視劇里,生旦凈丑也都得齊全吧?除了奶油小生,也要硬漢吧?相貌如葛優、孫紅雷,還不照樣紅得發紫?這個道理誰都懂,但是沒法,現在的影視圈就是帥哥美女更占優勢。“ 現在一些沒有文化的大老板進入了影視圈,這些暴發戶是沒有藝術修養和審美情趣可言的,他們就是要看俊男靚女,有些甚至是為了選美女做他的小蜜或太太的,現在情況太不正常了,可是藝術有時就被這些控制了,導演沒有權利了,資本說了算,而不是藝術說了算。”武珍年說,“像美國就不一樣,也有資本,但是資本和藝術找到了一個平衡點,兩者都很成熟,有一些不是很漂亮的男女演員也能當男女主角。但是現在我們的市場是畸形的,是不成熟的,必然會誤導藝術院校的招生,因為市場是這樣的,高等院校當然要為市場服務。”
武珍年透露,在謝晉藝術學院成立時,謝晉導演號召學生要像馬家軍一樣刻苦訓練,但是請來的香港知名制片人吳思遠立馬“唱反調”:“孩子們,我告訴你,要成名,你的功夫、能力不是最主要的,90%靠的是機會。”前者是理想主義,而后者道出了殘酷的現實。君不見,那些沒心靈體驗只有蒼白的港式擺POSE表演、臺灣雞血式表演的明星們卻能靠靚麗的外表拿著不菲的片酬,他們是被市場哄抬而身價百倍的。藝術學院的學生們的眼睛可是“雪亮”的呀,他們寧愿不上課,連畢業大戲的女主角都不演,甘愿去電視劇里演個小丫鬟,以增加“亮相”的機會,時不可待,機不可失,成名可要趁早啊!
“現在很多人的視野小,格局小,膽子也小,該大的地方都小,該小的地方很大。很多藝術家以前的理想是我們怎么做點有意思的事,畫點畫也好,搞點行為藝術,哪怕是惡作劇也好。但現在不是了,現在沒有什么興趣了,只是想著怎么弄個車、弄個房子,怎么把工作室弄漂亮點,太注意物質方面的東西,太注意把表面的東西作為一個展示,忽視了自己的內心。”劉大鴻感嘆。不少名畫家、名演員、名播音、名主持都忙著爭名奪利,在這樣的“榜樣”下,如何讓后來者們拋棄世俗的東西,像李叔同修行那樣鉆研藝術?
現今社會,在不少人眼里,什么是成功?就是有錢有房有名有勢;什么是幸福?就是穩定、高福利、有保障。社會評價標準的一元化,勢必導致思維的單一、行為的趨同。藝考、國考的火熱就是明證。一位來自東北大慶油田的男考生哭著來找武珍年,他說,“我必須得考大學,不考大學的話,沒有文憑,沒有大學文憑,連工作都找不到好的,只能當清潔工、操作工,不能坐辦公室,那我的一生……我被逼到絕境了。但是考大學我的分不夠,就只能考分數低的藝術類院校了。”當白領,坐辦公室成為很多學生的目標。2011年,國家公務員考試報名人數逾140萬,繼2009年以來連續三次超過百萬,競爭最激烈的前6個職位考錄比例超過3000:1。20年前,隨著市場經濟迅速發展,大批年輕人紛紛走出體制,進入外企或下海創業,這里有著更多的空間,然而20年后,開始大幅度轉向——年輕人紛紛涌到“體制中”去。
在整齊劃一的“標尺”下,在單一化的快速培養標準下,“批量生產”出的將是眾多“萬精油”型的庸才,連“殊異”都少有,何來的大師?在功利化的環境影響下,本應大膽創新的年輕人不愿再做特立獨行的一小撮。他們沒有陳寅恪先生提出的“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更沒有憂國憂民的胸懷。“教育問題是無解的。白說。”陳丹青嘆道。果真如此?幸而,有不滿者、抗爭者正在為僵化的教育體制松土,但國家一直呼吁的創新型人才的出現,更需要來自社會各方面力量匯集的一場“大雨”的澆灌,因為創新型人才的培養需要一個健全的、多元化的教育體制,而此教育體制的建立需要的是一個開放、尊重個性、有多元價值判斷的社會,只有有了這個多元的環境,才會激發無數個體的創造性。
期許“偏才”們、“歪瓜裂棗”們的春天早日到來。

“藝考熱”的高燒不退背后充斥著功利化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