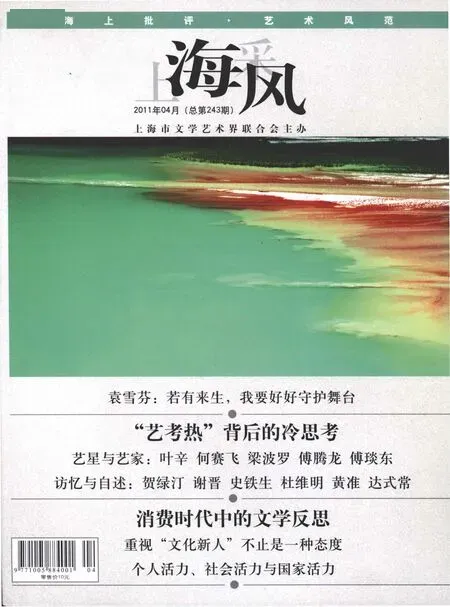葉辛:作家的本分就是寫作
文/本刊記者 劉莉娜
葉辛:作家的本分就是寫作
文/本刊記者 劉莉娜

葉辛近影(沈建一攝)
前不久,市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與上海社科院文學研究所聯合召開了推進本市文化發展座談會暨葉辛長篇新作《客過亭》作品研討會,會上,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劉云耕及眾文藝界人士如羅懷臻、王小鷹、秦文君、王汝剛、趙長天等都進行了發言,對《客過亭》的文學性、思想性和時代性進行了探討。對此,葉辛自己都深為感慨地說:“我做作家和人大代表都做了三十幾年了,教科文衛組織為一本文學作品開研討會,就我的經歷來說這大約是第一遭。”基于某種思維定式我問道:“這是否說明‘知青文學’在當下社會還具有值得探究的意義?”葉辛一副“就等你這一問”的笑容,接口說,“其實我是想說,這說明,《客過亭》已經不是一部傳統意義上的‘知青文學’了——它是一本人生之書。”
在長篇小說《客過亭》中,葉辛通過一群知青伙伴們的一次“重返插隊時的第二故鄉”之旅,以沉靜平和的心態與寬廣的胸懷,思索了整整一代人的信仰和愛,追索了他們過失的往事和錯誤,回憶了他們有過的希冀和欲望,透過他們色彩斑斕的命運和各自背上的心靈重負,寫出了逝去年代的至誠至愚、至真至悲,也寫出了逝去年代里生命軌跡中的尷尬和無奈,更寫出了這一代人的生活現狀及對人生、命運、愛情、歷史、社會的詰問。書中那一群與共和國同時代也是與作者同時代的伙伴們,他們出身不同,心性各異,青春時期各有屬于自己的追求和理想,曾經虔誠、曾經盲目、曾經狂熱地順應時代,回城后各有自己的人生遭遇與沉浮,如今都人到中年,漸入老年。在經歷了洗禮般的輪回后,當他們重逢于目睹了無數歷史風云變幻的“客過亭”上時,他們在殊途同歸的人生之路的盡頭終于幡然醒悟,“再絢爛輝煌的東西都會輸給無情的時間”,從而各自尋找到了生命的真諦。
葉辛的文學創作雖成名于“知青文學”,但他的小說題材早已遠遠突破了“知青文學”,所以我很理解他為何反復強調“我不是一個知青作家,《客過亭》也不是一本知青小說”。不過,提及這本書的靈感與寫成,“知青”始終是個繞不開的話題。葉辛說:“知青歲月是我們這一代人的陣痛,也是共和國歷史上的一段陣痛,現在,我們和共和國同歲的這一代人大多已進入回首與反思的年齡階段,很多老知青都在組織返鄉活動,含著熱淚、懷著復雜的心情回憶那些日子。”于是就有了2007年夏天葉辛的妹妹與當年在同一個縣插隊落戶的老知青們相約一起回山鄉探尋回憶的旅程,這一次旅程間接成為葉辛寫《客過亭》的誘因,因為他的妹妹回到上海后帶回了一本“修文縣上海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名冊”。“名冊中,上海遠赴修文山鄉插隊落戶的462個知青的簡況都標注得清清楚楚。尤其是如今幾乎不被人注意的‘家庭出身’,在這一半寸寬的小框里,有工人、職員、小業主、資產階級、干部、反革命,還有富農、地主、攤販、工商地主、壞分子、舊軍人、歷史反革命、自由職業者、個體勞動者、兵痞、偽警察、店員、偽職,也有至今看著都模糊的私方、勞動者、四類分子等等,活脫脫是一幅上海社會的百景圖。”這本珍貴的“名冊”觸動了葉辛,最讓他激動不已的,是名冊最后面的那個標注著“備注”的小框,不知是知青辦哪一位有心人,把所有462個上海知青離開農村以后的去向都一一標出來了。原來,462個人的命運,竟有如此大的天壤之別。
“名冊中還有一些當年因各種各樣原因出名的知青,一看到他們的名字,我的腦海里就會展現出一幕幕生動的影像:有人是先進知青,當年呼風喚雨;有人因同農民睡覺臭名遠播;有人生下了孩子無奈送人;有人是慣偷……”無數的往事隨著這些名字從葉辛的記憶深處呼嘯而出,他說:“我的思緒一下子打開了,我想,近年來隨著曾經轟轟烈烈波瀾壯闊的上山下鄉運動相繼迎來35周年、40周年的紀念活動,遍布全國的知青們或出書,或編畫冊,或拍攝影碟,或出版攝影集,或聚會,或像我妹妹她們一樣,帶著子女甚至第三代重返第二故鄉,重走當年走過的路,在人數眾多和各種各樣小型的聚會中,我聽到了多少同時代伙伴們的故事啊。我陡地感覺到,就用一群知青們重返第二故鄉的旅程來寫一部新的長篇小說,不是一件十分有意味的事情嗎?”
但觸動歸觸動,葉辛寫長篇卻有個習慣,就是當新的創作沖動產生后,他會把相應的構思先整合好,并不動筆,而是放在一邊讓它“冷卻”一段時間,沉靜一段時間,他將此稱作“等待開頭”,也可以稱為期待一次沖動——因為要寫就一部好的長篇,一時的沖動是不足以支撐大局的,而一個有寫作空間的題材也一定會經受得住時間的打磨和思想的沉淀。這一沉淀就是兩年多,直到去年4月3日,當葉辛走進了一位重病中的重慶知青陳俊的家中,聆聽這位“埋藏了31年純真愛情”的男主人公講述他和傣族女子依香娜的愛情故事后,他一下子找到了自己一直期待的小說開頭。葉辛說:“我是去重慶開中國作協的主席團會議的,正好《重慶晚報》一位年輕的記者找到了我,給我引見了知青陳俊,說他得了重病將不久于人世,最后的愿望一是想見一見當年的傣族戀人,二就是想見一見我。”于是葉辛就上門去見他了。“他是一個很普通很普通的人……”葉辛說完這短短一句,做了一個非常久的停頓,久到我有點不安,然后我看見他端起茶杯大口喝茶,明顯地壓下了一些情緒。“這個陳俊,做了一輩子最底層的老百姓,也沒有升一點點小官發一點點小財,從世俗意義上可以說,一輩子也沒取得任何成功或者成就,可是當他知道自己生命不久的時候,他鼓起勇氣向現在的妻子述說了當年和傣族女子依香娜的一段純潔戀情,以及自己為了返城卻對她不辭而別的愧疚。他很想再見一見依香娜,很想和她說一句抱歉。”葉辛突然覺得,他們這一代人,早衰的也好,不如意的也好,其實都有過精彩的年輕歲月;而當年的愛也好恨也好,不管當年多么激烈,到最后一切都將在時間中得到釋然。這讓他想起自己插隊時候一位當地老農民無意中的一句話:山坡是主人是客——在自然與時間面前,我們都只是過客。于是,小說的開頭也有了,小說的名字也得了,從重慶回到上海,葉辛的長篇也就順理成章地起筆了。

葉辛與夫人
記者:能具體說說書名《客過亭》的由來么?
葉辛:大概是我下鄉第三年的時候,那一年我差不多21歲了,可是在鄉下,我的勞動能力還遠遠達不到一個21歲小伙子的水平,于是隊里就安排一個56歲的老農和我搭檔給梯田送水。這個勞動一般身體好的農民可以一次搖動三百多下,可是我搖五十多下就累得不行了,這時候老農就照顧我讓我休息休息。于是我們就躺在土坡上,那個老農順手指著山頂的一棵樹,跟我說:“我現在是50多歲,我跟我的孫孫說,你看山頂這棵樹,爺爺我像你這么大的時候,它就在現在這個位置,就是現在這個樣子了,那時候我爺爺也給我指這棵樹呢。現在我都這么老了,它還是這個樣子——山坡是主人是客哪!”我當初聽這個話后,印象特別特別深,特別有感觸,比看任何哲學書都受觸動。這句話我就牢牢記住了,這次寫這個長篇,關于歲月起伏人生際遇,我一下子就想到這句話。
其實我為了保留這個書名,還有一定損失呢,因為最初出版社覺得這個書名比較平淡,不夠吸引人,不能促進銷售,于是我主動跟他們說,我之前出版的長篇小說最少起印都是五萬冊的,但這次為了保留這個“平淡”的書名,我主動讓步,讓出版社用減少起印量來分擔風險。
記者:結果賣得如何?
葉辛:現在上架也才一個多月,出版社反饋的情況還是不錯的,他們說很多年輕的讀者也提供了很好的反饋。
記者:所以你對自己讀者群的定位也有包括年輕人的咯?在寫作的時候會不會有意識地顧及到年輕讀者的閱讀傾向?
葉辛:這個不會的。但我的書一直是希望感興趣的人都來看一看的,即使沒有知青經歷,即使沒有那段歲月的生活經驗,也可以得到閱讀的樂趣。我對《青年報》的記者曾經說過——可不是為了給我自己的書做宣傳——只要你靜下心讀半個小時這本書,你一定會放不下的。
這一個半月下來,據說各個年齡層次的讀者都有購買的反饋,其實我一直提倡,就像所有年齡的人都可以去看脫口秀一樣,就像所有年齡的人都可以去看滑稽戲一樣,我希望各個年齡層次的人都來看看小說,這是很有意義也很有樂趣的。讀書,并不一定要當作嚴肅的事情來做,讀讀小說亦不失為普羅大眾的一種休閑娛樂方式。
記者:這本長篇小說你用了一個月不到的時間寫完,真的很快。很多作家都說寫長篇是體力活,你如何保持這樣充沛的寫作狀態呢?葉辛:其實到了我這個年齡,即使是很打動我的事情,我也可以很好地控制情緒慢慢的寫出來了。可是對于我個人來說,可能有的人寫東西喜歡精雕細琢,我卻很講究行云流水的氣韻和節奏感。當年寫《蹉跎歲月》,35萬字,我也就寫了差不多一個月。
我覺得,作家寫出的文字和情緒有關,中國的文字和文學都講究節奏和情緒,情緒很充沛的時候寫的文字可能是不夠精致,但讀者肯定讀得出里頭的情緒感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創作語言的情緒和音韻感是否通達酣暢,比追究文字的華麗和雕琢更有意義。當然,有的時候在情緒支配中寫下的文字,難免情節有些單薄或者線索有小漏洞什么的,所以我至今都保留了一旦有了小說構思就先講述給夫人聽的習慣,這個習慣從我們還是戀人開始一直延續到今天,幾十年了,夫人在生活和寫作上都是我的賢內助。
記者:聽著很溫馨呢。那么你下一步有什么寫作計劃?
葉辛:其實對于現在的我,多寫一本小說或者少寫一本已經沒有任何區別了——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我的《蹉跎歲月》和《孽債》已經達到了很難超越的高度,可能我之后的寫作都很難超越它們的影響力了。不過我一直說,作家其實就和農民一樣,作家的本分就是寫作,農民的本分就是種田;農民不可能因為秋天我獲得了這一季的豐收,明年我就不種田了,明年還得種啊。同理作家也不可能因為已經寫出了有一定影響力的作品,就不再寫作了,作家也得繼續勞動。活著就得勞動。
具體來說,我打算在60歲到70歲的十年里寫3本書吧,現在《客過亭》算第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