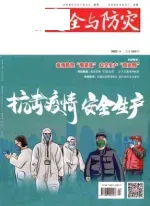安全氛圍研究綜述
文 / 張妮斯 湖南師范大學(xué)教科院
盧斌榮 湖南省安全生產(chǎn)監(jiān)督管理局
安全氛圍研究綜述
文 / 張妮斯 湖南師范大學(xué)教科院
盧斌榮 湖南省安全生產(chǎn)監(jiān)督管理局
隨著工業(yè)社會(huì)的發(fā)展以及社會(huì)文明的持續(xù)進(jìn)步,安全生產(chǎn)問(wèn)題日益突出,現(xiàn)代化企業(yè)通過(guò)諸多的技術(shù)手段和工程方法來(lái)提高生產(chǎn)的安全性,但是在技術(shù)層面提升安全生產(chǎn)水平的局限性日趨明顯。分析國(guó)內(nèi)生產(chǎn)安全事故發(fā)生的原因,可以發(fā)現(xiàn)因管理不善、違章指揮、違章作業(yè)以及違反勞動(dòng)紀(jì)律造成的事故要占事故總數(shù)的70%以上。由此可見(jiàn),絕大多數(shù)事故都是人為因素造成的。近年來(lái)諸多研究者開(kāi)始將目光轉(zhuǎn)到探究人、組織以及其它非物理因素上。人們的安全態(tài)度、安全承諾以及組織對(duì)安全員、領(lǐng)導(dǎo)者的態(tài)度等社會(huì)因素均影響安全績(jī)效或不安全行為,由此形成了組織的安全氛圍研究領(lǐng)域。
安全氛圍的核心含義
在以往的研究中,安全氛圍與安全文化的關(guān)系一直處于爭(zhēng)論當(dāng)中,盡管兩者在詞源上有著區(qū)別,但它們的名稱在許多研究中經(jīng)常交替使用,甚至?xí)诲e(cuò)誤地理解。因此,要理解“安全氛圍”的核心含義,必須首先將其與“安全文化”區(qū)分開(kāi)來(lái)。
1986年,國(guó)際原子能機(jī)構(gòu)(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的調(diào)查報(bào)告中認(rèn)為安全文化不足是導(dǎo)致切爾諾貝利災(zāi)難的主要潛在因素。自IAEA首次提出“安全文化”的概念后,這類研究受到越來(lái)越多的關(guān)注。英國(guó)健康安全委員會(huì)(HSC)則定義“安全文化”為:個(gè)人和群體的價(jià)值觀、態(tài)度、認(rèn)知、能力、行為模式以及組織的安全健康管理方式和形象。積極的企業(yè)安全文化可表現(xiàn)為相互信任、共享對(duì)安全重要性的認(rèn)知、對(duì)預(yù)防措施有效性的自信等等特征。
“安全氛圍”這一概念最早由Zohar在1980年對(duì)以色列制造業(yè)的安全調(diào)查過(guò)程中首次提出,并將其定義為:組織內(nèi)員工共享的對(duì)于具有風(fēng)險(xiǎn)的工作環(huán)境的認(rèn)知。
“安全文化”是由“組織文化”衍生而來(lái)的概念,一般而言,組織安全文化是指企業(yè)在將它對(duì)待安全的態(tài)度和價(jià)值觀傳遞給它的員工時(shí)使用的一系列標(biāo)志、儀式、好習(xí)慣,安全文化對(duì)工作和組織而言包含潛在的安全信仰、安全價(jià)值觀和安全態(tài)度等特性,集中于宏觀的理論研究層面。“安全氛圍”是從組織氛圍的研究中衍生而來(lái)的概念,安全氛圍與對(duì)安全政策、程序和實(shí)踐的共享感知有關(guān)。安全氛圍通常被認(rèn)為比安全文化淺一層次的、描述安全文化當(dāng)前狀態(tài)的概念,更接近于企業(yè)生產(chǎn)運(yùn)行狀態(tài),具備對(duì)工作環(huán)境、生產(chǎn)實(shí)施、組織政策和管理的認(rèn)知特點(diǎn),其研究和運(yùn)用范圍主要針對(duì)組織的微觀運(yùn)行層次。由此可見(jiàn),兩者雖然存在相似點(diǎn),但在具體上存在一定的區(qū)別:安全氛圍本質(zhì)是一種心理表象,常與組織內(nèi)部的工作環(huán)境和安全狀態(tài)問(wèn)題密切相關(guān),表現(xiàn)為個(gè)人和組織在特定地點(diǎn)、特定時(shí)間內(nèi)對(duì)安全狀態(tài)的認(rèn)知(包括對(duì)組織安全政策、安全程序和安全訓(xùn)練的認(rèn)知),是安全文化的短暫“快照”,具有不穩(wěn)定性和變化性。
因此,安全氛圍的核心概念是:一種能夠測(cè)評(píng)安全文化即時(shí)狀態(tài)的、反應(yīng)組織內(nèi)部不同個(gè)體安全認(rèn)知的工具,相對(duì)于組織當(dāng)前環(huán)境和狀態(tài)而言,安全氛圍是對(duì)特定地點(diǎn)、特定時(shí)間內(nèi)的具體狀態(tài)的認(rèn)知,并隨著環(huán)境和狀態(tài)的變化而變化。
縱觀安全氛圍的相關(guān)研究,Copper提出了目前安全氛圍的四種研究取向:第一,設(shè)計(jì)心理測(cè)量工具并且確定安全氛圍的基本因子結(jié)構(gòu);第二,提出和驗(yàn)證安全氛圍的理論模型來(lái)明確其影響因素;第三,檢驗(yàn)安全氛圍和實(shí)際安全績(jī)效之間的關(guān)系;第四,探究安全氛圍和組織氛圍之間的關(guān)系。
安全氛圍的因子結(jié)構(gòu)
對(duì)于安全氛圍的有關(guān)研究表明,它能夠有效地測(cè)量安全態(tài)度、并且是安全行為的有效預(yù)測(cè)源。但是對(duì)于安全氛圍的因子結(jié)構(gòu)仍然存在著許多爭(zhēng)論。下圖是歷年來(lái)對(duì)安全氛圍因子結(jié)構(gòu)研究的列表:

表1 安全氛圍的維度研究總結(jié)
在對(duì)安全氛圍進(jìn)行研究時(shí),許多研究者會(huì)通過(guò)諸如文獻(xiàn)、事故分析、深度訪談、小組專題座談等方法,或者從其他研究工具中選取項(xiàng)目的方法來(lái)構(gòu)建自己的安全氛圍問(wèn)卷。由于構(gòu)成安全氛圍的因子結(jié)構(gòu)有很多,安全氛圍的研究結(jié)構(gòu)通常由于研究者的個(gè)人認(rèn)知或者理論依據(jù)的不同而導(dǎo)致較大的差異。
目前,構(gòu)成高階安全氛圍因子的一階因子具體有哪些,研究者們還沒(méi)有達(dá)成一致意見(jiàn)。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多數(shù)研究中都包括安全管理承諾。可以通過(guò)管理者對(duì)員工福利的關(guān)注、對(duì)安全管理的態(tài)度、安全對(duì)于組織的重要性等題目對(duì)安全管理承諾進(jìn)行測(cè)量。Flin和Guldenmund也曾指出,最近的研究中只有管理承諾是各個(gè)安全氛圍研究中唯一共同的因子,除此之外,不同組織安全氛圍的因子結(jié)構(gòu)有顯著的差別。
安全氛圍與安全行為
以往研究表明,安全氛圍可以預(yù)測(cè)與安全相關(guān)聯(lián)的行為所導(dǎo)致的后果,例如事故率、傷殘率。并且,安全氛圍也會(huì)影響個(gè)體的安全行為。鑒于安全氛圍對(duì)安全行為有著重要影響,許多學(xué)者對(duì)此進(jìn)行了深入探討,Zohar提出的模型最具代表性。他的模型認(rèn)為安全氛圍通過(guò)三個(gè)階段來(lái)影響安全行為的結(jié)果:(1)氛圍感知影響行為——結(jié)果期待;(2)期待影響安全行為的普及;(3)行為上的安全影響公司的安全記錄。第一個(gè)階段暗含于安全氛圍的定義中,而且是隱性的。在該模型中,安全氛圍是指員工對(duì)組織中的安全優(yōu)先級(jí)的感知。員工對(duì)安全氛圍感知和組織的安全政策有關(guān),因而氛圍感知將影響結(jié)果期待。即如果員工覺(jué)得組織有良好的安全氛圍,那么他可能認(rèn)為只要自己遵守組織中的規(guī)章制度,就應(yīng)該能保證工作安全。這就是員工形成的行為期待。第二個(gè)階段是基于社會(huì)學(xué)習(xí)和期望效益的構(gòu)想,通過(guò)確定的行為得到某一結(jié)果的可能性越大,這一結(jié)果的效益越大,則遵守特定方法來(lái)行動(dòng)的動(dòng)機(jī)越強(qiáng)烈。最后,第三階段基于有關(guān)工業(yè)事故中人的行動(dòng)重要性的大量實(shí)證。考慮到認(rèn)為失誤可以解釋85%的工業(yè)事故,行為安全應(yīng)與公司安全記錄呈現(xiàn)顯著正相關(guān),這將導(dǎo)致安全氛圍和安全記錄間的整體聯(lián)系。這三步共同形成了一個(gè)安全氛圍和安全行為報(bào)告之間的關(guān)系。
安全氛圍與安全績(jī)效
目前,對(duì)于安全績(jī)效定義的研究說(shuō)法不一,現(xiàn)在普遍認(rèn)同的是將安全績(jī)效定義為意外事故發(fā)生對(duì)個(gè)人所造成的傷害程度。國(guó)外對(duì)安全績(jī)效維度的研究,由于研究領(lǐng)域不同,到目前為止沒(méi)有統(tǒng)一的定論。研究領(lǐng)域比較集中在任務(wù)績(jī)效和結(jié)構(gòu)方程這兩個(gè)領(lǐng)域。
基于任務(wù)績(jī)效理論,Neal等人(1997)提出了一個(gè)安全績(jī)效結(jié)構(gòu)模型,模型融合了兩個(gè)維度:服從(obedience)和參與(participance)。安全服從包括遵守安全程序、安全地工作;安全參與包括幫助同事、主動(dòng)示范、改善安全計(jì)劃和提高工作場(chǎng)所的安全程度。
Neal和Griffin等假設(shè)組織氛圍對(duì)安全績(jī)效的影響受安全氛圍變量的影響,而安全氛圍對(duì)安全績(jī)效的影響則受安全知識(shí)和激勵(lì)程度的影響。安全知識(shí)與技能更多的是影響安全遵守,而安全動(dòng)機(jī)更多的是影響安全參與。評(píng)定是以員工自我報(bào)告的形式進(jìn)行的。由于這種方法是自我觀察、自我報(bào)告,在實(shí)踐中很少使用,但在理論研究中可以用作結(jié)果變量。而且,這一模型提出了安全參與概念,相比以前只強(qiáng)調(diào)安全遵守來(lái)說(shuō),是一種積極主動(dòng)的安全。用結(jié)構(gòu)方程模型進(jìn)行分析,驗(yàn)證了假設(shè),得到以下模型:

總結(jié)與思考
目前來(lái)看,研究者們對(duì)于安全氛圍的定義比較一致,但是對(duì)于安全氛圍的因子結(jié)構(gòu)劃分還存在著分歧。一方面,在進(jìn)行測(cè)量時(shí),很多問(wèn)卷中的題目都沒(méi)有很好區(qū)分安全管理措施、安全氛圍和安全行為之間的差異,即對(duì)安全現(xiàn)狀、安全心理和安全行為的區(qū)分度較差,讓人產(chǎn)生混淆,造成測(cè)量結(jié)果的差異很大。另一方面,國(guó)內(nèi)外進(jìn)行的測(cè)量基本是從安全系統(tǒng)與工程、管理科學(xué)的角度出發(fā)的,鮮有從心理學(xué)和組織行為學(xué)的角度對(duì)安全氛圍進(jìn)行實(shí)證研究的,而且國(guó)內(nèi)對(duì)安全氛圍測(cè)量上僅限于對(duì)一個(gè)企業(yè)進(jìn)行數(shù)量不多的問(wèn)卷調(diào)查,沒(méi)有反映國(guó)內(nèi)整體全貌。
安全行為的測(cè)量方法也存在著同樣的難題,客觀事故率過(guò)于粗放,不足以表現(xiàn)行為的過(guò)程,而對(duì)于行為本身的測(cè)量既難以劃分因子結(jié)構(gòu)又沒(méi)有明確的標(biāo)準(zhǔn)。此外,個(gè)人的安全績(jī)效測(cè)量方法也是多種多樣,各有利弊。由于實(shí)踐中的種種限制,目前沒(méi)有特別精確的測(cè)量方法。對(duì)于安全績(jī)效的統(tǒng)計(jì)方法,也有很多種,但是安全績(jī)效的指標(biāo)是多樣化的,很難在一個(gè)研究中進(jìn)行綜合的對(duì)比。
盡管安全氛圍的研究仍然存在著諸多不足之處,但是對(duì)安全氛圍的因子結(jié)構(gòu)、影響機(jī)制等進(jìn)行相應(yīng)的探索分析,可以為提高組織的安全生產(chǎn)水平和運(yùn)營(yíng)效率提供一條嶄新的途徑。
■責(zé)任編輯 鐘金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