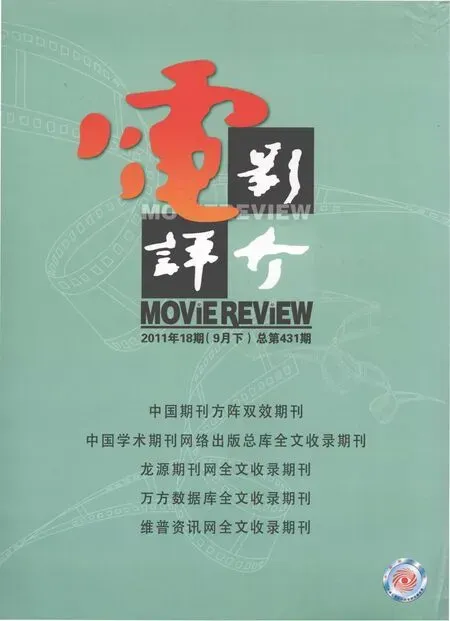出家與歸家的自我詰問:從李安“家庭三部曲”到《臥虎藏龍》
作為世界組成單位中最小的個體,從墜地開始,到終老結束,都是孤單單的來,孤單單的去,因為作為個體存在的人,獨一性是永恒的慣性。然而,作為人,我們又是害怕孤單的,所以為避免孤單,人類產生了各種各樣的團體,而最牢固和持久的,就是家庭。應該說,人類從出生到死亡,無法逃避和釋懷的團體便是家庭。家庭,最本質特征便是“群體性”,這在本質上與人與生俱來的獨一性便互相抵觸,作為個體的人內在要求的自由、個性(即出家)與家庭內在要求的秩序、服從(即歸家)的不可調和性成為千百年來在家庭圍城內外掙扎的人們永恒的議題。臺灣導演李安就是一個在這樣議題上走得較遠的一個探索者。
李安有著濃厚的東方文化底蘊,多年的異域旅居生活,以及扎實的戲劇舞臺基礎和好萊塢專業的電影訓練。他將自己對于東西方文化,人類文化傳承的思考選擇了一個很好的載體——家。從中國古老的造字學就能明白,家是由大屋頂封閉型結構建筑和對男性主神的崇拜兩個基本點構成。儒家認為,家庭中心價值即“中和”,有言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家庭,作為承載社會文化的最小單位,它的秩序表現為其一:父權秩序不可侵犯;其二:傳宗接代;其三,孝順父母,養奉天年。在中國千百年來的儒家思想體系下,這些成為社會綱常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在這樣的秩序下,家庭的傳承性使其帶著兩個明顯特征,即變動性和文化附著性。恩格斯在《家庭.國家.私有制起源》引用摩爾根語:“家庭,是一個能動的要素,是隨著社會從較低向高階段發展。”所以在代代相傳中,產生了一些浪子形象,他們擁有的“未成年性”,使他們在既存體制下反抗,疏離父權體制強加的桎梏,壓迫。他們往往是矛盾的綜合體,即帶有父系文化的傳承性,又有著對新異文化的向往追求,渴望“出走”。這在中國佛學文化中有所表示:“出家”為基本隱喻,走出父母血緣關系為基礎的綱常之家,走到宇宙之家,得到最終的解脫。然而一般人難以做到真正的看破紅塵,出家也未必能歸隱世俗之心,浪子無一例外的是最終陷入一個艱難的文化焦慮之中,結局無外乎兩個:回歸父系家族或重組一個新異文化家庭,誰都無法逃脫家庭這個大背景。
李安深諳“浪子”深切的“出家情結”,在他的“家庭三部曲”中,《喜宴》和《推手》中的兒子形象,《飲食男女》中朱家三姐妹,在這樣的現實題材中都可以找到兩種文化的沖撞與調和。《喜宴》中的兒子是個同性戀,他所破壞的是家庭秩序文化中最為嚴重的“傳宗接代”的禁忌,是代表著一種新異文化對傳統家庭秩序的對抗,盡管在最后,父親的心愿已了,但是作為父系正統秩序也已分崩離析;《飲食男女》中的家倩由叛逆到回歸,也是因為父親主動摧毀原有家庭體系,從而找到自我,形成新的家庭內核。作為更加迷離傳奇的武俠電影,《臥虎藏龍》中走得更為極端和浪漫,玉蛟龍沖出家庭,最終選擇義無反顧的跳崖以“得道”,真正達到了禪宗里“大解放”的自由與超脫。應該說,是有了“家庭三部曲”的積累和迷茫,李安在找尋浪子渴望個性自主的命題上有了一個終極的答案,全部賦予《臥虎藏龍》里的玉蛟龍,她不再是傳統結局中的回歸或重組家庭;她最終的一躍,完成了她的父輩——李慕白未曾領略的境界,即萬物皆空的佛家之道。從愛情中出走的玉蛟龍,在情字上不再有李慕白的迷失感,當李這個角色以生命換取了她的悟道后,父親身份的缺失使玉蛟龍的心再無羈絆,她的悟道使她擺脫了所謂重返父性文化,或被異己文化吞沒的慣有結局,溶入“宇宙之家”,達到影片里李慕白因迷失于愛情而未能達到的圓寂永恒的最高境界。
李安在其影片中,除了描摹浪子的“出走”情懷之外,也突出浪子深深的戀父情結。父親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代表著一種不可逆轉的秩序,兒子自身對于父權有著深切的反叛情緒,但又因為強大的血緣關系保持著的生命聯系,使自己作繭自縛的處于一個艱難的文化困境中:兒子對于父親的敬仰和依戀,與現實中父親的蒼老形成一種不可調和的矛盾。《推手》中父親的身份是一位自信從容的太極拳師,這與最后入獄時的黯然形象形成鮮明對比,是一種對于自身文化的固守,也包含著李安對于固守者一種悲涼的贊嘆;《喜宴》中父親曾是叱咤風云的將軍,卻不得不運用計策來忍辱求全以實現傳宗接代的家族最基本要求。如果說前兩個父親都是有些被動的接受者與反抗者,那《飲食男女》中的父親算是一個主動的迎戰者,一開始就失去了味覺的他,卻最終主動出擊,最終找到了自我,搬出了老宅;但他味覺的“回歸”也是建立在他對自身文化的破壞之上的。家倩盡管處處與父作對,也是建立在父親不讓她下廚這個前提上的,所以造成“文化鏈的斷裂”,最終的和解也是因為“文化鏈的縫合”,這不能不說家倩帶有深深的戀父情結;《臥虎藏龍》中的李慕白在修煉得道時卻沒有應有的喜悅,反而感到一種寂滅的悲哀,充滿了在頂端的迷茫感和虛無感,中華文明中固有的道德禮法使他不能沖破原有秩序,作為超然物外的俠士形象,他內心卻并不自由,一直將自我禁錮在內心舊秩序的藩籬之中。對新秩序的建立,他甚至用犧牲生命的方式才得以完成。最終悟道的玉蛟龍,之所以選擇縱身一躍,也是因為其深深的戀父情結所致,這份情結,遠遠超越了她與羅小虎的單純愛情。
李安另外一大特點便是突出外來文化與中華傳統文化的沖突撞擊。李安深深的迷戀著中華傳統文化,對于描述中華文明在他的影片中的某一領域的缺失,總是帶著深深的惆悵與無奈的情緒。《推手》中洋媳婦與傳統父親角色的設置,就有著十分明顯的指向性含義。在中外文化沖擊的這場大戰中,以父親搬出家庭,犧牲他三世同堂的理想結束,成全了處在兩難境地中的兒子。對于外域文化的入侵,父親是一個堅決而無奈的固守者形象,兒子則是一個主動調和者的形象;《喜宴》中的外來文化即為同性戀文化,它與中國千百年來“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子嗣香火思想背道而馳。兒子在片中便是這樣新異文化的代表,作為一個積極對抗者的形象,兒子采取了假結婚的方法,卻早已被“老謀深算”的父親識破,用計妥協的完成了家族傳宗接代的使命;《飲食男女》中原本叛逆的女兒與失去味覺的父親,與最終回歸的女兒與尋找到自我的父親,女兒與父親角色的對錯,完成了一次另類的文化鏈的傳承,一種新秩序的重新輪回;《臥虎藏龍》中的羅小虎,作為外域文化的代表,以一種強盜的方式闖入了玉蛟龍的生活,他奔放、熱情、大膽的特性與中華正統文化中的含蓄內斂形成鮮明反差;玉蛟龍此時作為父系文化傳承者的代表,在爭搶梳子的過程中與其相戀,臣服于外域文化入侵者——羅小虎之下,他作為打開玉蛟龍心性的一把鑰匙,梳子成了一個很好的媒介,搶梳子——贈梳子——還梳子——留梳子,這個過程巧妙的完成了兩人關系的轉變,也象征了玉身份的轉變:承守者——叛道者——悟道者。
所以,李安在各種題材中最終探討的仍然是文化傳承與家庭人倫為主題,縱觀這四部影片的結局,都帶著某種明顯的暗指性含義:《推手》中的父親在與洋媳婦為代表的快節奏的外來文化的爭斗中失敗時,站在陽光下的他說著“沒事兒”的無奈而茫然的表情,他對于自身文化可貴而執著的堅持,也激起李安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尷尬處境的反思;《喜宴》中的兒子攜情人、太太送別父母,兒子的積極對抗最終被父親的心計營運化解為一場相互妥協,兒子與情人、兒子與太太代表著兩種文化的并存,兩種文化的和平共存表達了導演的美好得近乎尷尬的愿望;《飲食男女》中家倩的回歸與父親的出走,空空的朱家大院里不再有朱父儀式化的飲食盛宴,取而代之的是家倩的晚宴,父女兩人圍坐在桌旁,朱父的味覺突然回歸,父女關系的和解,“男女”和“飲食”與原有秩序全然相悖,代表著對于原有文化的徹底顛覆,代表著一種新秩序的全新確立;《臥虎藏龍》中最后的對白也極具禪思:無法再獲取心靈平靜的玉蛟龍對羅小虎說,你還記得那個“心誠則靈”的故事嗎?那么許個愿吧。小虎說,一起回新疆。玉蛟龍隨即躍入萬丈絕壑。懷著心誠則靈信仰的玉蛟龍,最后無法再回歸父系家庭,也無法重建所謂的新異文化家庭,內心如明鏡的她選擇赴死以成全內心的信仰,她是真正逃脫了宿命的“出家之子”,即真正的悟道者。
從《推手》《喜宴》中的兒子,《飲食男女》中的家倩,《臥虎藏龍》中的玉蛟龍身上我們都可以看見自身的影子,能看見人類子子輩輩都處于這樣的文化焦慮中心,我們自己不停重復著前輩重復著的文化困境;永遠處在圍城內外的男男女女,永遠在家庭內外進進出出,掙扎,困擾,生命不息,困境永存。化身為武當山群山峰巒中一縷孤魂的玉蛟龍,只能成為我們幻想中的一種逃脫永恒宿命的誘人的理想主義,如同武當山里千古不散的氤氳,縈繞于我們每個人的夢魘,揮之不去。
劉婷:《關于家的寓言:李安電影及其浪子文化形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