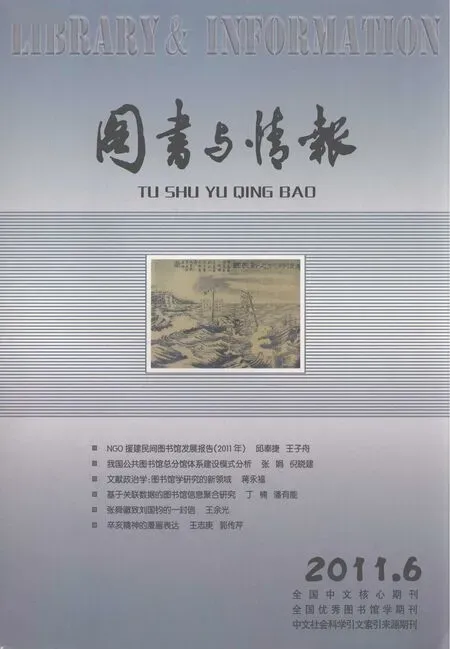文獻政治學:圖書館學研究的新領域
蔣永福 (黑龍江大學信息資源管理研究中心 黑龍江哈爾濱 150080)
1 文獻政治學及其與圖書館學的關系
什么是文獻政治學?或者說,文獻政治學是研究什么的學問?顧名思義,文獻政治學是研究文獻與政治關系的學問。從學科性質上說,文獻政治學顯然是文獻學和政治學之間的交叉學科。
政治的核心是權力。[1]簡單地說,政治就是國家公共權力的運用。恩格斯在論述國家產生時認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2]這種保持“秩序”的“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就是政治權力。國家和政治權力是分不開的,“無論如何,‘政治的’一般而言是與‘國家的’相互并列,或者至少是與國家之間存在著某種關系。”[3]可以說,國家就是運用政治權力保持秩序的政治機器。
為了保持秩序,國家政治權力對社會的各個領域加以控制,其中包括文獻活動領域——文獻的生產、流通、利用活動領域。在中國古代,秦朝曾發生過著名的“焚書坑儒”事件;自漢代始,歷朝歷代的皇帝大都親自關心文獻活動,許多官修書目、類書、政書、叢書就是在皇帝的過問甚至是親自領導下編纂完成的。西方國家近代的書報刊檢查制度,就是國家政治權力對文獻活動加以控制的一種制度。沈固朝先生著有《歐洲書報檢查制度的興衰》(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一書,較詳細論述了歐洲書報檢查制度由興致衰的歷史過程。這樣的事例還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舉。總之,政治權力與文獻活動之間確實存在相互影響的歷史淵源聯系。研究這種歷史淵源聯系現象的學問就是文獻政治學。
從圖書館學的角度看,文獻源研究、文獻閱讀研究、文獻整理研究(主要是書目、標引、編目等)、引文研究、文獻運動規律(如普賴斯定律、布拉德福定律、洛特卡定律等)研究等被認為是圖書館學研究的重要內容,甚至有人認為“文獻”是圖書館學的邏輯起點。[4]也就是說,圖書館學必須要研究社會的文獻現象,包括文獻與政治權力的關系問題。迄今為止,在圖書館學研究領域,有“文獻計量學”、“文獻經濟學”、“文獻分類學”、“文獻信息學”、“古典(文獻)目錄學”、“專科(文獻)目錄學”、“中國文獻學”、“文獻編目(學)”等稱謂,但尚未有人提出“文獻政治學”這一稱謂。從一般邏輯上說,如果上述“文獻××學”成立,那么“文獻政治學”自然也應該成立。從事實邏輯上說,既然文獻與政治權力之間存在事實上的歷史淵源聯系,那么研究這種歷史淵源聯系的“文獻政治學”也應該成立。吳慰慈先生認為,圖書館學與文獻學之間是“同族關系”。[5]既然圖書館學與文獻學是同族關系,那么圖書館學與文獻學之下位類學科“文獻政治學”之間當然也是同族關系。圖書館學既然可以研究 “文獻計量學”、“文獻分類學”等文獻學之下位類學科,那么同樣作為文獻學下位類學科的“文獻政治學”自然也可以成為圖書館學的研究內容之一。在我國,哲學、政治學、歷史學領域一些學者的研究已涉及到文獻政治學內容,如周光慶著有《中國古典解釋學導論》,周裕鍇著有《中國古代闡釋學研究》,李清良著有《中國闡釋學》等等。不過,從這些著作的題名中可以看出,他們是從闡釋學角度研究中國古代文獻的,與文獻政治學研究有較大區別。而我國的圖書館學研究領域,至今尚未出現純正的文獻政治學研究成果。于良芝曾經使用過“圖書館政治學”一詞,[6]但她沒有進行專門的圖書館政治學研究。在我看來,圖書館政治學和文獻政治學之間是相互交叉的關系。在我國圖書館學研究領域,文獻政治學研究還是一個有待挖掘的新領域。
2 文獻政治學研究示例
如何進行文獻政治學研究?文獻政治學研究的表現形式是什么樣的?下面以對中國古代文獻分類目錄編制中的 “經→史→子→集”次序結構安排和類書編纂中的“天→地→人→事→物”次序結構安排的分析為例予以說明。
2.1 分類目錄的“經→史→子→集”次序結構
眾所周知,漢代劉歆所編《七略》首創文獻分類的“六分法”。其六個類目名稱依次為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七略》中的首略為“輯略”,但此略為各略之總要,所以真正的首略是六藝略。六藝略又包括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等九個子目,①《七略·六藝略》名為“六藝”但卻列出了九類,即多出了論語、孝經、小學三類。之所以如此,清人王鳴盛在《蛾術篇》卷一中解釋道:“《論語》、《孝經》皆記夫子之言,宜附于經,而其文簡易,可啟童蒙,故雖別為兩門,其實與文字同為小學。小學者,經之始基,故附經也。”王國維在《觀堂集林·漢魏博士考》中也作了大體相同的解釋,認為劉向、劉歆父子于五經之后,“附以《論語》、《孝經》、小學三目,六藝與此三者,皆漢時學校誦習之書。”可見,六藝略的內容為儒家經典著作。唐初修《隋書·經籍志》,不僅完成文獻分類的“四分法”體例,而且直命經部、史部、子部、集部,由此“經史子集”四部之名形成;而清代乾隆朝所修《四庫全書》及其《總目》則為徹底貫徹經史子集四分法的集大成者。也就是說,自《隋書·經籍志》以來,中國的文獻分類目錄一直延續著“經→史→子→集”四部名稱及其次序。那么,中國古代文獻分類活動為什么始終堅持以經為首的分類次序呢?這就需要我們弄清中國古人對“經“的理解。
《白虎通義·卷八·五經》曰:“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 《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 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象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宋人王陽明對“經”作了如下解釋:“經,常道也:其在于天謂之命,其賦于人謂之性,其主于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7]《漢書·藝文志》云:“六經者,圣人之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兇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人天之理,可得而知,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周予同先生對“經”作的通俗解釋是:“經是中國封建專制政府‘法定’的古代儒家書籍,隨著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和統治階級的需要,經的領域在逐漸擴張,有五經、六經、七經、九經、十三經之稱。”[8]
經學知識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經學載道、論道、傳道,是所有知識的不竭之源,后世者只能通過經學才能體道、悟道,進而才能做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國語·周語下》云:“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韓詩外傳》卷五云:“儒者,儒也,儒之為言無也,不易之術也,千舉萬變,其道不窮,六經是也。”清人章學誠在《文史通義·詩教上》中對此概括地說:“戰國之文,皆源出于六藝。何謂也?曰:道體無所不該,六藝足以盡之。”另外,在中國古代文獻分類活動中,經書的首要地位還源于先人“文出于經”的觀念。南宋陳骙在《文章精義》中認為,六經、四書“皆圣賢明道經世之書,雖非為作文設,而千萬世文章從是出焉”。南北朝時期的教育家、文學家顏之推在《顏氏家訓·文章篇》云:“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于《書》者也;序述議論,生于《易》者也;歌詠賦頌,生于《詩》者也;祭祀哀誄,生于《禮》者也;書奏箴銘,生于《春秋》者也。”這些認識,其實都在提出一個無形的問題:什么知識最有價值?答案就是:經學知識最有價值。②英國社會學家斯賓塞(H.Spencer)在《教育論》一書中提出了“什么知識最有價值”的問題,他自己給出的答案是:科學知識最有價值。后來學者們把這一問題稱為“斯賓塞問題”。斯賓塞.胡毅譯.教育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8,43。這說明,中國古代文獻分類活動的最終旨趣不在于文獻秩序,而在于 “明道”,即通過文獻分類活動,把統治集團認可的“經義”(王道)凸顯出來,使其法定化、常規化。對此,《四庫全書總目》凡例十九說得非常明確:“圣朝編錄遺文,以闡圣學,明王道為主。”
關于“經→史→子→集”的次第關系,乾隆皇帝有一段精彩比喻:“以水喻之,則經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流也、支也、派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經而出。故吾于貯四庫之書,首重者經,而以水喻文,原溯其源。 ”[9]這段話,毫無遮隱地界定了 “經→史→子→集”這種差序結構的內在邏輯。這種“經→史→子→集”差序格局,其實就是中國古人對“什么知識最有價值”問題的明確回答。這說明,“斯賓塞問題”在中國古人那里早有定論,只不過中國古人認為“首重者經”而非科學知識。正因為“首重者經”,所以除了經學之外的其他知識包括科學技術知識都被當作 “次等知識”而被忽視。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的文獻分類方法實際上是為以綱常倫理秩序為核心旨規的統治秩序服務的工具。要言之,中國古代的文獻秩序服務于倫理秩序、統治秩序,而統治者的權力意志是文獻秩序是否合理的最終依據。
2.2 類書的“天→地→人→事→物”次序結構
自唐初纂修《藝文類聚》以來,中國古代類書的類目體例基本定型為“天→地→人→事→物”次第格局。之所以形成這種次第格局,與中國古代儒家、道家對 “天—地—人”三者關系賦予特定的秩序意義緊密相關。
漢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立元神》中指出:“何謂本?曰: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為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也。”在《天地陰陽》中又說:“圣人何其貴者?起于天,至于人而畢。畢之外謂之物,物者投其所貴之端,而不在其中。以此見人之超然萬物之上,而最為天下貴也。人,下長萬物,上參天地。”從“天、地、人,萬物之本”,到“人,下長萬物,上參天地”,其排序是“天→地→人→事→物”,而這正是《藝文類聚》輯錄資料的編排順序。由此斷定中國古代類書的“天→地→人→事→物”大類排序導源于天人感應說,大概不會有太大異議。
清代纂修的《古今圖書集成》是中國現存最大的一部古代類書,“是書為編有六,為典三十有二,為部六千有余,為卷一萬”。其凡例詳細說明了前四編按照天、地、人、物的順序排列的理由:“法象莫大乎天地,故匯編首歷象而繼方輿。乾坤定而成位,其間者人也,故明倫次之。三才既立,庶類繁生,故次博物。”其中所謂的“三才”,即指天地人。陳鼓應先生認為,“三才說”源于《老子》二十五章所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是“先秦道家天地人合一的一種特有的思維方式”。[10]
那么,中國古代類書為什么把“物”這個大類排列在最后呢?葛兆光先生的解釋是,《藝文類聚》“全書最后收錄的自然世界中的各種具體知識,雖然古代中國傳統中本來也有‘多識草木蟲魚鳥獸之名’的說法,對這些知識有相當寬容和理解,但在七世紀,顯然這些知識越來越被當作枝梢末節的粗鄙之事,《藝文類聚》把這些知識放在最后面,顯示了這些知識在人們觀念中的地位沉浮。”[11]其實,在中國古人心目中把物理原理及其應用技術視為“奇技淫巧”的觀念極為普遍。《禮記·王制》說:“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與上齒”,“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劉歆總天下群集而奏《七略》,其中方技列于七略之末;《漢書·藝文志》將方技三十六家列于卷尾;《新唐書·方技列傳》云:“凡推步(指天文、數學)卜相巧醫,皆技也。”在中國古代文字中,“技”、“伎”、“妓”三詞同源。可見,在中國古人那里,無論是科學抑或是技術,終究不是正道,充其量只能稱之為“道”的皮毛表象,是“形而下”之“器”。所以,在《藝文類聚》中,“物”這個大類共有 40 卷,按卷數比例來計算,整整占了《藝文類聚》全書的五分之二之多,然而,它卻只能占據末尾之列。
從以上分析可知,中國古代文獻整理活動確實是在追求一種秩序,但所追求的真正目標并不是文獻秩序,而是給文獻秩序以另外一種更深層的意義,或者說,文獻整理活動所產生的文獻秩序必須體現出更為深層的一種秩序。這種秩序就是思想秩序(綱常倫理秩序)所支撐的權力秩序或統治秩序。
3 文獻政治學研究的內容框架
關于文獻政治學的內容體系,可從不同的角度概括出不同的內容體系。本文以“中國古代”為時空界限,把文獻政治學的研究內容概括為四個方面:文獻“經典化”過程及其權力介入、文獻整理活動中的權力介入、文獻傳播過程中的權力介入和文獻闡釋活動中的權力介入。這實際上是“中國古代文獻政治學”的研究內容。
3.1 文獻“經典化”過程及其權力介入
毋庸置疑,經典文獻一經產生,其對人們的思想影響是極其強大而又明顯的。而經典是通過“經典化”過程形成的。從歷史事實上看,某種文獻成為經典,不僅取決于該文獻的思想內容本身是否 “深入人心”(內在價值),而且還取決于統治階級是否認同和宣揚。在中國古代,“十三經”的形成過程表明,某種文獻能否列入“經書”范圍,不僅取決于士人階層的極力“推薦”,而且還取決于當時執政者的欣然“接納”。 馬克思說過:“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12]“十三經”中的任何一經,如果不能滿足統治者的統治需要,不經統治者的“同意”,就不可能入圍于“十三經”之中。經典的形成過程是文獻內在價值與外部權力話語共同作用的結果。相比較而言,后者的效果更為明顯,如漢代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對于儒家經典的形成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不僅如此,“十三經”中的某一經在某一時代或朝代受到格外重視,往往也取決于統治秩序的需要。如漢元帝、成帝以至哀帝時期,就出現了獨尊《春秋》到獨尊《詩》的轉換。當時統治者的首要任務就是麻醉人民,以掩蓋矛盾,從而決定了《詩》比《春秋》更能滿足統治者的需要。還有一個具體的原因是,當時外戚專權盛行,《春秋》所主張的“天子不臣母后之黨”顯然不利于外戚專權,而“《詩》則不然,它提倡‘溫柔敦厚’,目的是培養溫、良、恭、儉、讓的馴服工具……所以,為了維護專權,外戚當時也特別提倡《詩》教。 ”[13]凡此種種,表明文獻的“經典化”過程中始終伴隨著權力的介入。論述和評價文獻“經典化”過程中的權力介入的表現及其意義,應該成為文獻政治學研究的重要內容。
3.2 文獻整理活動中的權力介入
這里的“文獻整理活動”是一個廣義概念,它泛指古代所進行的文獻分類、編目以及編纂類書、政書、叢書、史書(正史書)等活動。從歷史事實看,中國古代官方的文獻整理活動中一直伴隨著權力的介入。本文前面論述的分類目錄編制中的“經→史→子→集”次序結構安排和類書編纂中的“天→地→人→事→物”次序結構安排,就是權力介入文獻整理活動所形成的結果。當然,這種結果不完全是權力影響使然,還有這種結構安排符合文獻整理所需要的客觀要求的原因,但沒有權力的介入,就不可能形成一種歷朝歷代一貫遵循的“永制”。西漢第10位皇帝宣帝劉詢召集的一次學術會議——石渠閣會議,其主要任務是“平《公羊》、《谷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最后“上親稱制臨決”。所謂“上親稱制臨決”就是由漢宣帝親自裁定評判。到了唐代,唐太宗令孔穎達編定《五經正義》,以最高統治者的名義結束儒學內部的宗派紛爭,為科舉取士和統一思想制定了“標準答案”。至清朝,康熙、雍正年間,統治者“御纂”、“欽定”的諸經注疏及各種類書、史書就達數十種之多。在中國歷史上,對文獻整理活動過問最多的皇帝恐屬清朝乾隆帝。在纂修《四庫全書》期間,江西巡撫海成查繳禁書“最為認真”,但由于他未能發現王錫侯《字貫》凡例內“將圣祖、世宗廟諱及朕御名字樣悉行開列”的嚴重“違礙”之處,乾隆毫不留情,立即將海成革職問罪。[14]諸如此類的皇帝親自干預文獻整理活動可視為權力介入文獻整理活動的典型表現。這表明,中國古代文獻整理活動所表現的“整序”過程并非是完全的自足行為,而必須是按照統治者需要進行的“尊指”、“尊令”行為。揭示和批判這種權力干預文獻整理活動的事實及其危害,應該成為文獻政治學研究的重要內容。
3.3 文獻傳播過程中的權力介入
文獻傳播的過程就是知識和思想傳播的過程。正因為文獻是思想傳播的重要載體,中國古代的集權統治者們不可能對文獻傳播活動采取寬容政策,而是要加以嚴格控制。在中國古代歷史上,秦朝發生的“焚書坑儒”事件是權力介入文獻傳播活動的典型案例。焚書坑儒的直接導火索是博士淳于越反對廢封建而立郡縣的制度,稱始皇不師古,于是丞相李斯認為鄙儒“以古非今”,應當禁絕“師古”的途徑,其辦法就是焚禁古書,絕其傳播。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李斯當時認為“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于是建議“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可以說,焚書坑儒是用行政權力干預文獻傳播,進而阻止非正統思想傳播的野蠻措施。明清時代盛行的“文字獄”現象,其實也是通過權力介入來限制文獻傳播進而規制思想傳播的高壓政策。如纂修《四庫全書》時,四庫館正式制定有《查辦違礙書籍條款》,明確申明“字句狂謬,詞語刺譏,必應銷毀”。該《條款》中有這樣一條規定:“錢謙益、呂留良、金堡、屈大均等除所自著之書俱應毀除外,若各書內有載入其議論,選及其詩詞者,原系他人所采錄,與伊等自著之書不同,應遵照原奉諭旨,將書內所引各條簽名抽毀,于原版內鏟除。”如果說,錢謙益等人的文獻遭此厄運,是因為他們的文獻中有“違礙”之處,那么,宋應星的《天工開物》被拒收于《四庫全書》如何解釋呢?只能解釋為當權者認為“奇技淫巧”無助于維護“三綱五常”之倫理秩序。據統計,乾隆皇帝親自領導的《四庫全書》禁書運動,共禁毀書籍三千一百多種、十五萬一千多部,銷毀書板八萬塊以上。[15]皇帝親自領導“文字獄”運動,足見權力干預文獻傳播對于維護統治秩序的重要意義。故此,闡明文獻傳播與權力秩序維護之間的關系,當為問先政治學研究的重要內容。
3.4 文獻闡釋活動中的權力介入
中國古代的文獻闡釋活動源源流長。漢魏人長于注經,唐宋人長于疏注,明清人長于辨考,這種圍繞經書而展開的闡釋學問叫做“經學”。自孔子開創“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風以來,歷代歷朝的無數學者們皓首窮經,手捧經書注疏不停,撰寫出了數百倍于原經篇幅的注疏著作。在“十三經”中,幾乎所有的經都存在“一經多注,一注多疏”的現象。根據多種目錄統計,“歷代易學著作多達6000-7000種,其中現存于世界的亦近3000種”。[16]后世把古代闡釋經典的學問起名為“訓詁學”。 那么,古人皓首窮經、前赴后繼地大量著述訓詁著作的意圖是什么呢?簡單地說,就是為了“明經”即明儒家經義。清人戴震在《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中說:“古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圣人之理義明……賢人圣人之理義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也。”對中國古代人來說,明儒家經義是每個有志者安身立命、登科升遷,進而實現立德、立言、立功理想的必由之路。反復訓解經義(即訓詁活動),就是明儒家經義的具體實踐。然而,中國古代的訓詁活動也不完全是純潔無暇的獨立學術活動,其中貫穿著各種形式的意識形態說教,留下權力介入的痕跡。上文提到的《五經正義》的編定,以及宋代朱熹的《四書章句集解》被確立為科舉取士的范本,就是權力介入訓詁活動的典型表現。許慎在《說文解字·序》中說道:“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在許慎看來,文字訓詁也要從“經藝之本,王政之始”的高度來對待。即使是對詩歌作品的訓詁,也貫穿著儒家綱常倫理說教。如 《詩經·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描寫的是女主人公望見梅子落地,引起青春將逝的傷感,希望有男子來求婚。但毛傳卻作了如下解:“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這首呼喚愛情的戀歌之所以被附會成“男女及時”的頌歌,就在于它符合一條儒家禮規:“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所以蕃育人民也。”可以說,《詩經》中大量描寫愛情的詩作大都被后來的訓詁學者作了“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的政治教化為旨趣的解釋。對《詩經》的訓解如此,對其他儒家經典的訓解也大都如此,限于篇幅,在此不作贅述。總之,辨識和剖析文獻闡釋活動中的權力介入的表現及其社會后果,應該成為文獻政治學研究的重要內容。
4 結語
本文的主旨不在于全面論述文獻政治學的學科性質和內容體系,而在于證明文獻政治學成立的可能性。筆者之所以提出“文獻政治學”這一新稱謂,意旨不在于標新立異或“發明”一種新學科,而在于試探圖書館學研究成果向其他學科輸出的可能性與必要性問題。長期以來,圖書館學一直處于社會“公認度”不高的局面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筆者看來,努力把圖書館學研究成果向其他學科輸出,是提高圖書館學的社會“公認度”的必要途徑。文獻政治學的研究成果有望被政治學、歷史學、闡釋學等學科“輸入”,也就是說,文獻政治學研究有利于圖書館學研究成果向其他學科的輸出。若然,筆者提出“文獻政治學”的目的達到也。
[1]單繼剛等.政治與倫理——應用政治哲學的視角[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8.
[2]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0.
[3]卡爾·斯密特.劉宗坤譯.政治的概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00.
[4]何長青.文獻是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邏輯起點[J].圖書館雜志,1992,(3):18-19.
[5]吳慰慈,董焱.圖書館學概論[M].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修訂 2 版,2008:33.
[6]于良芝,李曉新,王德恒.拓展社會的公共信息空間——21世紀中國公共圖書館可持續發展模式[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15.
[7]王陽明.王陽明全集(上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54-255.
[8]周予同.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844.
[9]弘歷.文淵閣記[A].李希泌,張淑華.中國歷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Z].北京:中華書局,1982:17.
[10]陳鼓應.易傳與道家思想[M].北京:三聯書店,1997:179.
[11]葛兆光.中國思想史(一)[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457.
[12]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
[13]晉文.論《春秋》《詩》《孝經》《禮》在漢代政治地位的轉移[J].山東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1992,(3):35-39.
[14][15]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63,74.
[16]周玉山.易學文獻原論(一)[J].周易研究,1993,(4):3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