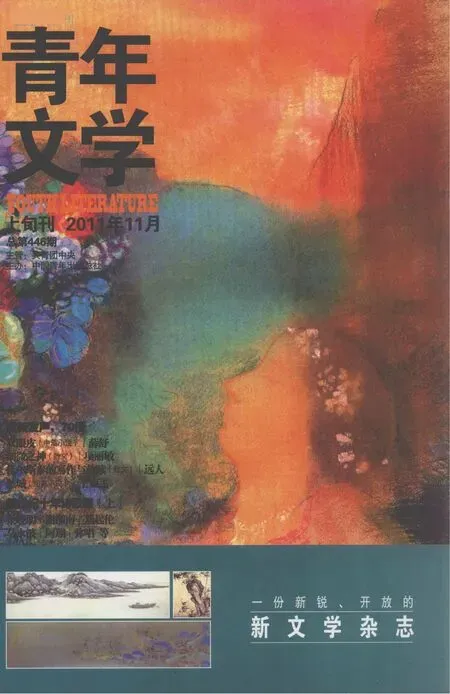婆媳
■青槐
一
寫下婆媳,我看見:
奶奶清瘦的影子在筆尖上閃了閃,一種溫暖在血脈里奔突,爬出眼眶時,居然染了淚的清涼。
一滴露趴在狗尾巴草肩上,它的影子里游著母親的影子。
三月,一炷檀香點燃春天,熏紅了桃花的臉。奶奶隔著土壤翻了個身,一樹的梨花便散了魂,追隨奶奶的白發而去。
春風如剪,剪出了杜鵑的黃衣裳,也剪斷了奶奶的佛號與最后一聲對我的呼喚。
沙河的水清澈啊,我投下蜷縮的悲傷,它還給了我一河床的卵石,每一個都流淌著資江河灘的圓潤。
二
日子是條流動的河,其寬度蓋不過資水,其深度蓋不過爺爺的皺紋。
一根纖長的竹篙,拄著流水的青春,在烏篷船的行程里漂洗河風。
河風吹老少年郎啊,十五當家的兒郎,用行船翻閱江南丘陵的厚度。
鄉親黝黑的笑容里,稻花扛不起的生命饑渴,全喂給奔騰不息的河風。
父親胸口的大紅花開了,一聲軍號揚起他青春的臉。低頭時,他發現腳下踩著的,是傳說中的高原雪景。
三
魚兒會跳,蝦兒會蹦,童年的天真走不出奶奶的叮嚀。
奶奶說:門前的河灘有鬼有神,可不敢下水游泳。
稍大點兒我明白,流水如瀑的寡婦灘,一渦回旋的水顛翻了行船,淹死了無數回家的夢。
每一次夢斷,奶奶便會在佛前靜坐,佛號輕誦。爾后的夜晚,奶奶的《苦婆婦》沿月瀑盤旋而上,砸進母親的眼里,濺得淚落如傾。
四
不識字的爺爺偷聽的《三字經》,在我童稚的嘴里圍爐夜坐。
逃災大娘的乞求點亮了煤油燈,她孫女的小腳印追著我的背影,在屋后的小山上爬了兩天,又隨著奶奶的淚光消失在腸子般糾結的山徑。
那一天,奶奶的黑夜很長,阿彌陀佛的輕誦,打濕了公雞的喔鳴。
五
母親的黑夜總是很瘦,扛不起備課本的體重。
母親的鋼筆喜歡走夜路,且擅長跳躍,它牽著煤油燈光線的袖角一蕩,便從春雨的深夜跳進雪落的清晨。
誰說交白卷是英雄?母親暴怒的巴掌掀翻了二蛋子壯壯的身影。
村莊的谷場上,二蛋子跪立的怯弱,在鄉親的呵斥里抖動。母親雙手如大鵝翅膀擋住了二蛋子父親的狂怒:孩子沒錯,那是廣播里播放的聲音。
六
奶奶用墳圈養的虔誠,是母親最初的哭泣、最后的感動。
今天,母親用退休完滿一段旅程。她的叩拜投在紙錢里,拔高了火苗的舌頭。
小本子上的數字一頁頁跳進火里,三十年的承諾,讓火苗讀給奶奶聽:在我的學校,一千多元,買來了百多個孩子讀書的身影。
一只喜鵲飛來,在墳角的椿樹上傾倒奶奶的笑聲。
七
屋角,奶奶刺繡的蓮花在蒲團上打坐,無助的渴望里,提醒母親念幾句佛語,求幾遍觀音。“生死契闊、三界苦深”的口頭禪,長在母親的嘴角,居然是淡淡的笑容。
燕子營巢,網住了春天的花事。
清明的細雨濃啊,淹沒了五指峰,卻淹不沒隨煙舞蹈的鞭炮聲。
枇杷微黃的絨毛里,白頭翁的尖喙穿出穿進。父親的吆喝被母親折斷:孩子們不在家,就讓白頭翁過一回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