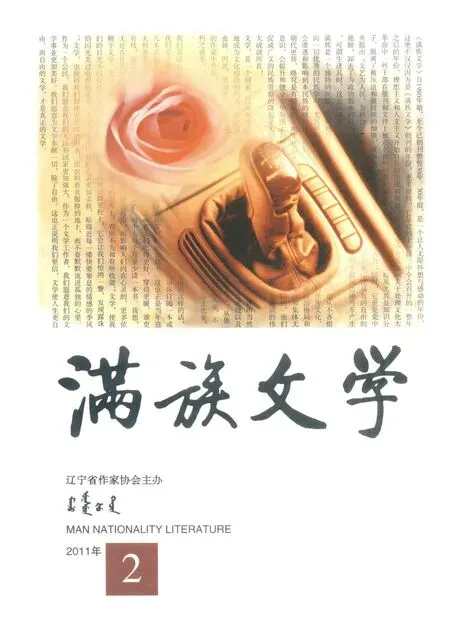哥本哈根冷飲店
張全友
哥本哈根冷飲店
張全友
從那間黑得像一個菜窖的地下室里出來,劉泊有些頭暈。太強了,這陽光。
他似乎覺察到自己被騙,而且騙得不輕,干凈徹底。五萬塊啊!這五萬塊錢,要是拿回去給老娘治眼,他想一定是夠了,那么老娘的眼,就不再是白內障,而會是一雙明亮的眼,給他再去補經常撕開口子的褲襠,就不會扎破手指頭了。要是拿上這些錢回村修房子,那間耳房也就會立豎豎地蓋起來,而不再是父親生前的滯留工程,像一個豁嘴唇的人臉那樣兒,一進院兒里,就很讓人別扭,更別說相親娶媳婦那層事了。要是去打家具,就是老娘經常念叨的準備給他辦喜事的那些家具,都可以打上一大排,甚至還要有余頭。
可是現在,五萬塊錢飛了,都投資到這個叫做“哥本哈根村”的地方。那個還算有幾分姿色的、著一身淺灰色西服的中年女人的笑臉,還在他的腦海里晃悠。她確實有幾分姿色。劉泊在那樣黑的地下室里,竟然能夠辨別出她是穿著一身淺灰色的衣服,而且西裝,是那種緊身的,還有一張笑臉。劉泊很佩服自己的識別能力,但他也最恨自己天真,做事嫩點,不是一般的嫩,簡直是個悶頭鱉。
劉泊低頭走路。準確說,他不知道路的方向。再準確說,是連東西南北都辨別不出的樣子,簡直像一只無頭蒼蠅。但大街上很繁華,這一點他知道,因為人來人往,車水馬龍,一股腦地老往他眼里鉆,由不得他拒絕這些。
那個所謂的“哥本哈根村”,其實是一家地下投資公司。說白了,就是那種政府打擊的黑傳銷組織。可是他不知道為什么要叫哥本哈根。哥本哈根是什么地方?劉泊隱約在電視上知道一二,那是人家西歐丹麥的首都。記得有幅外國的畫,畫的是一位警察阻斷了所有交通,以便讓一個母鴨子帶領它的鴨兒女們橫過馬路,說的就是那個哥本哈根。可是這個城市不是那樣,這個城市很擁堵,是那種到處都是人肉翻卷氣味熏熏的大都市。那些遠處錯落有致的摩天大廈,老有要傾倒下來砸在他身上的感覺。
劉泊從來沒有到過這樣大的城市,心里難免有點隔膜。他感到了陌生,所有的人陌生,所有的物陌生,就連這座城市叫什么,都忘記了。這種陌生感,鬧得他很不自在,以至于神經深處老往上翻著一波一波的激靈,是那種冷激靈。劉泊實在搞不懂自己,為什么會來到這樣一個陌生的地方——哥本哈根村。他給這座城市就命名了這個名字:哥本哈根村。這個村,比起他們那個遠方的小山村,可是大多了。本來,是想到這個什么哥本哈根搞到一大筆錢,然后回去修房子娶妻生子孝敬老娘,對了,再給她治治那雙白內障的眼,可是沒想到現在卻陷進去五萬。五萬塊錢,要擱在有錢人身上,也許只是一根汗毛。但劉泊不行,他整整花了三年時間,在一個小縣城里做那種頭頂安全帽的小工,辛苦攢下這些錢。原本也知足,但表哥說去哥本哈根吧,咱弟兄不能一輩子就做這種小工,咱也要做做老板。劉泊表哥叫馬廣利,他也準備了五萬。劉泊抽下去整整兩包煙,聽了馬廣利一夜介紹,終于下定決心跟他一起來這個地方投資。他甚至憧憬著一幅未來美好生活的圖景:有了大把大把的錢,應該如何來享受?搞幾個保姆來伺候老娘?建一座別墅在海邊?要有健身房和游泳池的那種。最好再配套洋人們玩的那種高爾夫和賽馬場……
可是現在表哥呢?他唯一認識的馬廣利這小子,現在也不見了。
劉泊開始發躁,躁極了。這樣一躁,還伴著點慌,心一慌,就口渴。他隨便找到了一家冷飲店,大聲喊:“來一聽啤酒,要冰鎮的。狗日的南方,賊熱。”
劉泊打一個響指兒,很流氣的那個樣。他這也是習慣,在家鄉的時候,縣城一條街上,誰都知道他好打一個手指響兒。
這家冷飲店里,人很少,就三五個,還有一女的。這幾個人都坐在臨近寬敞明亮的玻璃櫥窗前眊大街。正是上午時分,這條街上的繁華,像汛期的壺口瀑布,一浪高過一浪。劉泊心想:南方人,都瘋了,賺錢賺瘋了。他又想起來自己那五萬塊錢,心里一疼,就來了氣。
“怎么你們都聾啦?老子喊你們,人都死光啦?!”
也許是劉泊的口氣太過響亮,那幾個人不約而同投過了各種各樣的目光。有一個男的,還一邊噓噓著斜眼過來,一邊悶聲道:“什么玩意兒。”
這句話被劉泊聽到了。
此時,一個女服務員從里邊房間的哪個角落出來,問他:“怠慢了。您要點什么?”
劉泊早不再去搭理她。他移步過來,右手的食指像一把手槍的槍管,頭還惡狠狠地歪著,沖剛才說話那男的問:“你說什么?給老子再重復一遍!”
那男的也不示弱,呼的一下站起來。原來這人是那么的魁梧高大,像一座水塔,黑著一張臉。“我說你不是東西!”
劉泊心里本來窩火,無名的火。他大概是氣自己氣過了頭吧,似乎要專門想找一個硬朗些的家伙來教訓自己一下,一看眼前這位,心想也正合適。那塊頭,一拳頭落下,就夠你好受一陣子。劉泊甚至希望對面這家伙,最好把自己給揍死算了,免得再去拖累別人。“你罵老子,我操你八輩祖宗——”
那男的仿佛被劉泊一下給怔住了,雖然像一座水塔,可站在那里巴眨著眼,嘴巴氣得都哆嗦了,一會兒紫一會兒青的,就是發作不起來。
同坐的幾位,也站起來,就勸上了:“志華,算了,犯不著跟一個生驢子叫勁。走,咱們不喝了。”
這話要是另外某個男的說的,劉泊也許就沒有多大興趣。可偏偏是那女的。劉泊今天特反感女人。他在糊里糊涂把那五萬塊錢交給那個有幾分姿色的、著一身淺灰色西服的中年女人之后,從那間黑屋子里出來,心里就納悶:女人?如此厲害?自己就這樣輕易上了她的賊船?現在,面前這個女人又說自己生驢子什么的,仿佛還真觸到了他的某個痛處。
劉泊二話沒說,掄起就是一拳頭,砸了那女人個滿面飛紅花。
劉泊這一拳頭太厲害,不僅砸了那女人個滿面開花,他還捎帶了一句天地不搭邊的發狠的咒罵,莫名其妙,不計后果,一起痛快做下。
在場的幾位男士,被眼前的陣勢給弄愣了片刻。不妨去假設一下:他們是親友相聚?是生意伙伴?或者是同學路遇?反正,不管屬于哪一種人際結構,同時來到這家冷飲店里,突然發生了這種事請,都不會袖手旁觀。最先是那個叫什么志華的,上來就將劉泊給攔腰抱住了。另一位還欲將劉泊的一條胳膊反扭住。再一位是上去扶那倒地的女的。他在從懷兜里往外掏衛生紙的時候,把手機帶出來。那只手機落地的聲音十分清脆,“咣啷”一下掉在了烏黑瓦亮的瓷磚地面上。
“快,快打110報警。”那女的呼哧著紅紅的鼻子說。
一直被嚇壞了的那個女服務員,急忙朝里邊跑去,邊跑邊尖叫:“不好啦,殺人啦——”
劉泊笑了。他也不知道自己為什么,偏偏會在這個時候,突然噗嗤一下,笑了。
劉泊松了松膀子,然后又緊了緊,一抖,竟然一下就把上來的幾位高大男人,給抖趴下了。看來,這些城里人真是不經整,別看他們個個長得威武兇猛,一身的肥膘,原來都是虛的,是一個個紙老虎。劉泊還去一方桌子上揪起一個空酒瓶,在桌沿兒“啪嚓”磕碎,手里握著玻璃碴銳利的瓶子把兒,指著地上趴著的幾位:“你們都給我學乖點兒。不然,都送你們去見閻王!”
事情發展到這一步,也就有一些熱鬧可看。這個劉泊自己認為就叫哥本哈根村的大都市,沒有哪條街不是熙熙攘攘。眼下這家冷飲店所臨的這條街,自然不會例外,大街上過往的行人,到底也有不少樂于觀看此等熱鬧的人。他們有的伏在那些櫥窗玻璃上,向里邊窺探。有的兩條胳膊架起來,抱在懷前,腳尖還在地上墊著,仿佛做一種聽什么音樂時的自然跟拍,立著靠在門邊上,很陶醉很悠然地靜盯著劉泊跟里邊這些人。他們大約共同期待著更精彩的一幕即將發生。
更有一位老漢,看上去像一位老干部模樣,已是白發蒼蒼,留著個大背頭,長一臉肉疙瘩麻子,個子不高也不矮,不胖也不瘦,穿著一簾大褲衩,一只手拎著一把芭蕉扇,另一只手握著一只白玉色的牙簽在剔牙。不過,他嘴卻不閑著,用變調的口氣冷冷地說:“嗯,不錯。不過,不夠過癮。這要是我二十年前遇到的陣勢,起碼不會像他現在這樣窩囊,叫外面看熱鬧的人心里發癢卻沒處抓,我會滿足所有喜歡看熱鬧人的眼癮。”老漢說過這些話,收起了那只牙簽,很神奇地從后背抽出一個X型的小馬扎,坐下來,回頭還喊正在偷著笑的矮他許多的另一個老漢:“拿出來,殺兩局。”
他們就在這家冷飲店的門側邊兒上開了殺戒。楚河漢界。將士象馬車炮兵。
一個衣著更為整潔略顯發胖臉盤平板眼睛小小的中年男人走過來。
“諸位諸位,不要再鬧了,不就是話不投機嗎?小事一樁,大家都消消氣,都坐下來,今個我請你們客。小玲,上啤酒,冰鎮的——”
“你是老板?”劉泊回頭問他。
那人先是笑臉點了一下頭,隨手就把劉泊手上的破酒瓶給拿下了。
可沒成想,那人臉色一變,黑了下來,順手從一個衣兜里摸出了一副手銬,給他結結實實干凈利索地戴在了手上。
“跟你小子多日了,還敢跑這里鬧事撒野!”
這時候,地上的那幾位也都踉踉蹌蹌站起來。“真是倒霉晦氣,碰上殺人犯了。”
“老子不是殺人犯!大不了判幾年,到時候還會再來找你們算賬!”
那幾個人的臉色更加驚恐地看過來,“你就是殺人犯,吃槍子去吧你!”
那警察逮著劉泊往外拉。在經過兩老漢下棋攤子的時候,劉泊使勁探著用腳尖去踢翻了他們的楚河漢界。
一枚枚棋子兒,可憐兮兮地滾落到哥本哈根大街上的任意一個角落,像夜空中一粒粒散落的星星。有一粒,竟然不偏不倚飛進了那個專注于棋局老者的嘴里。
白發蒼蒼老干部模樣的老漢,一口吐出了那粒棋子,這下反倒樂了,“好,這才是個漢子樣兒。”
劉泊看了老漢一眼。老漢似乎還沖他豎了一下大拇哥。
“24號,提。”
幾個身著警服的人把劉泊帶到了一間審訊室。
劉泊現在不叫劉泊了,叫了24號。
他被一輛警車周折了三天三夜,從哥本哈根村押回了北方那個他出生的小縣城。
“說,你去搶愛民飯店,到底分了多少贓?”
“五萬。”
“同伙都是誰?”
“馬廣利,沒了。”
“就你們兩個?”
“兩個。”
“那你現在給我們交待一下,你們是怎么去搶愛民飯店的?誰是主謀?”
劉泊動了動肩膀,又動了動。“我為什么不老實交待?我媽說,都是他們教壞了我,現在,我到了這一步,還能怎么樣?老實不老實,你們不相信,可以隨便去調查。”
劉泊本來有一句口頭禪:他媽的,老子。可是到底覺得這里不是發泄的地方,一咬牙,這些都咽回肚子里去了。
“現在不是要你表白什么,說,誰是主謀?”
“馬廣利。”
“馬廣利在逃。我們遲早會抓住他和你對質。”
“我當然不怕你們對質,我巴不得。”
“你在那家冷飲店里大打出手,那個女人的孩子死了。”
“沒有,她就一個人,她并沒有帶孩子去啊!”
“你說她沒有帶孩子?女人的孩子都在肚子里,你難道連這個也不懂?”
“……”
“你是暴力搶劫,故意殺人。”
“……”
“你還有什么話要說?”
劉泊搖搖頭,表示沒有什么可說。
“你真是一個離奇的人。”一個警察說。說這話的,好像還是個女警察。
太陽升起來的時候,也是劉泊將要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了。他想,他現在什么人也不想再見到,最好干凈如茫茫沙漠一樣的那種孤獨。一枚餓狼似的子彈,瞬息間吞噬掉他的生命。那樣最好。那個女警察說他真是個離奇的人。沒錯,他自認為自己很離奇,還古怪,干脆不是人,一頭四不像的東西。
一個胖子警察喊他:“快點起來!你的覺睡過頭了,要睡,到那邊去睡吧,那里沒人再管你。”
劉泊被兩個警察架了胳肢窩,腳鐐碰擊水泥地板的聲音很響。他認真環顧了下四周:走廊、夾道、一處小花園。再遠一些,是一排鋼筋結構的圍欄。外面,是一條依然很熱鬧的大街。那大街,也不亞于哥本哈根的那條街。街上,像鄉下夏季茅廁里蠅蛆似的人們,偶爾送過來的一瞥,也是那樣仇視他的目光。劉泊現在已經沒有多少留戀這個世界的意思。但他就不明白了,這世界所有他遇到的人,為什么要如此地憎恨他?他知道,假如那個在哥本哈根冷飲店里遇到的女人恨他,哪怕親自來殺了他,他也會坦然就范。可是現在的情形是,他似乎得罪了這個世界的所有人?這讓他無論如何也想不明白。
劉泊被塞進了一輛裝著鐵籠子的囚車。那層網狀的隔層,把他與這個熙熙攘攘的世界分開。當然,這并不影響他看到人們的嘴臉。他有點不甘心。哥本哈根、冷飲店、房子家具、媳婦,統統他娘的滾蛋!他想再找找那雙眼睛,是媽媽的眼睛。他很認真地找,幾個十分熟悉卻依然是仇恨的面孔進入他的視線。馬廣利竟然也混雜在那里面,同樣是仇恨?再過去一點,他終于看到了他的媽媽。那個白發蒼蒼的老人,她兩手使勁地伸著,朝著他這里。那被人們簇來擁去的身子,淚水飛濺,蓬頭垢面。劉泊意外地送去一個微笑,給他的媽媽。
“啪嚓——”
一顆子彈穿透了他的心臟。他知道,一般槍決罪犯,子彈是對準腦袋放的。可是他,怎么要擊穿他的心臟?不過,他已經沒有時間來做這些分析。他下面的任務是:去死吧。
起來起來!做事啦!
從那間黑的像一個菜窖的木板工棚里出來,劉泊確實有些頭暈。
外面的陽光,太強了。不遠處的那些樓房,都仿佛燃燒起來似的,扭動著它們的腰身。
照舊是,吃飯:饅頭燴菜外加一碗白開水。做工:把太陽從東邊請出來,背在背上,腰要弓著,四肢不停地跳動,直到將太陽送去西邊的山下。晚上看錄像。
昨晚錄像看得太遲了,一部警匪片,看到了子夜時分。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到工棚里,倒頭就進入了那個可怕的夢里。
劉泊多么希望自己就是夢里的那個劉泊:去搶,去什么哥本哈根撒野,還遇到了幾個有些姿色的女人。哪怕去警局里蹲監獄,吃槍子也痛快。可惜,不是。那只是個夢:哥本哈根村?冷飲店?自己去搶劫殺人?都是子虛烏有。現實是,劉泊他要繼續做工。他老娘的眼,也要繼續白內障下去。家里那間房子,今年也許會去修繕一下了。到時候看看工錢結算情況怎樣。媳婦嗎,還是遙遙無期。表哥馬廣利說,他們村里有個寡婦,人長得還算不錯,就是身邊有一個孩子。她男人去浙江打工,都快九年了也不見再回來,想必早死了。
劉泊給表哥的回話是,等等吧,等回去了再說。
劉泊心想:哥本哈根也許真的有那么一家冷飲店。自己看來是要好好攢些錢了,將來或許真的會去那里走一遭。
〔責任編輯 宋長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