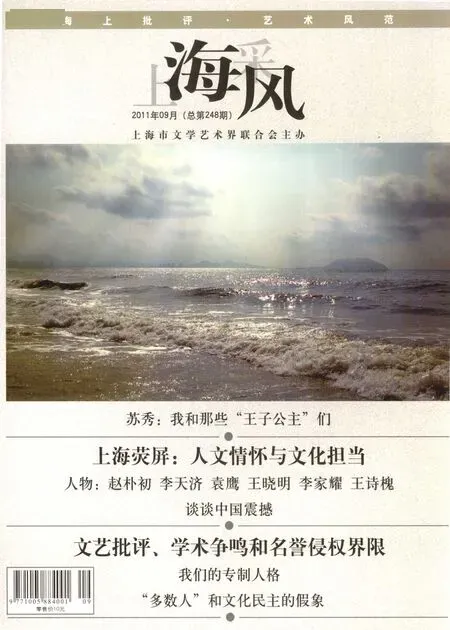回到中國
文/于 堅
今天,國際化已經成為一場如火如荼的中國運動。許多地方領導甫一上任,立馬想到的就是將這個地方“國際化”。國際化是一套現成模式,隨之而來的就是拆遷、移民。其行事風格,就像占領軍司令,完全不顧地方的歷史、廟堂、文化和人民積累千年的地方生活經驗。將一種全新的生活模式、建筑格局強加給有著幾千年傳統的生活世界,似乎當地人從來沒有生活過,他們野蠻到連房子都不會蓋。
這些司令甚至都沒有時間去翻翻當地的史冊,其實在司令們的“新世界”到來之前,地方一直在將此地作為“神社”、“魚米之鄉”來記載、歌頌并安居著的。按理說,來到一個地方施政,首先要尊重,地方是一個已經完成的“重”,那是別人傳宗接代的故鄉、盤根錯節的家園,不是一張白紙。一個地方有一個地方的生活經驗,這是歷史、文化、語言、傳統、風俗、氣候、地理位置等等決定的。執政者首先要問道于地方上的父老鄉親儒生漁父,起碼要問問,在這個地方,要怎樣生活才是幸福。或者幸福曾經是如何的。但不然,往往是視之為蠻荒,舍我其誰,在我之前的一切都是落后,一個字:拆。許多地方,傳統家園早已拆掉,如今拆著的是前任的“政績”了(有些地方已經在拆前任的形象工程了)。
司令們人手一冊的施工圖千篇一律,國際化,不外乎就是照搬美國、歐洲、新加坡、日本……這些地方的模式。他們忘記了一點,美國是美國人根據美國地方因地制宜的結果,歐洲是根據歐洲地方因地制宜的結果。最近看到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對美國的評論,他認為那地方“無聊得要命”、“令人氣餒的荒涼,美國95%是一個丑陋、教人喘不過氣來的、各人自掃門前雪的國家,總之無可救藥的平淡”、“只需走一小段高速公路……就可以勾勒出美國的輪廓”……卡爾維諾這么說,是基于他的意大利地方生活經驗。
在全球化勢如破竹的今天,國際化無法回避。國際化是經濟運動,是用貨幣重估某些價值,它只是權宜之計,而不是大道。如果國際化最后僅僅是接上了那兩根直挺挺的軌,與地方的復雜深厚豐富多元的生活經驗水火不容;如果那些以摧毀“車如流水馬如龍”、“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的生活世界為代價建起的“國際”,只是一座座水泥鬼城;如果高速公路終端只是死去的河流、有毒的田野、寂靜的春天,人民要這種“國際化”干什么呢?
“削足適履”這個成語的意思恐怕許多人已經忘記了。在我看來,今天許多“國際化”,其實都在削足適履。那些慘烈的拆遷,起因無不是當局者執意要削足適履。削足適履與因地制宜是兩種不同的方式,前者要命后者生生。可怕的是今天的中國地方,“國際化”似乎越來越成為“道”了,老子所謂的“非常道”也被國際化了。因地制宜比“國際化”麻煩得多。國際化其實很容易,圖紙就是那幾份。鞋匠造鞋很麻煩的,要創造出各式各樣的細節、分寸、尺度、角度、厚薄、輕重、軟硬,只有如此,鞋才適足,飄然上路。如果所有的鞋都是一號,它就要被天足們一雙雙先后蹬掉。纏足,硬搞了幾百年,大道上血淋淋的,最后還不是回到天足了么?削足很容易,也很痛快,但這是絕后之技,后患無窮。因地制宜很麻煩,但那是大道。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我以為,走向國際,最終是為了回到中國故鄉,回到中國經驗,回到中國的“生生之謂易”、回到安居樂業這個大道,而不是永遠在國際上漂泊、流浪、灰塵滾滾地疲于奔命。這與古代圣賢的社會理想是一致的。中國文化喜歡講衣錦還鄉,如果只顧衣錦而失去了故鄉,那么我們將有去無回,只是孤魂野鬼而已。如果“國際化”最終不能使人們重建故鄉世界的生活經驗,重建漢語文學記憶中的生活天堂,那么一切還是要重新來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