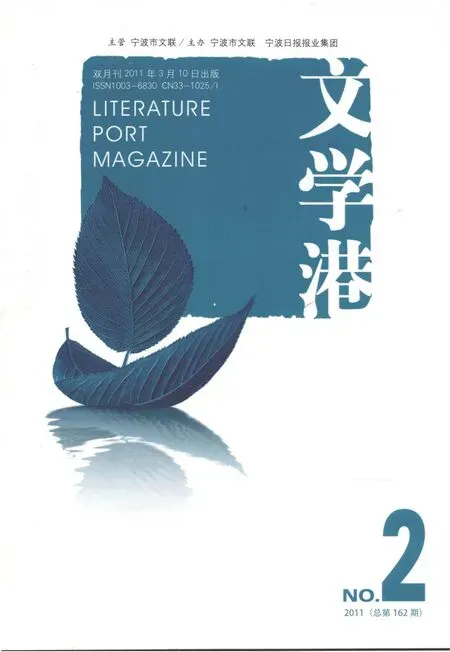讓那些沉默的女性開(kāi)口說(shuō)話
——論蔡康《紅顏宿命:古籍中的女性》
任茹文
讓那些沉默的女性開(kāi)口說(shuō)話
——論蔡康《紅顏宿命:古籍中的女性》
任茹文
蔡康的新作《紅顏宿命——古籍中的女性》是一本生動(dòng)、有趣而十分嚴(yán)謹(jǐn)?shù)臅?shū),應(yīng)該說(shuō),我們很難準(zhǔn)確描述它的面貌和性質(zhì)。總體來(lái)說(shuō),它具有學(xué)術(shù)隨筆的嚴(yán)肅性,但在很多時(shí)候它又流露出某種新歷史小說(shuō)鋪演的生動(dòng)性。書(shū)中篇目單獨(dú)成文,以某部文學(xué)作品或歷史傳記中的女性為論述的對(duì)象,如《楊玉環(huán)的情天恨海》、《李師師的花枝清淚》,又如《唐琬的驚鴻凄影》、《貂蟬的鳳儀悲歌》。溯其源頭,這本書(shū)是作者從報(bào)紙讀書(shū)專欄文章拓展開(kāi)來(lái)的一系列讀書(shū)隨筆,這就可以理解里面所收文章大多兼具嚴(yán)謹(jǐn)?shù)膶W(xué)術(shù)氣和嫵媚的通俗性特點(diǎn)。因?yàn)槿珪?shū)的研究對(duì)象是古籍中的女性,又因?yàn)檫@些女性大多具有傳奇故事,因此文章題目在規(guī)整的形式中仿佛帶著通感意義上的旖旎脂粉氣。但細(xì)看文章,發(fā)現(xiàn)里面既有綿密的史料考證,有對(duì)社會(huì)世態(tài)和人情世故的精彩詮釋,也有根據(jù)作者的理解和想象而使之完善和鮮明起來(lái)的人物形象。
從考證功夫上看,作者在材料收集和細(xì)節(jié)推理上頗費(fèi)心力,如閻婆惜一家為何要離開(kāi)熟悉的東京而去陌生的山東?經(jīng)過(guò)分析作者認(rèn)為是去投奔閻婆惜在“行院”相識(shí)的一個(gè)客人;如對(duì)貂蟬身世的推測(cè),作者認(rèn)為貂蟬十分干脆且堅(jiān)決地接受一個(gè)以自己一生命運(yùn)為代價(jià)的重任,一方面是為了報(bào)答王允的養(yǎng)育之恩,另一方面也表現(xiàn)出對(duì)朝廷當(dāng)權(quán)者的刻骨仇恨。而自幼入府過(guò)著相對(duì)安定生活的貂蟬似乎不會(huì)有如此的切齒之恨,除非她的家庭曾遭受過(guò)種種傾軋和迫害,抑或親人死于非命,因此才有難以消除的切膚之痛和報(bào)仇雪恨的無(wú)畏心愿。這也從另一個(gè)角度說(shuō)明她有可能出身于敗落之家。
類(lèi)似這樣的闡釋和推測(cè)是從小說(shuō)文字的空白中得來(lái),是建立在閱讀體悟和歷史佐證基礎(chǔ)上的內(nèi)涵延伸,可以解答如我這樣的讀者在閱讀過(guò)程中的多年疑惑。當(dāng)然,我要說(shuō)的重點(diǎn)既不在于作者的考證功夫,也不在于通過(guò)文字空白所推演出的微言大義,前者對(duì)于本書(shū)來(lái)說(shuō)只是寫(xiě)作的基礎(chǔ),而后者則幾乎是所有讀書(shū)隨筆存在的價(jià)值和理由。這里,我想著重談?wù)勛髡邔?duì)廣泛涉及到的古籍進(jìn)行闡釋時(shí)所采取的立場(chǎng),當(dāng)然,這些立場(chǎng)可能敞亮也可能隱蔽,可能意識(shí)也可能無(wú)意識(shí)。
世事洞明皆學(xué)問(wèn),人情練達(dá)即文章。《紅顏宿命》一書(shū)在對(duì)很多古籍女性人生命運(yùn)的闡釋中,很有意味的部分是對(duì)古今相同的世態(tài)人情的準(zhǔn)確分析,文學(xué)社會(huì)學(xué)的視角使人物的存在有了清晰的背景,使我們對(duì)于貂蟬、孫尚香、杜十娘等女性人物所處的社會(huì)時(shí)代有了準(zhǔn)確的認(rèn)知。丹納在《藝術(shù)哲學(xué)》中曾深入分析種族、時(shí)代和環(huán)境三者和文學(xué)之間的密切聯(lián)系。文學(xué)社會(huì)學(xué)的視角使蔡康對(duì)這三者、尤其是環(huán)境對(duì)于人物命運(yùn)的形成作用有特別的敏感和獨(dú)到的把握。如《白秀英的勾欄劇目》中,作者分析《水滸傳》中的白秀英引來(lái)殺身之禍的前因后果,一個(gè)小女子的遭遇折射出錯(cuò)綜復(fù)雜的社會(huì)脈絡(luò)。作者在分析白秀英何以來(lái)到鄆城,又何以得罪雷橫時(shí),充分注意到人物身份與周?chē)h(huán)境的膠著關(guān)系,“即使與知縣有這樣一層關(guān)系,作為藝人的白秀英父女初來(lái)乍到還是處處陪著小心,唯恐稍有疏忽,得罪了鄆城縣方方面面的頭面人物,因此連小小的都頭雷橫也在事前 ‘參拜’之列。由此可見(jiàn),干這營(yíng)生確實(shí)不容易,用張青的話說(shuō)就是 ‘沖州撞府,逢場(chǎng)作戲,賠了多少小心’!”又如分析貂蟬的身世時(shí)作者寫(xiě)道:“另一種可能是家境敗落,無(wú)以為生,或無(wú)人撫養(yǎng),只能賣(mài)身入府,而這個(gè)敗落的過(guò)程最能體味世態(tài)炎涼,貂蟬從而早熟,從而精明,從而懂得人情世故和種種手段。”
王國(guó)維在《人間詞話》中說(shuō):“‘君王枉把平陳業(yè),換得雷塘數(shù)畝田’,政治家之言也。‘長(zhǎng)陵亦是閑丘垅,異日誰(shuí)知與仲多’,詩(shī)人之言也。政治家之言,域于一人一事。詩(shī)人之言,則通古今而觀之。詩(shī)人觀物須用詩(shī)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故感事懷古當(dāng)與壽詞同為詞家所禁也。”①盡管有對(duì)世故人情的通脫認(rèn)識(shí),但蔡康以“詩(shī)人之眼”來(lái)觀察和評(píng)價(jià)古代女性,倫理情感是梳理人物命運(yùn)與人物關(guān)系的主要脈絡(luò),這就十分準(zhǔn)確地點(diǎn)出了很多古籍中的女性命運(yùn)何以悲劇的成因,如對(duì)《三國(guó)演義》中孫權(quán)之妹、劉備之妻孫尚香的分析有三個(gè)要點(diǎn):一是孫尚香的庶出身份,“作為庶出,孫尚香在同父異母哥哥孫權(quán)的眼里向來(lái)無(wú)足輕重,更談不上骨肉情深。這從周瑜提出用孫尚香作誘餌孫權(quán)當(dāng)即表示贊同可以看出,也可以從后來(lái)孫權(quán)對(duì)蔣欽、周泰下的命令 ‘汝二人將這口劍去取吾妹并劉備的頭來(lái)’中得到印證。其二是孫尚香的性格“志勝男兒”,這與她特殊的生活環(huán)境和顯赫的社會(huì)地位有關(guān)。其三是孫尚香與其母親的關(guān)系及其母親在東吳影響力的消長(zhǎng),雖然孫尚香是東吳老祖宗吳國(guó)太的“甚愛(ài)幼女”,但年邁的國(guó)太畢竟不能庇護(hù)她一生,因此她在東吳不管嫁誰(shuí),都很難消除這心中的陰影。這層層遞進(jìn)的分析就將《三國(guó)演義》中著墨不多的孫尚香演繹得十分準(zhǔn)確。
另外,在對(duì)歷史人物的評(píng)價(jià)中,作者作了人道意義上的準(zhǔn)確還原,關(guān)于李清照的分析尤其如此。除了個(gè)人的小環(huán)境,還有時(shí)代的大環(huán)境,大小環(huán)境相互結(jié)合共同鋪就個(gè)體的人生道路,這樣的規(guī)律對(duì)李清照來(lái)說(shuō)尤其適用。作者在《李清照的秋雨黃昏》一文中這樣分析:如果說(shuō)李清照“欲語(yǔ)還休”的原因是個(gè)人的“閑愁暗恨”,那么爾后“欲語(yǔ)淚先流”的原因便是國(guó)破家亡帶來(lái)的“物是人非事事休”了。靖康元年 (1126年),金兵南下,遼闊的中原再也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shū)案,閨閣才女李清照也由此開(kāi)始了她后半輩子的凄涼歲月。因此,作者揣測(cè)道,也許臨終前李清照也悲哀地覺(jué)得在這樣的時(shí)代和社會(huì),才藻確非女子事也。這一個(gè)案經(jīng)典性地詮釋作者在分析多位女性時(shí)反復(fù)表達(dá)的一個(gè)核心觀點(diǎn):生活方式可以選擇,社會(huì)環(huán)境卻無(wú)法選擇,社會(huì)環(huán)境是影響個(gè)人命運(yùn)最不鮮明但力量卻最大的一個(gè)因素。因此,歷史上的很多杰出女性由于個(gè)人生存環(huán)境和時(shí)代社會(huì)環(huán)境的巨大落差而使她們的命運(yùn)具有悲劇宿命色彩。
在古代典籍的眾多故事中,女性往往被剝奪了言語(yǔ)權(quán),通過(guò)男性作者的視角展現(xiàn)她們的心理和命運(yùn)。《紅顏宿命》一書(shū)中作者采取的是沉默的女性視角,為弱小女性悲呼是本書(shū)的基本立場(chǎng)。如對(duì)林沖娘子張氏人生道路的闡釋:林沖被發(fā)配了,面對(duì)虎視眈眈一心想把她娶到手的高衙內(nèi),留在東京的張氏想靠父親張教頭的庇護(hù),等到丈夫歸來(lái)是萬(wàn)萬(wàn)不可能了。對(duì)這一事件的幾種結(jié)局看得比較清楚的是賣(mài)友求榮的陸謙,他說(shuō)過(guò),這事只除她自縊便罷。果然,走投無(wú)路的張氏最后終于徹底絕望,自縊身死,為林沖保持了自身的貞操和清白,也為自己連名字都沒(méi)留下的一生畫(huà)上了一個(gè)辛酸和悲哀的句號(hào)。也許,在生命的最后時(shí)刻,她終于看清了這個(gè)殘酷的尤其對(duì)女性更為殘忍的“清平世界”的真正面目。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這本書(shū)中選擇的對(duì)象有多位是青樓女子,如白秀英、閻婆惜和杜十娘,對(duì)于她們的身世,作者大多結(jié)合時(shí)代環(huán)境的多重因素作綿密梳理,如對(duì)杜十娘的分析:小杜微入行院成了名姬杜十娘后,擁有了不下萬(wàn)金的“百寶箱”。她因?yàn)橛邪賹毾涠@得從容與不凡,也因?yàn)橛邪賹毾涠兊糜字膳c盲目,從而把終身托付給了不該托付之人。作者最后寫(xiě)道:自絕之人往往選擇獨(dú)自悄悄踏上不歸之路,但杜十娘偏偏愿意在眾目睽睽之下把一切有價(jià)值的東西撕碎給人看。她要讓人知道她所擁有的巨大財(cái)富,這是她受無(wú)數(shù)人追捧的見(jiàn)證。她就是要在李甲的悔恨和孫富的吃驚中把價(jià)值萬(wàn)金的百寶一一毀掉;她就是要在眾人的惋惜和流涕中把“渾身雅艷,遍體嬌香”的自己毀滅,她就是要用自己生命的代價(jià)給天地間留下永恒的嘆息。又如在《李師師的花枝清淚》中,作者這樣分析:紅顏?zhàn)怨疟∶凇般俱矡o(wú)復(fù)向來(lái)之態(tài)”的今日,仍有人深情地盼望著她的“江南梅萼”,李師師傷心傷感之余,該為有周邦彥這樣的一生知音而欣慰了。
另一個(gè)值得注意的視點(diǎn)是,《紅顏宿命》的視角是以現(xiàn)代人看古代人,一個(gè)現(xiàn)代人撩起歷史帷幕的一角看古代生活場(chǎng)景下的滄海桑田,因此便有一種時(shí)空的古今雜糅交錯(cuò)的效果。在古代與現(xiàn)代的視點(diǎn)交錯(cuò)鋪演歷史,是歷史隨筆的文體特點(diǎn),它可以用現(xiàn)代人的觀點(diǎn)觀照古人。《潘巧云的情動(dòng)無(wú)忌》一文讓我想起二十世紀(jì)三十年代心理現(xiàn)實(shí)主義小說(shuō)家施蟄存“將歷史重做”的小說(shuō)《石秀之戀》,在文本的重構(gòu)中,“貞潔與放蕩”、“懲戒與占有”、“美麗與邪惡”、“欲望與險(xiǎn)惡”構(gòu)成多重反諷,從而形成豐富的藝術(shù)張力。施蟄存認(rèn)為《水滸傳》中石秀的“力比多”帶著正義的面具得以釋放,在偽裝的表象下體現(xiàn)出畸形的性意識(shí),《石秀之戀》一文解構(gòu)了梁山好漢仗義的形象。《紅顏宿命》中《潘巧云的情動(dòng)無(wú)忌》也具有這樣的解構(gòu)思維,作者分析道:在這場(chǎng)替人捉奸的義舉中,石秀的動(dòng)機(jī)大可存疑,石秀的舉動(dòng)令人費(fèi)解。一個(gè)販羊挑柴的粗人,值得嫁過(guò)兩任押司且有心儀的師兄暗戀著的潘巧云常常說(shuō)“風(fēng)話”么?在翠屏山上,石秀把該證明的事情通過(guò)楊雄的刑訊逼供一一落實(shí)了,唯獨(dú)沒(méi)再提那“風(fēng)話”一事,是他忘了,還是不想讓楊雄增添更多的煩惱,抑或本來(lái)就是不敢當(dāng)面對(duì)證的無(wú)中生有自作多情?又如在《潘金蓮的情竿殘酒》和《孫二娘的十字兇坡》兩篇文章中,作者相互對(duì)照并借金圣嘆之口點(diǎn)出了武松的二元人格:“上文武二活是景陽(yáng)崗上大蟲(chóng),此處武二是暮雪房中嫂嫂。武松與孫二娘相見(jiàn)后,武松叫無(wú)數(shù)嫂嫂,二娘叫無(wú)數(shù)伯伯,前后兩篇,殺一嫂嫂,遇一嫂嫂。先做叔叔,后做伯伯,武松以此寫(xiě)活,血肉可見(jiàn)。”
這種深入人格深處的體察不僅表現(xiàn)在對(duì)武松分析上,也體現(xiàn)在對(duì)其他人物的分析中,有時(shí)還散落在文章的細(xì)節(jié)和角落中。如《扈三娘的心死無(wú)言》一文對(duì)扈三娘丈夫王英的分析,就是以冷幽默方式挖掘出男性內(nèi)心深處只露出“冰山一角”的潛意識(shí):王英自從娶了扈三娘,再也沒(méi)有這方面的不良記錄,不過(guò)江山易移,本性難改,王英成了正人君子,其中的無(wú)奈與苦楚大概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而對(duì)扈三娘的分析則更見(jiàn)作者深入人物內(nèi)心的功力,作者分析扈三娘的“沉默”:在看清了自己的真實(shí)處境后,回天無(wú)力自救無(wú)法的扈三娘只能茍且了此殘生,直至甘愿戰(zhàn)死沙場(chǎng)。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書(shū)中的一丈青扈三娘自從上梁山正式落草后沒(méi)說(shuō)過(guò)一句話,言為心聲,心既已死,夫復(fù)何言!茅盾評(píng)價(jià)二十世紀(jì)初丁玲的女權(quán)主義小說(shuō)《莎菲女士的日記》中的莎菲是“心靈上負(fù)著時(shí)代苦悶的創(chuàng)傷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絕叫者”,而蔡康隨筆中的這些女性大多沒(méi)有直接的絕叫,她們或者沉默,或者被男性化或奴化,或者郁郁凄慘而死,最多也不過(guò)如決絕的杜十娘那樣怒沉百寶箱。
魯迅在《且介亭雜文二集·幾乎無(wú)事的悲劇》曾說(shuō)“《紅樓夢(mèng)》中的小悲劇,是社會(huì)上常有的事”,認(rèn)為這種平常的生活故事,足以表現(xiàn)真正的社會(huì)悲劇。比如果戈里的“幾乎無(wú)事的悲劇”,這些極平常的或者簡(jiǎn)直近于沒(méi)有事情的悲劇,正如無(wú)聲的語(yǔ)言一樣,非由詩(shī)人畫(huà)出它的形象來(lái),是很不容易覺(jué)察的。然而人們滅亡于英雄的特別的悲劇者少,消磨于極平常的,或者簡(jiǎn)直近于沒(méi)有事情的悲劇者卻多。
我想,蔡康之所以費(fèi)心寫(xiě)下這一系列沉重而有意味的文章,用意正在于此吧。
① 王國(guó)維:《人間詞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頁(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