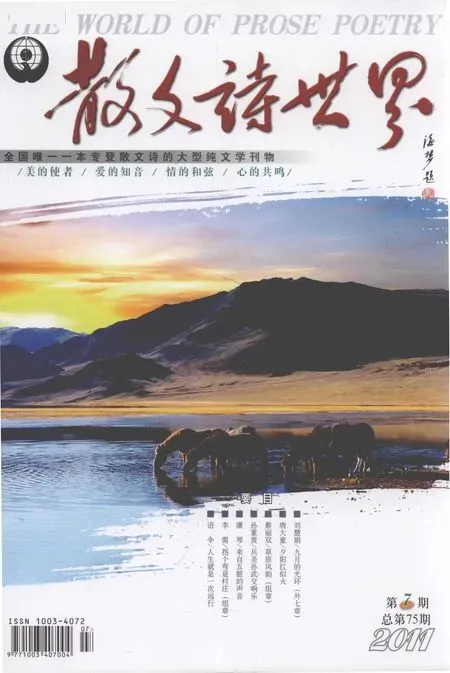峽 谷(外四章)
云南昭通彝良縣角奎中學 李發強
比巖石更低矮的是河流;比河流更低矮的,是天空;比天空更低矮的,是劃傷我眼睛的飛鳥。
這刀子劈開的峽谷,孑然而立,兩片濕冷的嘴唇練習親吻,宛如兩棵樹的愛情,它們懷抱永生永世的相思。
大風吹不走巖石。沉默的巖石拒絕大風,拒絕月光之神的撫摸,拒絕與天空說話,卻無法拒絕一點一滴的紅土的血。那些血,飛揚跋扈地穿過堅硬的虎豹之軀,一瀉千里。我看見騎馬的人順水而下,逃離炊煙,叩響天堂或地獄之門。
然而有誰的牙齒比柔軟的風更為堅硬?峽谷坐落在時間之上,冷峻如鐵。風咬碎肉,咬碎骨,咬碎巖石的魂,讓長于河岸的垂柳輕歌曼舞,以峽谷的名義向水中的鳥影低頭。
不安分的河流,刨出地底的水彩和黃金,刨出神,引領一條魚的命運。而所有的魚蝦都死于愛情,它們的私處,滿是工業文明的傷口。
我躺在石頭之上,讓一顆石頭見證我的老去。這些死去的骨頭,沉默著,一萬年之后才開口說話。
小米溪
綠色的岸延伸到小米溪的上游,直至一條河流的出身,你會發現,那是乳汁豐滿的農田,以及風骨矍鑠的高山,樹葉在唱婉轉的歌。
順流而下的角奎鎮,小米溪飛揚跋扈,一條水堅硬的程度是無法揣摩的。八月無情,日日暴雨,夏天隨水而逝。風,無法抵達彼岸。
水沉默地咆哮。在暗處,石頭的一生,便是這樣悄然被磨碎的。隱藏的呻吟,在夢里,在白天黑夜,在美麗的浪花之下。
魚蝦沉于水底。網魚的孩子,成為魚的誘餌。
建筑工地
蒼蠅凍死了,蛇隱于土,出租房門前的小米溪如我般消瘦。
我站在窗口,建筑工地上正熱火朝天,如同一場革命,大勢所趨。
那些燕子窩是被鐵錘敲碎的,但我找不到真正的元兇:鐵錘、掄鐵錘的民工?包工頭、還是建筑老板?線索在這里中斷了,再繼續,會牽涉整個冬天。
這是一樁無頭公案。
挖掘機阻住我的路,來回迂行,我只能在河水之上行走。大地不是用來行走,而是用來挖掘的,這個強盜的真理被人反復運用卻不需要經過論證。
打樁機徹夜不停,它們叫囂著,仿佛一場軍演,一再試探大地的底線:那種堅硬得能咬碎一切的巖層。
我翻過圍欄,站在一口深井邊,看見那個戴安全帽的人緩緩下降,進入白天的夜晚:他躲起來了。黑暗中,最后一只鳥繞過工地的天空。五分鐘后,井邊的人開始攪動滾筒,一桶泥土徐徐上升:大地的心臟被掏出來,曝曬在冷雨之中。
我看見一只鳥突然折翅,摔死在無所依托的天空。
春 天
門前的河逐漸緩慢,悄然止于流動。
出租房背后的花椒樹林,停在了去年秋天。半年里,我愛的人沒來過一次電話。
畢竟是春天,菜花總是要開的,櫻花、桃花、梨花總是要開的。在某個鮮為人知的午夜,它們孤獨地美麗。
燕子又興致勃勃地飛回滇東北的角奎鎮,適逢一場干旱。在迷茫的塵埃里,它們面如土色。
種莊稼的人拍散焦土,胡亂埋下種子,如同舉辦一場草率的婚禮。站在地里的稻草人無所事事,它們揮舞著拳頭,終于與低飛的鳥們握手言和。
而那個賣萵苣的老人被白花花的陽光晃了眼,背對著一輛飛揚跋扈的運水車,她一個跟頭就栽在躍進橋上,額上滲出干燥的血。我去扶她的時候,她像一株蔫巴的萵苣,無法站立。
十 月
居然如此冷靜:十月,風冷靜地吹,拂過一株梧桐的額頭,葉片落下。
樹葉冷靜地燃燒,飄飛的火焰冷靜如水。
一場冷雨,淋濕了水。
我端起水杯,透明的冷深入十月,深入唇。愛情躲在生活里。冷靜的生活,無法深入。
冷靜的還有孩子。書包在雨夜行走,忘記了哭。我躲在黑暗的路燈下,把未來接回家。
一條路擋住我。一條路正在背叛車輛和行人,不容拒絕。
只有生活無法背叛,也無法拒絕。
白晝縮短,夜長夢多,物質與精神一直在打斗。生與死的話題躲在哲人的紙張里,一再被翻開:在世界面前,我輕如塵埃;而沒有我,世界將灰飛煙滅。
午夜之后我終于入睡,如同有預謀的死亡。
在夢里,我手舞足蹈:看吧,是我拋棄了這個世界!
而黑夜啞然,它一直那么冷靜地凝視著我,等我醒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