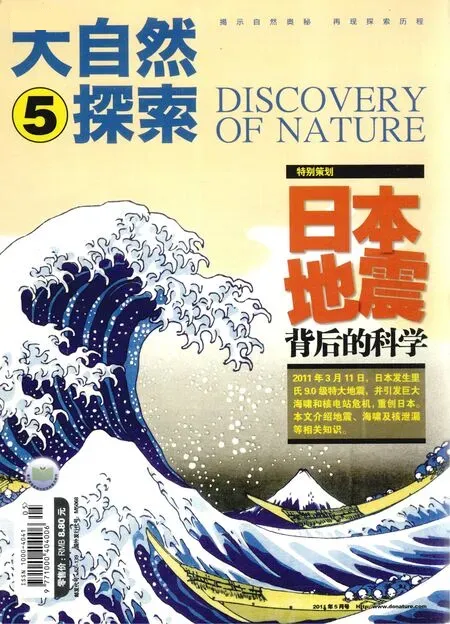探索地球生命起源奧秘
編譯 方陵生
探索地球生命起源奧秘
編譯 方陵生

2011年3月,美國宇航局科學家理查德·胡佛在《宇宙學》雜志上發表論文稱,他在隕石里發現了來自太空的外星微生物化石。他同時還堅稱,這些微小的生命形式不是地球的 污染物,而是在彗星、月球和其他星球上生活的活體有機生物的遺留物。胡佛的論文引起了人們的極大關注。如果這項研究成果得到證實,可能意味著宇宙到處都存在生命跡象,地球上的生命或許來自太陽系的其他地方,隨著彗星或小行星一類的太空巖石來到地球。不過,很快就有科學家對此提出了質疑。
地球上的生命是如何起源的?這是地球上所有奧秘中最大的奧秘。由于缺乏地球早期生命體化石以及相關的地質學證據,我們至今仍不清楚地球上最初的生命是怎樣出現的,出現在哪里,其形態是什么樣的……地球生命起源的諸多奧秘依然撲朔迷離。
最初的地球生命是怎樣出現的?
這是地球生命起源奧秘中最有趣也最困難的一個謎題。在人類的各種文化中都有解釋生命起源的故事。

斯坦利·米勒和他設計的實驗裝置
中世紀的歐洲學者認為,一些小動物如昆蟲、兩棲動物和老鼠,是“自發產生”的,即非生命成分自然地“自我組裝”,比如從舊衣服堆或垃圾堆中產生生命。1668年,意大利醫生弗朗西斯科·雷迪對這種說法提出了質疑,他發現蛆蟲是從蒼蠅產下的卵中孵化出來,而不是從腐爛物質中自然形成的。到19世紀60年代,法國微生物學家巴斯德進行了一系列實驗,徹底否定了生命“自發產生”理論。
1871年,達爾文在一封信中寫道:“最初的生命體有可能是在一個溫暖的小池塘中出現的,這個池塘中可能同時具有各種化學物質(如氨水、含磷的鹽等)和閃電、光亮、熱量一類的東西。經過一系列復雜的化學反應后,蛋白質合成物出現了,它們開始經歷若干更復雜的變化。”此后,無數科學家前仆后繼,逐漸完善著達爾文想象中的那個孕育地球生命的“溫暖的小池塘”。其中,最有影響力的是人是俄羅斯科學家奧巴林和英國科學家霍爾丹。
奧巴林和霍爾丹推斷,生命產生之初的地球早期大氣中沒有氧(或有很少的氧),但卻有可以通過化學反應產生氫原子的其他高濃度氣體成分,而氫原子是合成創造生命的化合物所必不可少的。據此,科學家認為,促進原子和分子重新排列進入有機生命形式的能量來自于陽光、閃電或地熱。
為了檢驗上述理論,1953年,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物理學研究生斯坦利·米勒設計了一個實驗:在密封玻璃容器中充滿地球早期大氣中存在的各種氣體,容器底部是沸騰的水,水的上方通過儀器產生電火花穿越氣體混合物。經過一星期的反應,米勒發現,在氣體中和水中都形成了氨基酸。氨基酸是構成地球生命的基本成分之一,構成生命的蛋白質和酶都是以氨基酸為基礎的。
不過,后來的科學家發現,在生命產生之前,地球早期大氣可能根本不像奧巴林、霍爾丹和米勒認為的那樣已經為生命的誕生做好了準備。他們推斷,火山活動給早期大氣中增添了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以及少量的氧。近年來,科學家在實驗室條件下模擬數十億年前的地球早期大氣,已產生了有機體中發現的所有20種氨基酸。
但是,在沒有生命存在的情況下,這些氨基酸是如何連接在一起形成更復雜的化合物,進而成為地球早期生命體的呢?實際上,問題并不在于氨基酸,而在于蛋白質,所有活細胞都是由蛋白質組成的。氨基酸以化學方式利用特定的酶連在一起形成某種蛋白質。沒有酶,氨基酸就無法以化學家稱之為聚合作用的方式連接起來。那么在早期地球上,沒有酶的幫助,氨基酸是如何連接在一起的呢?一種可能性就是,氨基酸與熾熱的砂子、黏土或其他礦物結合在一起。實驗室實驗表明,氨基酸和其他高分子聚合物的稀釋液滴落到溫暖的沙地、黏土或其他礦物質上,以這種方式連接起來形成較大的被稱為類蛋白的分子。可以想象,在達爾文設想的“溫暖的小池塘”里,自發形成的“氨基酸湯液”飛濺在熾熱火山巖石上的情景,黏土和黃鐵礦也為生命最基本成分形成更大的分子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臺”。
氨基酸和其他有機化合物的形成被推定為生命起源的一個必要步驟,這一點是確定無疑的,至少是所有生命體都依賴于DNA 和RNA 進行復制這一發展過程中的一環(請參閱“相關鏈接”)。科學家由此推測,一旦第一個可以進行自我復制的分子出現,進化就主宰了之后的生命發展之路,最適應于當地環境條件的特定分子能夠最有效地進行自我復制,直至原始細胞出現。一旦細胞產生,通過自然選擇和生存競爭,地球上多種多樣的生命形式便紛紛開始出現。
蛋白質是生命的物質基礎,沒有蛋白質就沒有生命。機體中的每一個細胞和所有重要組成部分都有蛋白質參與。蛋白質的種類很多,性質、功能各異,但都是由20種氨基酸按不同比例組合而成的。氨基酸賦予蛋白質特定的分子結構形態,使它的分子具有生化活性。
基因是編碼蛋白質或RNA等具有特定功能產物的遺傳信息的基本單位,是染色體的一段DNA序列。也就是說,生物的遺傳信息都儲存在細胞核內的DNA中。細胞分裂時,為了確保每一代的細胞具備相同的遺傳信息,DNA必須通過自我復制使子代細胞帶有同樣數量的DNA,這一過程被稱為“復制”。細胞在執行某種生物功能時,需要特定的蛋白質來完成,此時DNA將信息傳遞給RNA(這一過程被稱為“轉錄”),然后RNA按照特定的信息通過氨基酸的不同組合來組成特定的蛋白質(這一過程被稱為“翻譯”)。這樣,DNA中的不同遺傳信息就可以根據需要翻譯成不同的蛋白質,而不同的蛋白質則在機體內執行不同的生物功能。這即“生物中心法則” ——細胞內的信息按照預定順序流動:DNA將遺傳信息轉錄給RNA,RNA嚴格按照DNA的遺傳信息,通過氨基酸的不同組合合成蛋白質。
DNA的中文名稱是脫氧核糖核酸,英文名稱是Deoxyribonucleic acid。RNA的中文名稱是核糖核酸,英文名稱是Ribonucleic acid。DNA是由一個一個核苷酸連結成雙螺旋分子結構的大分子。RNA也是由許多核苷酸連成的長長的大分子,但沒有DNA長,分子量也小得多。蛋白質是由氨基酸單分子連起來的大分子。

地球生命起源于海底熱液口?
有關地球生命起源最引人注目的話題之一是:簡單的有機化合物是在什么地方演變為更復雜的聚合物,進而成為地球早期生命體的?
達爾文設想,地球生命是在“溫暖的小池塘”中產生的,但也有科學家認為,剛誕生不久的地球是一個不適合生命生存的荒涼地方,大氣中沒有氧氣,也沒有如今能夠阻擋大量有害紫外線輻射的臭氧層,所以他們認為,最有可能產生生命的環境是深海熱液口。
1976年,科學家乘坐“阿爾文號”潛艇潛入深海底,在那里發現了一些裂縫,被熔巖加熱到幾百攝氏度高溫、富含礦物質的海水源源不斷地從裂縫中噴涌而出。這就是被稱之為“海底熱液口”的地方。科學家還發現,在海底熱液口附近,存在著一個奇特的生態系統,在那里聚集了大量海洋生物,包括巨大的管蠕蟲、盲蝦和噬硫細菌。
1996年,礦物學家鮑勃·哈森開始了一項實驗,旨在證明:海底熱液口附近是生命誕生的理想之地。哈森認為,海底熱液口的高溫高壓環境,豐富的礦物質資源,以及裂縫中源源不斷噴涌上來并立即與冰冷的海水交融在一起的熱水,這種種復雜的環境條件表明,這里很可能是地球生命起源的地方。為了測試這一理論,哈森和他的同事們使用了一種被叫做“壓力彈”的設備。“壓力彈”在技術術語上被叫做“內部加熱氣體介質壓力容器”,看上去就像一口超級廚房高壓鍋,可產生超過1800℃的高溫和相當于海平面氣壓10000倍的高壓。
做實驗時,哈森將水、一種被叫做丙酮酸鹽的有機化學物質,以及一種能產生二氧化碳的粉末裝進一個由金子做成的小膠囊內,然后將小膠囊放進設定在480℃、2000個大氣壓的“壓力彈”中。兩小時后,他取出膠囊,發現里面的東西已經變成了數以萬計的不同的化合物。之后,哈森和同事們又用氮、氨以及其他早期存在于地球上的分子進行實驗,最終創造出了各種各樣的有機分子,包括各種氨基酸和糖類,這些都是構成生命體的基本物質。

哈森的“壓力彈”實驗標志著一個重要的轉折點。44年前,米勒在裝滿“地球早期大氣”的玻璃試瓶里,用電火花模擬閃電,成功地創造出了含有氨基酸的“生命原湯”。而現在,哈森的“壓力彈”實驗則表明,不僅僅是雷電,生命的基本分子還可能在各種場所形成,包括海底熱液口附近,火山口中,甚至在隕石上。
在科學家看來,在地球上形成生命的基本元素如碳、氫、氮等并不難,難的是:這些基本元素是如何組合在一起的?還有,氨基酸以多種形式出現,但其中只有一些被生物體用來構成蛋白質,那它們又是如何發現和找到彼此的呢?
哈森認為,各種分子漂浮在浩瀚海水——“生命原湯”之中,但那決不是什么濃厚醇香的燉牛肉湯,它非常稀薄,只是在一片汪洋大海中,這里或那里偶爾飄浮著幾個分子而已。可以說,在茫茫大海中,分子與分子相遇,產生化學反應,并最終形成較大結構的機會可謂無限之小。哈森推測,海底的巖石,即在海底熱液口周圍堆積起來的礦床,很可能是幫助孤單的氨基酸互相尋找到彼此的最好媒介——礦物巖石擁有紋理,有的光滑、有光澤,有的粗糙、凹凸不平,表面附著各種分子;氫原子若即若離地徘徊在礦物巖石的附近,與其上的各種分子發生反應;某種氨基酸被礦物分子所吸引,形成一個鍵,足夠多的鍵形成一種蛋白質……目前,哈森及其同事正在實驗室里對不同的礦物質和分子加以組合,一遍又一遍地做實驗,以重復地球早期海洋里曾經發生過的那些事兒。
哈森還從另一個角度探索生命起源的奧秘,這就是:生命是如何促進了礦物的演化?我們知道,在太陽系形成之前,宇宙塵埃粒子中大約只有十幾種礦物質,包括金剛石和石墨等;當太陽形成之時,又形成了大約50種礦物質。在地球上,火山爆發噴發物形成玄武巖,板塊構造運動促成了銅、鉛和鋅等礦床的形成。哈森認為,在恒星爆炸、行星形成和地球板塊運動的壯麗史詩中,這些礦物質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接下來,生命活動起到了關鍵作用。光合作用將氧氣引入大氣中,進而進入地殼中,促成了一些新種類的礦物質,如綠松石、孔雀石和藍銅礦等的形成。苔蘚和藻類爬上陸地,使巖石碎裂,形成黏土,更大的植物得以生長,土壤也向縱深發展,如此等等。如今地球上的礦物質大約有4400種,其中超過2/3的產生是因為生命的存在改變了這個星球,其中一些完全是由活的生物體死亡后形成的。
哈森認為,海底熱液口附近復雜的環境正是生命誕生的理想之地——噴涌而出的熱水與巖石附近冰冷的海水產生相互作用,礦床表面提供堅實的表面,讓新形成的氨基酸擁有一個能夠聚集在一起的落腳之處。他說,“長期以來,有機化學家一直利用試管來進行化學反應實驗,而生命起源所利用的則是巖石、水和大氣。一旦生命有了立足點,多樣化的環境因素就成為演變發展的推動力量。”礦物質演變并增多,生命出現并向多樣化發展,于是,三葉蟲、鯨魚、靈長類動物相繼登上了地球歷史舞臺。

一些科學家認為,剛誕生不久的地球是一個不適合生命生存的荒涼地方,大氣中沒有氧氣,也沒有如今能夠阻擋大量有害紫外線輻射的臭氧層,所以最有可能產生生命的環境是深海熱液口。
地球生命起源于外太空?


2011年3月,美國宇航局科學家理查德·胡佛發表文章稱,在隕石碎片中發現了外星微生物化石,但很快美國宇航局的頂級科學家們對此進行了駁斥。上圖是用電子顯微鏡拍成的Titanospirillum velox巨型細菌的真實畫面,與胡佛所發現的“外星微生物”化石相似。下圖是將研究樣本隕石放大1000倍后拍攝的圖片,可見許多絲狀體物質。
有科學家認為,地球上的生命或許來自太陽系的其他地方,是隨著彗星或小行星一類的太空巖石來到地球的。
目前科學家普遍認為,地球生命根源于某些特定無機物的組合。在混沌之初,“生命原湯”中的各種物質經歷了一系列化學反應,最終形成了氨基酸等結構復雜的有機化合物。自19世紀,有科學家發現,這些富含碳元素的有機化合物同一些隕石的組成成分十分類似,于是提出了地球生命可能來自外太空的觀點。
小行星帶被認為是地球生命起源較為理想的發生空間。小行星帶介于火星和木星之間,遠離形成過程中的行星的高溫高壓環境。一些科學家推測,小行星帶中的小行星不斷發生激烈碰撞,產生的隕石攜帶著一些物質運行在太陽系中,其中一些最終墜落到了地球上,正是這些“太空來客”提供了地球生命形成所不可缺少的各種有機成分。
隕石分為球粒隕石和非球粒隕石兩類。科學家認為,球粒隕石對生命起源有著較為重要的意義,因為其中含有氨基酸和其他化合物,它們撞擊地球產生熱和沖擊波,可以在地球早期大氣中激起合成有機化合物的化學反應。1969年,一顆隕石隕落在維多利亞的默奇森地區,科學家在這顆隕石中發現了多種氨基酸。默奇森隕石屬于碳質球粒隕石,極可能是來自彗星的殘余物質。這是科學家首次在隕石中發現氨基酸。科學家還在默奇森隕石中發現了與微生物極為相似的微體化石,被一些微生物學家認為是來自太空的微觀生命。
科學家在其他的碳質球粒隕石中也找到了各種形態的微生物化石,長條形的,圓形的等,與地球上的微生物非常相似。這些隕石樣本被一些科學家認為提供了地球生命起源于外太空的寶貴證據。
2010年,美國科學家在一塊叫做“Ureilite”的隕石中發現了19種氨基酸。令科學家驚訝的是,他們在Ureilite隕石中既發現了“左手性”的氨基酸,也發現了“右手性”的氨基酸。氨基酸中的原子排列呈立體組合,有L型(左旋)和D型(右旋)兩種,呈相互鏡像關系,如我們的左手和右手對稱一樣,因此也被分別稱作 “左手性”和“右手性”。研究發現,除了少數動物的特定器官內含有少量的“右手性”氨基酸之外,構成地球生命體的氨基酸幾乎都是“左手性”的。有科學家據此認為,這些氨基酸肯定來自外太空,而不是在地球上被“污染”的。

一些科學家認為:地球上的生命或許來自太陽系的其他地方,是隨著彗星或小行星一類的太空巖石來到地球的。
2011年2月,一個美國科學家小組宣布,他們從1995年在南極洲地區發現的一塊編號為“Grave Nunataks 95229”的隕石中提取了4克巖石粉末樣本進行化學分析,結果發現樣本中含有豐富的氮元素,而構成生命基本要素的DNA和蛋白質中都含有氮元素。一些科學家認為,這為地球生命起源于外太空的說法提供了進一步的有力證據。
2011年3月,美國宇航局科學家理查德·胡佛宣稱,他在隕石中發現了地外生命的痕跡。這位天體生物學家曾花費10年時間對隕落在世界各處荒涼角落的隕石進行研究分析。胡佛稱,他將發現自南極、西伯利亞和阿拉斯加的碳質球粒隕石進行切片,然后用掃描隧道顯微鏡進行觀察,結果發現了“大型的復雜絲狀體”,這種類似地球上能產生氧氣的藍藻細菌的外星微生物化石或可證明宇宙中外星生物的存在。如果這項研究成果得到確認,它將為“胚種論”提供有力支持。該理論認為,細菌可以在休眠狀態下隱藏于隕石中進行超長距離的星際旅行,而當它們最終落到一個新的行星上后,在條件適宜的情況下,便有機會復蘇并實現“生命種子”的星際傳播。
胡佛的這一研究成果引起了極大的關注,但同時也受到了很多科學家的質疑。美國航天局的頂級科學家很快發表聲明說,沒有科學證據能夠支持他們的同事所宣布的這一驚人發現。他們認為對這個說法最簡單的解釋是:這些隕石碎片上確實存在微生物,但它們是地球上的微生物。也就是說,這些隕石在降落后被地球的微生物“污染”了。
事實上,之前也有過相似的消息,但最終都被證實是錯誤的。如在上世紀60年代就有人稱在一塊隕石中發現了一個“胚種艙”,但后來證明是被人故意粘上去的。
還有另外的地球生命起源形式嗎?
科學家普遍認同,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起源于一個共同的祖先。會不會還有不同的地球生命起源形式呢?
2010年,英國皇家學會在倫敦召開了主題為“探測地外生命及其對科學和社會的影響”的研討會。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搜索來自外星人的信號”、“搜尋地球另一個生命起源”和“探討尋找外星生命的社會意義”。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的保羅·戴維斯教授在會上提出了“在地球上搜索‘影子生物圈’” 的想法
何謂“影子生物圈”?即指存在于地球或地球之外,與已知生命形式毫不相關的獨立的生命源的后代。到哪里去尋找“影子生物圈”呢?科學家指出,并非乘坐星際飛船到太空中許多光年之外的地方去尋找,而是在我們的地球上尋找。
我們所熟悉的各種各樣的多細胞生物都起源于一個共同的祖先,沒有人懷疑這一點,其根據主要源自于生物化學和分子生物學,比如櫟樹、鯨魚、蘑菇和細菌看起來是完全不同的物種,但從生物化學和分子生物學的角度來看,它們的內部機制卻是相同的,都用DNA和RNA存儲信息,用ATP分子(ATP即三磷酸腺苷,是各種活細胞內普遍存在的一種高能磷酸化合物)儲存和釋放能量,等等。生物學家還發現,許多截然不同的物種,它們的基因卻極為相似,比如人類與小鼠相同的基因達63%,人類與酵母相同的基因達38%。
無論是動物園里的動物,庭院里的植物,還是天空中的飛鳥和海里的魚,它們都是同一種生命形式——多細胞生物。不過,多細胞生物只是地球生命的一部分,地球生命的絕大部分是微生物。
在顯微鏡下,我們可以發現構成微生物的生物化學結構:DNA,蛋白質,核糖體,和你我身體的基本構成是一樣的。但是,地球上充滿了這些微小的生物體,僅1立方厘米的土壤內就可能含有種類多達數百萬種、數量多達數十億的微生物,其中絕大多數都還沒有被歸類,更不用說進行研究了,在這中間會不會有我們所不知道的生命形式呢?
問題還在于,進化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偶然性,不同起源的生命體很可能有著完全不同的生物化學結構,“影子生物圈”有可能被淹沒在常規形式的生命中。
那么,我們應該如何去尋找我們所不知道的生命形式?一個可行的方法是:到傳統生命無法生存的極端環境中去探索,比如沙漠、冰原、高空大氣層和火山口。
在過去30年里,生物學家不斷驚訝地發現,在一些以前被認為足以致命的環境中,一些生命卻欣欣向榮,繁衍不息。20世紀60年代后期,在美國黃石國家公園的溫泉中,發現了可承受90℃高溫的微生物(被稱為嗜熱菌)。更為驚奇的是,1976年,在深海熱液口附近,首次發現了生活在高達350℃熱液中的微生物。科學家還相繼發現了能夠承受極端寒冷、耐腐蝕以及耐輻射等的微生物。這些發現表明,生命的生存空間比我們以往所認為的要寬廣得多。
不過,研究證明,迄今發現的這些極端微生物仍然是地球上的常規生命形式,和你我一樣,都源自于同樣的生命之樹。假如存在一個“影子生物圈”,其生存環境甚至超越了迄今已發現的最頑強生命的生存極限,情況又會怎樣呢?一個很好的例子是溫度。我們知道,溫度超過120℃,DNA和蛋白質就會被破壞和瓦解,一系列分子修復和保護機制也會遭到破壞。但是,超級嗜熱菌的耐熱極限達到約130℃。另一個例子是深度。20世紀80年代,天體物理學家托馬斯·戈爾德在監管一個實驗性石油鉆井工程時,在鉆孔幾千米深處發現了生命。之后幾年里,其他研究人員也紛紛在巖石孔隙中尋找到生活在地下深處的微生物,并在1000米深處的海底巖石中發現:每立方厘米中含有數以百萬計的微生物!科學家推測,地球上有著一些與世隔絕或幾乎與世隔絕的地下生態系統,每一個生態系統都自成一體,自我維持,并基本上隔絕于我們所熟悉的地球生物圈。

尋找我們所不知道的生命形式的一個可行的方法是:到傳統生命無法生存的極端環境中去探索,例如沙漠、冰原、高空大氣層和火山口。
目前至少已有三個這樣的生態系統被發現——深埋于地下,幾乎完全與地面生物圈隔絕。生活在其中的微生物群落以氫為能量——地下水與熾熱的巖石接觸產生氫,或者通過巖石的輻射作用產生氫。這些生物體從氫和溶解的二氧化碳獲得能量,并釋放甲烷為其排泄物。這些生物體中有許多是嗜熱菌或超級嗜熱菌,越接近地殼深處,它們能耐受的溫度越高。
遺憾的是,這三個與世隔絕的地下生態系統仍被認為屬于常規地球生態系統。不過,“奇異生命”形式有可能生存在其他一些地方,包括高層大氣、寒冷干燥的高原和高山頂(高山頂上高通量的紫外線輻射是普通生命形式所無法承受的)、溫度低于-40℃的冰沉積層,被有毒金屬嚴重污染、令普通生命形式無法生存的湖泊,等等。在未來的鉆探工程中,無論是陸地上還是海上,完全都有可能發現生存著“奇異生命”的“影子生態圈”。
尋找“奇異生命”形式的另一個問題是,它們可能與常規生命生活在同一個生物圈中,使甄別的難度很大,如像科幻小說中所描寫的那樣,生活在我們中間的外星人,與地球人看上去沒有什么區別。而且一個小人國版本的“外星人滲透”事件有可能真的存在于我們的地球上:看上去就像普通細菌的“奇異微生物”,與普通細菌居住在同一個環境中,人們或者已經看到它們了,但沒有認出它們來。
我們不知道“影子生命”到底是什么樣的,這是一個極大的挑戰。因此,尋找“影子生命”的另一個方法就是:設計出探測其他生物化學結構的手段——兩種微生物也許看上去完全相同,但它們在生物化學結構上未必完全相同。目前只有美國宇航局的微生物學家進行了這類實驗——尋找“鏡像生命”。普通生命體幾乎無一例外都采用右旋糖和左旋氨基酸,并避免形成它們的鏡像等價物,可如果“影子生命”是以相反的偏好發展呢?以“手性”為線索尋找“影子生命”,不失為一種明顯而簡單的技術。
2004年,美國生物學家克雷格·文特爾參加了人類基因組測序,當他宣布他從提取自北大西洋相當貧瘠的馬尾藻海中的海水樣本中分離出了120萬個新的基因、1800種之前尚未確認的微生物時,整個科學界都為之震動了。文特爾說:“我們正在尋找火星上的生命,但我們其實連地球上究竟還有些什么生命都不知道。”
幾個正在進行的海洋采樣研究項目為發現海洋中的“影子生命”提供了絕好的機會。科學家在密切關注二氧化碳積累對海洋生物多樣性的影響的同時,還將研究來自世界各地的深海微生物。如果我們能發現另一種生命起源的形式,將成為生物學史上最轟動的事件,對科學特別是天體生物學的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因為我們可以由此肯定:茫茫宇宙中充滿了多種形式的生命。
關于地球生命起源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解答,同一問題在科學界也還存在不同的觀點。生命起源奧秘似乎很難破譯,但科學家相信,只要堅持不懈,地球生命起源之謎最終可以被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