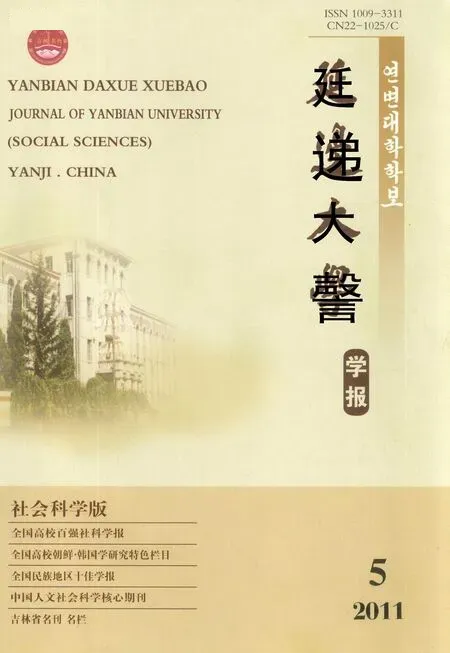地緣戰(zhàn)略地位的可變性及其影響
王 志 偉
(延邊大學 社會科學基礎(chǔ)部,吉林 延吉133002)
地緣戰(zhàn)略地位的可變性及其影響
王 志 偉
(延邊大學 社會科學基礎(chǔ)部,吉林 延吉133002)
地緣政治理論由于所服務(wù)的國家和地緣環(huán)境不同,強調(diào)的地緣戰(zhàn)略重點區(qū)域也不同。對地緣政治理論中不時閃現(xiàn)的“環(huán)境決定論”和“對抗性”思維的否定過程中,以及從地緣戰(zhàn)略地位理論自身的邏輯結(jié)構(gòu)來看,都內(nèi)在地包含著地緣戰(zhàn)略地位可變性的理論思路。對處于不同地緣戰(zhàn)略地位的國家來說,重要的是抓住不同時期賦予的機遇,推動國家的發(fā)展和促進內(nèi)部穩(wěn)定。
地緣政治理論;地緣戰(zhàn)略地位;可變性;影響
當今世界依然存在著很多地區(qū)熱點問題,如阿富汗問題、伊朗核問題、朝鮮半島問題、利比亞問題,等等,每一個熱點問題的背后都或多或少顯現(xiàn)了某一國家或地區(qū)地緣戰(zhàn)略地位的身影。其中比較突出的是阿富汗和朝鮮半島,這兩個地區(qū)至少從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到現(xiàn)在,雖然經(jīng)歷了國際格局的變遷,但作為地緣政治爭奪熱點地區(qū)的“宿命”依然不變。那么,某一國家和地區(qū)能否改變其地緣戰(zhàn)略地位,本文試從地緣政治理論體系的內(nèi)在邏輯出發(fā),分析地緣戰(zhàn)略地位的可變性,并進一步探討地緣戰(zhàn)略地位的變遷對其自身安全與發(fā)展的影響。
一、經(jīng)典地緣政治理論流派中戰(zhàn)略重點的差異
地緣政治理論主要是通過地理空間現(xiàn)象和國際政治之間的關(guān)系,來分析相關(guān)國家的國際戰(zhàn)略。任何時代的地緣政治理論者,都是從各自國家在那個時代所處的地緣環(huán)境出發(fā),為國家利益的實現(xiàn)繪制戰(zhàn)略藍圖。因彼此服務(wù)的國家和所處的地緣環(huán)境不同,所強調(diào)的地緣戰(zhàn)略重點區(qū)域也必然有差別。通過分析幾種最具代表性的地緣政治理論,可以更清晰地把握這種差異。
美國著名的“海權(quán)論”者馬漢,從陸地和海洋劃分的基本地理觀念出發(fā),從時代和歷史發(fā)展的角度論述了海洋戰(zhàn)略的重要意義。馬漢認為,“海洋是人們借以通向四面八方的廣闊的公有地”,“盡管海上有各種常見的和不常見的危險,但是無論是旅行還是運輸,經(jīng)海路總比經(jīng)陸路方便、便宜”,[1]當美國離不開海洋貿(mào)易所帶來的利益的時候,“對海運產(chǎn)生的濃厚的興趣將會重新迫使它去恢復海軍”,[1]“并且說明了美國應把握機遇將自己變?yōu)橐粋€主要海權(quán)國家與殖民勢力的重要性”。[2]他通過對歐洲和美洲歷史發(fā)展過程的分析,認為擁有了強大的海軍,才能夠擁有強大的海權(quán),也才能夠?qū)崿F(xiàn)美國的經(jīng)濟、政治、軍事乃至戰(zhàn)略利益。馬漢的理論對于20世紀初美國海洋力量的發(fā)展和成長為霸權(quán)國家產(chǎn)生了直接影響。馬漢的“海權(quán)論”是在“闡發(fā)海權(quán)理論,為美國的海洋政策、海軍戰(zhàn)略作理論準備,為美國壟斷資本主義的經(jīng)濟與政治服務(wù)”。[1]
英國著名學者麥金德,從維護英國海權(quán)優(yōu)勢的角度提出了經(jīng)典的“陸權(quán)論”。“麥金德是第一位試圖在一種廣闊的背景下,把地理和歷史聯(lián)在一起來真實地探索世界觀念的地理學家”。[2]他認為“世界歷史基本上是陸上人和海上人之間的反復斗爭的過程”,[2]“哥倫布時代的基本特征是歐洲幾乎是在沒有抵抗的情況下進行擴張”,[3]但到20世紀初為止,歐洲世界的領(lǐng)土擴張已經(jīng)基本結(jié)束,作為一種地理特征世界已經(jīng)“閉合”了,那么“我們不得不再一次與封閉的政治制度打交道”,[3]全球范圍內(nèi)各大勢力之間的斗爭將成為時代的主題。麥金德認為當時世界上主要存在兩種勢力,即海權(quán)勢力和陸權(quán)勢力,“并指出全球?qū)怪械膬纱蠼巧谴笥⒌蹏蜕郴识韲薄#?]由于鐵路的發(fā)展帶來的機動性的變化,可能改變海權(quán)勢力的機動性優(yōu)勢,從而使“優(yōu)勢開始有利于陸上強國”。[2]這就是麥金德所憂慮的癥結(jié)和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他最擔心哪一個國家控制了“心臟地帶”,進而控制整個歐亞大陸,那么英國的霸權(quán)時代將由此而終結(jié)。因此,在《民主的理想和現(xiàn)實》中提出了他著名的論斷:“誰統(tǒng)治東歐,誰就能統(tǒng)治心臟地帶;誰統(tǒng)治心臟地帶,誰就能主宰世界島;誰統(tǒng)治世界島,誰就能主宰全世界”。[3]麥金德的理論是,“試圖將英國的世界權(quán)力置于其地理的和地緣政治的背景中去分析”,[4]其“言行是尋求保持不列顛對于心臟地帶周邊區(qū)域控制的海上霸權(quán)”,[5]為英國霸權(quán)的維護敲響了警鐘并指明了方向。其后,因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德國東進戰(zhàn)略的實施,尤其是成為二戰(zhàn)之后美蘇爭霸的冷戰(zhàn)“預言”,使其理論煥發(fā)出新的青春,直至今日仍被世人重視而經(jīng)久不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尚未結(jié)束的時候,“在美國國際事務(wù)的實際戰(zhàn)略背后,已有一種戰(zhàn)后將創(chuàng)造一個怎樣的世界的爭論”,[2]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斯皮克曼提出了他著名的“邊緣地帶”理論。斯皮克曼鑒于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中都遭遇了安全威脅,以致不得不用參戰(zhàn)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因此為了保證戰(zhàn)后美國的安全利益,必須更好地處理國際關(guān)系,其中“地理位置和實力是國際關(guān)系中必須考慮的事項”。[6]他從這一視角出發(fā),認為世界上存在三大力量中心,即“海上世界、陸地世界(以心臟地帶為中心)以及介于兩者之間的邊緣地帶”,其中邊緣地帶“擁有統(tǒng)治世界的最大潛力”。[4]由此斯皮克曼修正了麥金德的論斷,將之修改為:“誰支配著邊緣地區(qū),誰就控制歐亞大陸;誰支配著歐亞大陸,誰就掌握世界的命運”。[6]美國的安全不在于消滅所有實力中心,而在于防止單一實力中心控制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戰(zhàn)后美國“只有采取一種外交政策使歐亞大陸不可能潛伏一個有壓倒優(yōu)勢的統(tǒng)治勢力”,[6]其安全與獨立才能得到保證。正是為了防止歐亞大陸上出現(xiàn)一個占有壓倒優(yōu)勢的國家,戰(zhàn)后的美國陷入了與蘇聯(lián)爭奪世界霸權(quán)的長期冷戰(zhàn)之中。在冷戰(zhàn)時期美蘇之間展開了對第三世界的爭奪,這倒是“一個更接近斯皮克曼預言”[2]的世界。
近年來,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wù)助理布熱津斯基先生的地緣政治理論,對于相關(guān)領(lǐng)域的學者來說更是耳熟能詳。不論是在冷戰(zhàn)時期,還是在冷戰(zhàn)結(jié)束后,布熱津斯基都認為“誰控制了歐亞大陸,誰就支配了全球”。[7]在冷戰(zhàn)時期美蘇之間“爭奪歐亞大陸是一場全面的斗爭,在三條中心戰(zhàn)略戰(zhàn)線上進行:遠西戰(zhàn)線、遠東戰(zhàn)線和西南戰(zhàn)線”。[7]美蘇爭奪主要取決于在三條戰(zhàn)線上,對于幾個地緣政治要害國家的控制。“所謂要害國家是指既具有內(nèi)在重要意義而在某種意義上又是‘任人爭奪’的國家”,[7]控制了要害國家就能夠贏得美蘇爭霸的優(yōu)勢。冷戰(zhàn)結(jié)束之后,美國“成為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真正的全球性大國”,[8]要維護美國的全球霸權(quán)和戰(zhàn)略利益,“歐亞大陸是最重要的地緣政治目標”。[8]因此美國的“歐亞地緣戰(zhàn)略涉及有目的地管理在地緣戰(zhàn)略方面有活力的國家,并審慎地對待能引起地緣政治變化的國家”,[8]它把這種國家分別稱為地緣戰(zhàn)略棋手和地緣政治支軸國家。處理好同這些國家的關(guān)系,“對于美國長久和穩(wěn)固地保持其在全球的首要地位是至關(guān)重要的”。[8]其中,所謂冷戰(zhàn)時期的“地緣政治要害國家”和冷戰(zhàn)后歐亞大陸的“地緣戰(zhàn)略支軸國家”,從地區(qū)的角度來看具有相似性。可見布熱津斯基先生不同時期的地緣政治理論和地緣戰(zhàn)略,都是為了更好地影響、控制和支配歐亞大陸的事務(wù),以實現(xiàn)和維護美國的全球霸權(quán)。
上述幾種地緣政治理論是從過去到現(xiàn)在,為實現(xiàn)霸權(quán)國家戰(zhàn)略目的服務(wù)的典型代表,都是從一定的時代背景出發(fā),為霸權(quán)國家和潛在的霸權(quán)國家爭得權(quán)力和利益服務(wù)的理論體系。這些理論根據(jù)國家的實力和地緣政治環(huán)境,形成自己眼中關(guān)于世界的整體觀念,在世界觀念的指引下構(gòu)建出一種適合國家實現(xiàn)和維護霸權(quán)的理論體系,并尋找出一條可以解決問題的路徑和措施。正因為每種理論所服務(wù)的國家不同、國家所處的地緣環(huán)境不同,因此其所強調(diào)的地緣戰(zhàn)略重點區(qū)域也不同。馬漢強調(diào)海洋權(quán)力的擴張;麥金德則不僅強調(diào)擴張海權(quán),更強調(diào)要防止陸權(quán)勢力控制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斯皮克曼強調(diào)控制大陸與海洋之間的“邊緣地帶”;布熱津斯基則不僅強調(diào)要處理好與歐亞大陸現(xiàn)實或潛在的大國的關(guān)系,更要控制好某些關(guān)鍵的邊緣區(qū)域。由此可見,在不同國家謀求世界霸權(quán)的戰(zhàn)略中,某一區(qū)域在地緣戰(zhàn)略地位上的重要性是有差別的,甚至在同一國家謀求霸權(quán)的不同時期,某一區(qū)域在地緣戰(zhàn)略上的重要性也是不同的。在布熱津斯基的理論中,其強調(diào)的戰(zhàn)略重點國家在冷戰(zhàn)時期和冷戰(zhàn)結(jié)束之后就有很大的變化。這表明,至少隨著不同時期霸權(quán)國家及其地緣環(huán)境的歷史性更替和變遷,地緣戰(zhàn)略重點區(qū)域也必然發(fā)生變化。
二、地緣戰(zhàn)略地位可變性的邏輯線索
縱觀上述地緣政治理論的發(fā)展脈絡(luò),不僅在不同的理論體系中強調(diào)的戰(zhàn)略重點區(qū)域不同,而且其理論中至少存在兩大突出特點,讓地緣政治理論或多或少帶有一點偏執(zhí)和傷痕。在克服其存在的理論傷痕的邏輯中,內(nèi)在地包含著地緣戰(zhàn)略地位可變性的思路。
其一,“地緣政治思想的一個最主要的特征是其環(huán)境決定論”。[4]在這方面存在著很多規(guī)律性的表述,如“必然性”、“決定性”、“命運”甚至“宿命論”等觀點。麥金德說:“任何地方的政治問題,都將以對自然特征考察的結(jié)果而定”,[3]就是過分夸大了地理因素的作用。這種決定論認為地緣環(huán)境包括土地、資源與空間位置等因素,是決定國家發(fā)展道路、發(fā)展模式甚至發(fā)展水平的決定性因素。只有地緣環(huán)境占優(yōu)勢的國家和民族才能夠獲得良性發(fā)展,否則國家將無法獲得良性發(fā)展而處于相對落后狀態(tài)。對于國家來說,是空間決定了歷史進程、國家間關(guān)系以及國家的興衰,對于地緣環(huán)境不理想和無法改變地緣環(huán)境的國家來說,只能處于大國競爭的悲慘“宿命”之中。如果從這種宿命論出發(fā),地緣環(huán)境惡劣的國家為了獲得更好的空間環(huán)境對它國實施侵略就是一種必然的選擇,若這種行徑在理論上合理,就成為侵略有理了,這顯然是不符合人類的價值觀念和發(fā)展規(guī)律的。從這種角度來看,“環(huán)境決定論”是錯誤的,那么過去和現(xiàn)在地緣戰(zhàn)略地位突出的國家無法逃脫大國爭奪的悲慘命運的結(jié)論,就無法站住腳。也就是說,破除了“宿命論”的迷信,某一國家或地區(qū)的地緣戰(zhàn)略地位就是可變的。
摩根索認為,“地理因素決定的帝國主義類型,在歐洲列強獲取歐洲大陸支配地位的政策中得到了最清楚的體現(xiàn)”,這主要是“由大陸的地理局限所決定的,但地理并非唯一的決定性因素”。[9]他的分析中體現(xiàn)了地理因素對政治形態(tài)以及權(quán)力爭奪產(chǎn)生了影響,但不是唯一的影響,這與“環(huán)境決定論”已經(jīng)有了一定的距離。地理環(huán)境是人類生存和發(fā)展的必要條件,不僅能夠影響到人類的生產(chǎn)和經(jīng)濟生活,還影響人類的軍事、政治等各方面活動。但環(huán)境并不能決定人類社會發(fā)展的程度和水平,是“人們所達到的生產(chǎn)力的總和決定著社會狀況”。[10]地理環(huán)境的影響將隨著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的提高而不斷弱化。人類生產(chǎn)的發(fā)展將導致人的能動性的提高。從根本上來說,不是地理環(huán)境決定人類的發(fā)展,而是社會條件制約和改變著地理環(huán)境對人類社會發(fā)展的作用。因此,破除“環(huán)境決定論”的根本因素在于人類生產(chǎn)的發(fā)展。
其二,是海權(quán)與陸權(quán)的對立以及國家利益的排他性所帶來的零和博弈理念。地緣政治理論從實現(xiàn)和維護國家的權(quán)力和利益的視角出發(fā),來思考和處理國際關(guān)系中所遇到的問題。在處理國際關(guān)系的過程中,需要認識清楚的問題,一是時代的特征和可以允許的行動準則,一是彼此的實力對比和地緣政治上的差異。要維護或扭轉(zhuǎn)實力對比關(guān)系以便贏得優(yōu)勢和權(quán)力,就需要把握地緣政治差異,地緣政治學著重思考的核心命題即在于此。從全球整體的地理狀況以及地緣政治理論的發(fā)展脈絡(luò)來看,從對世界霸權(quán)的歷史爭奪來看,都是“以海陸(空)差異作為最大的地緣政治差異”。[11]在這種差異觀基礎(chǔ)上,具有陸權(quán)優(yōu)勢國家實力的增長,就要迎來對具有海權(quán)優(yōu)勢國家的壓迫,甚至會剝奪海權(quán)勢力的優(yōu)勢,從而進入陸權(quán)國家的霸權(quán)時代。為此,海權(quán)國家要盡力防止這種狀況的出現(xiàn),并以相應的地緣戰(zhàn)略應對。與之相反,海權(quán)優(yōu)勢的增長也會帶來陸權(quán)勢力的應對。進入到這種思維慣性之中,海陸對抗就真的是一種必然的“宿命”了,大國之間的對立和爭奪也就成為地緣政治理論的主題。由此,地緣政治熱點地區(qū)也就必然存在著對立和爭奪,不同大國之間的爭奪“表現(xiàn)為強國對地緣戰(zhàn)略要地的高強度控制”。[12]這種爭奪具有強烈的排他性,一方之所得,必然帶來一方之所失,這種排他性或獨占性的零和博弈更加深了爭奪的必然性、激烈性和殘酷性。如果這種思維成為政策的基礎(chǔ),敵意也就成了自我實現(xiàn)的預言,這是地緣政治理論在某種程度上符合世界歷史發(fā)展進程的根本原因。
按照對抗性思維的邏輯,國家之間的合作甚至和平只能是分裂的世界中的一種臨時狀態(tài),不同國家和國家集團之間的對抗和沖突將是一種常態(tài),這是源自霍布斯精神的一種解釋。但事實上,隨著近代以來尤其是冷戰(zhàn)結(jié)束后全球化的不斷深入發(fā)展,國家之間在經(jīng)濟發(fā)展、生態(tài)安全乃至國際政治問題等方面的相互依賴日益增強。國際組織日益發(fā)展,各國共同遵循的規(guī)則和制度對國際問題處理的影響力愈益增強。在諸多國際問題的解決上,合作、共贏的思路和政策逐漸被世界各國所理解和接受。這并不是說“當相互依賴普遍存在時,國際沖突就消失得無影無蹤”,[13]但這至少說明對抗性思維與零和博弈不再是處理問題的唯一方式,合作與發(fā)展也可以成為處理國家間關(guān)系的思路和政策。這種狀況的發(fā)展,為現(xiàn)實或潛在的地緣戰(zhàn)略地位凸顯國家,轉(zhuǎn)變虛弱和混亂的狀態(tài)提供了相對良好的外部環(huán)境和發(fā)展方向。若其內(nèi)部發(fā)展得到顯著改善,其地緣戰(zhàn)略地位也必然將發(fā)生變化。
從地緣政治和地緣戰(zhàn)略理論本身的邏輯結(jié)構(gòu)來看,地緣戰(zhàn)略地位也是可變的。地緣關(guān)系包含著地緣政治、地緣經(jīng)濟、地緣文化等多方面內(nèi)容,其中地緣政治是核心因素。地緣政治是不同政治單元圍繞著權(quán)力和利益所展開的活動的總稱,或者說,“地緣政治就是各個文明實體為了利益而在特定時空圍繞著空間控制權(quán)所展開的活動和所結(jié)成的關(guān)系及規(guī)約”。[14]也就是說,地緣政治學是一種主觀的認知體系,而地緣政治則是一種客觀存在,地緣政治的爭奪處于不斷的動態(tài)變化之中。為了在地緣政治爭奪中占據(jù)優(yōu)勢,國家需要根據(jù)不斷變化的國際形勢制定切實可行的地緣戰(zhàn)略。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地緣戰(zhàn)略就是利用國家間的地緣關(guān)系獲取國家利益的謀略”。[15]有人認為,“地緣戰(zhàn)略地位,主要是指由地理位置決定的戰(zhàn)略地位”。[16]但從地緣本身所包含的維度和地緣戰(zhàn)略實施要面對國家實體這一現(xiàn)實,地緣戰(zhàn)略地位應該是由某一國家或地區(qū)的地理位置以及內(nèi)部發(fā)展程度和穩(wěn)定狀態(tài)所決定的戰(zhàn)略地位。
地緣戰(zhàn)略地位處于高位的國家需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方面,該國地理位置重要,是一個大國影響和遏制另一個大國或潛在大國的戰(zhàn)略前沿;另一方面,該國相對來說是脆弱的、混亂的、不穩(wěn)定的,也就是大國比較容易介入并發(fā)揮影響的地區(qū)。從空間的靜態(tài)的角度來分析,國家的地理位置從現(xiàn)代的意義上來說,發(fā)生重大變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從時間的動態(tài)的歷史發(fā)展過程的角度來分析,地緣戰(zhàn)略地位本身會隨著地緣政治、地緣經(jīng)濟的動態(tài)變化,尤其是該國內(nèi)部發(fā)展的程度與水平同世界的橫向比較,以及國家內(nèi)部穩(wěn)定性的變化,而不斷發(fā)生變化。斯皮克曼認為,“爭奪實力的斗爭本身會把一些地區(qū)提到顯著地位,而把另一些地區(qū)暫時降到被人遺忘的地位”,地緣政治分析“主要的特點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動的形勢而不是靜的形勢”。[6]也就是說,隨著條件的變化,地緣關(guān)系就會發(fā)生變化,“地緣環(huán)境具有一定的可變性”,[11]那么地緣戰(zhàn)略地位也必然會發(fā)生變遷。
“復雜的世界地緣政治格局本質(zhì)上存在著連續(xù)與變化的對立”。[4]變化是事物聯(lián)系和發(fā)展的根本規(guī)律,變化的觀點才能打破地緣政治理論發(fā)展過程中的“決定論”傾向,逐步破除地緣政治上的對抗性思維,才能推動世界向著更加和平友好的方向發(fā)展。某一國家或地區(qū)的地緣戰(zhàn)略地位,會隨著不同時期人類生產(chǎn)能力、地緣戰(zhàn)略重點區(qū)域自身的發(fā)展、實力中心的動態(tài)轉(zhuǎn)移和政策取向以及國際秩序及其運行規(guī)則等因素的變化,而不斷發(fā)生變化。通常來說這種變化不是在短時期內(nèi)能夠?qū)崿F(xiàn)的,需要相對較長時段的歷時性發(fā)展來實現(xiàn)。因此,地緣戰(zhàn)略地位是不變性和可變性的統(tǒng)一,不變性是相對的,可變性是絕對的,它如同人類社會的發(fā)展一樣,也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
三、地緣戰(zhàn)略地位變遷的影響
既然地緣戰(zhàn)略地位具有可變性,那么對于某一國家或地區(qū)來說,應該如何看待地緣戰(zhàn)略地位的變遷,或者說地緣戰(zhàn)略地位的凸顯與弱化哪種狀況才更理想呢?要回答清楚這樣的問題,必須放在具體的地緣環(huán)境中分析。
保羅·肯尼迪認為,歷史上歐洲大國之間頻繁的沖突和不斷的變換組合,“同時它還表明了地理因素的重要性。這里所說的地理因素不僅包括一個國家的氣候、原料、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力、可以利用的商路等因素,盡管這些因素對一國的全面繁榮強盛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指每個國家在這些多邊戰(zhàn)爭中所處的戰(zhàn)略位置這樣一個關(guān)鍵問題”。[17]巴爾干半島在近代被稱為歐洲的“火藥桶”,地緣戰(zhàn)略地位極為突出,也正是因為其地緣戰(zhàn)略地位的極端突出和敏感性,所以“1914年7月的暗殺,是歷史上引起全面危機進而爆發(fā)世界大戰(zhàn)的特殊事件中最突出的例子”,[17]那里成為兩大集團廝殺的第一個戰(zhàn)場,給本地區(qū)帶來的是空前的災難。從近代的英俄角逐到冷戰(zhàn)后的美蘇爭霸,直到今天美國成為唯一的全球性大國,阿富汗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緣戰(zhàn)略地位。也正是因為其重要的地緣戰(zhàn)略地位,冷戰(zhàn)時期蘇軍入侵阿富汗,今天美國以打擊恐怖主義的名義依然在進行著阿富汗戰(zhàn)爭。如何促進阿富汗的發(fā)展,努力通過自己的發(fā)展改變其地緣戰(zhàn)略凸顯的狀況,恐怕是改變阿富汗“宿命”的根本出路。從上述的例子中,我們看到地緣戰(zhàn)略地位突出所帶來的是災難,但這也不是千篇一律的結(jié)局。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之后,德國和日本兩個法西斯主義國家戰(zhàn)敗并且本土被盟軍占領(lǐng)。但由于在戰(zhàn)后的美蘇爭霸中,兩國所處的特殊的地理位置,成為美國遏制蘇聯(lián)的戰(zhàn)略前沿而凸顯其地位,這是兩國創(chuàng)造戰(zhàn)后迅速發(fā)展“奇跡”的最為重要的有利因素。波蘭在冷戰(zhàn)時期也曾是布熱津斯基眼中的地緣政治要害國家,冷戰(zhàn)結(jié)束之后其地緣戰(zhàn)略地位相對弱化了,但也并沒有因此就延緩了波蘭的發(fā)展甚至降低其國際地位,從長期來看,這種狀況可能是其發(fā)展的良好契機。
從人類歷史發(fā)展的長期視角來看,發(fā)生地緣環(huán)境變化的情況是非常多的。例如,在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崛起之前,地中海地區(qū)是連接歐亞的樞紐地帶,隨著“地理大發(fā)現(xiàn)”的進展,好望角航路的開辟使地中海喪失了這一優(yōu)勢,而蘇伊士運河的通航又降低了好旺角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jīng)濟地位。1967年阿以戰(zhàn)爭中,蘇伊士運河的關(guān)閉卻優(yōu)化了歐洲大西洋沿岸地區(qū)的地緣環(huán)境,使南歐遭受其負面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美蘇兩國展開了對廣大亞、非、拉美等發(fā)展中國家的爭奪,一方面凸顯了很多發(fā)展中國家的地緣戰(zhàn)略地位,提高了這些國家與大國討價還價的能力,另一方面也給很多國家?guī)砹藨?zhàn)爭和災難。冷戰(zhàn)結(jié)束之后,這些發(fā)展中國家不再具有美蘇爭霸時期凸顯的中間地帶的地緣戰(zhàn)略地位,相對而言也就失去了對大國的吸引力,但這卻有可能營造出有利于發(fā)展的比較和平的國際國內(nèi)環(huán)境。[18]馬六甲海峽隨著東亞地區(qū)及世界經(jīng)濟的發(fā)展其地位日益凸顯,但歐亞大陸上的輸油管道建設(shè)、陸上交通工具的突破性發(fā)展或?qū)碓隈R來半島的蜂腰地帶開鑿運河,都將影響到新加坡的優(yōu)勢地位,而提高其他區(qū)域的地位。“北冰洋在兩半球之間主要起了阻礙交通的作用”,[6]若在未來的日子里因氣候或者人類交通運輸能力的改變可以使天塹變通途,那么北冰洋地區(qū)的戰(zhàn)略地位將發(fā)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過去和將來,已經(jīng)發(fā)生的和將要發(fā)生的類似變化是非常多的。
地緣戰(zhàn)略地位的凸顯與否和國家的生存與發(fā)展具有重大的關(guān)聯(lián)性。20世紀初朝鮮半島成為日俄爭奪的焦點地區(qū),其地緣戰(zhàn)略地位處于空前的高位狀態(tài)卻導致了朝鮮半島亡國的厄運;冷戰(zhàn)時期朝鮮半島突出的地緣戰(zhàn)略地位,使其成為兩大集團對峙的前沿地區(qū)之一,卻使南北雙方都擁有過一個相對有利于內(nèi)部發(fā)展的時期。可見,地緣戰(zhàn)略地位凸顯有可能帶來發(fā)展的機遇,也有可能帶來戰(zhàn)爭乃至亡國滅種的厄運。地緣戰(zhàn)略地位回歸到平靜狀態(tài),可能會使國家失去與大國討價還價的機會,也有可能帶來適合發(fā)展的國際國內(nèi)環(huán)境。[19]對于不具有天賦的資源已成為地緣政治核心的國家來說,重要的不是自身的地緣戰(zhàn)略地位如何,更應該關(guān)注的是地緣政治的現(xiàn)實和未來發(fā)展的方向,并在其中尋找到適合自己的生存和發(fā)展的方式。也就是說,地緣環(huán)境對于國家戰(zhàn)略具有重要影響,“它既可能為一個國家提供某種機會和條件,也可能嚴重地限制一個國家的某些政策和活動”。[11]因此,國家應該充分利用自己的地緣政治優(yōu)勢,克服自己的地緣政治劣勢,以揚長避短、趨利避害。世界上的國家依其地緣位置的不同可以劃分為大陸國家、沿海國家、群島國家、內(nèi)陸國家等,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獨特之處,在國際關(guān)系上都處于不同的地位,重要的是不同的國家都能夠制定出適合自己發(fā)展的國家戰(zhàn)略。
當一個國家或地區(qū)不具有突出的地緣戰(zhàn)略地位的時候,就要利用難得的和平穩(wěn)定的環(huán)境,推動國家的發(fā)展。當處于大國爭奪的時候,弱小的不穩(wěn)定的國家經(jīng)常會成為地緣戰(zhàn)略上爭奪的焦點。但并不是弱小就一定會無所作為,“弱國常常能夠在均勢的空隙里找到運作的機會”,[20]只是機會只會留給有充分準備和善于利用的一方。雖然按照進攻性現(xiàn)實主義理論,生存是大國的首要目標,“在無政府狀態(tài)下,對生存的渴望促使國家實施侵略行為”,[21]使世界總是充滿著安全的競爭,存在不利于地緣戰(zhàn)略地位突出國家生存和發(fā)展的因素。但是,連經(jīng)典現(xiàn)實主義的大師摩根索都說,如果擴張性大國目標制定有誤并傾向于毫無限度,那么“不是征服者在吞并領(lǐng)土并從中獲得力量,而是領(lǐng)土在吞噬著征服者,削弱他的力量”。[9]競爭勢力之間的斗爭并沒有那么可怕,在主權(quán)國家原則下,強權(quán)滅亡它國和殖民的時代已經(jīng)一去不復返了,因此“如果霸權(quán)國只是維護自身的優(yōu)勢地位,而無意征服他國,則他國也將從中受益”。[13]
由上述可見,地緣戰(zhàn)略地位的可變性,從理論上來看是地緣政治理論自身的內(nèi)在邏輯要求,從實踐上來看是大國間實力對比和爭奪戰(zhàn)線動態(tài)轉(zhuǎn)移的結(jié)果,從某一地區(qū)或國家來看,在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但“從根本上說,都是因為經(jīng)濟上不去”,[22]因為內(nèi)部的混亂和不穩(wěn)定。在和平與發(fā)展成為時代主題的條件下,扭轉(zhuǎn)地緣戰(zhàn)略地位的根本方式,一是通過內(nèi)部努力營造團結(jié)穩(wěn)定的內(nèi)部環(huán)境,二是“要緊緊抓住經(jīng)濟建設(shè)這個中心,不要喪失時機”,[22]努力推動自身的發(fā)展。這是一個國家的外交戰(zhàn)略甚至國家戰(zhàn)略需要優(yōu)先思考的重大問題。
[1][美]A.T.馬漢.海權(quán)對歷史的影響[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6.24,25,序2.
[2][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紀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16,31,17,19,115,124.
[3][英]哈·麥金德.歷史的地理樞紐[M].北京:商務(wù)印書 館,2008.49-50,50,14,44.
[4][英]杰弗里·帕克.地緣政治學: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3.31,31,163,48,99.
[5][英]P·奧沙利文.地理政治論[M].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1.34.
[6][美]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學[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65.17,78,108,15-16,34.
[7][美]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競賽方案[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8.19,26,47.
[8][美]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大棋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5,41,53-54,255.
[9][美]漢斯·摩根索.國家間政治[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94,149.
[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0.
[11]李義虎.地緣政治學:二分論及其超越[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4,44,47.
[12]鞠海龍.論地緣政治的“對抗性”思維[J].世界經(jīng)濟與政治論壇,2009,(5):59.
[13][美]羅伯特·基歐漢,約瑟夫·奈.權(quán)力與相互依賴[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9,46.
[14]張江河.對地緣政治三大常混問題的辨析[J].東南亞研究,2009,(4):82.
[15]高金鈿.國際戰(zhàn)略學概論[M].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5.130-131.
[16]朱聽昌.試論中國地緣戰(zhàn)略地位的變遷[J].教學與研究,2009,(12):46.
[17][美]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M].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6.81-82,182.
[18]王慶忠.冷戰(zhàn)后東北亞地區(qū)安全困境形勢探析[J].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4):12-16.
[19]趙月峰.朝鮮半島危機的建構(gòu)主義解讀[J].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6):49-53.
[20][美]肯尼思·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48.
[21][美]約翰·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52.
[22]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54,270.
The Variability of Geo-strategic Status and Its Influences
WANG Zhi-wei
(Dept.of Social Sciences,Yanbian University,Yanji,Jilin,133002,China)
Theory of geopolitics will focus on different geo-strategic regions when it is applied by different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It should be admitted that geo-strategic status contains variability if taking the denial of the viewpoints on“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and“antagonism”,and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theory into consideration.As for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geo-strategic status,it is important to grasp opportunities in different periods so as to forward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their social stability.
theory of geo-politics;geo-strategic status;variability;influence
D815
A
1009-3311(2011)05-0030-06
2011-08-08
王志偉(1973—),男,吉林永吉人,延邊大學社會科學基礎(chǔ)部副教授,在讀博士。
[責任編校:吳守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