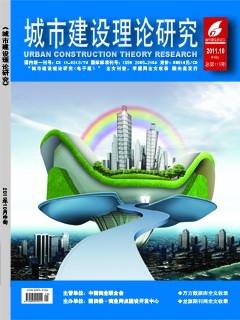綠色運動對生態建筑設計的影響
劉芳
綠色是春天的象征,綠色象征生命。在色彩學中,綠色屬冷調。但這個冷并非冷漠無情的冷,而是泛指其在人的視覺感受中,綠色蔥籠,令人身心愉悅、寧靜不躁、綠色使空間開闊宜人。生活在地球上的不同種族、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都幾乎毫不例外地認識到綠色與人生的關系。萬綠叢中一點紅,不只是一個文學形象,而是飽含生態哲理。綠色是地球生機旺盛的外顯,是自然界風調雨順的象征。綠色伴隨人類一生。綠色與國家前途,人民生活,全民健康息息相關。我國加入WTO后,在農產品出口市場便因農藥殘留超標,達不到“綠色壁壘”(國際貿易中的一種非關稅壁壘,亦稱“環境壁壘”)而屢屢受阻。人類只能同大自然和諧相處,惜綠、造綠,一生投身綠化建設才是改善自身生存環境的唯一途徑。
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綠色建筑受到建筑界關注,但綠色運動的主要倡導者,并不是建筑師,而是一批生物學家、生態學家,是他(她)們促成了地球上不同文化、不同族類、不同信仰、不同職業的人們根據各自的人生體驗,促成了觀念的更新,從人本中心論轉向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
綠色運動普遍被世人接受,應歸功于一位孱弱而又堅韌圖強的女性,美國海洋生物學家、生態學家和作家蕾切爾??卡遜,卡遜是一位為了拯救受到人類工業文明破壞,向人為破壞自然世界而進行抗爭的領導者。
卡遜在她的論述中,提出了一個當時尚不為人注意的生物破壞現象,她著重描述了由于農業生產中廣泛使用像農藥DDT這樣的殺蟲劑所帶來的對生物鏈的巨大破壞。由于在環境食物鏈中的逐步集聚,DDT對范圍很廣的生命物種具有毒性,也造成了嚴重環境污染。突出的表現之一如導致一些鳥類蛋殼變薄,鳥類、魚類大量死亡,甚至連金鷹和隼一類生命力旺盛的飛禽也難逃厄運。因此她告誡人們要加倍重視人類與大氣、土壤、海洋、河流、動物和植物之間相依相存的密切關系,重建人類與自然界的和諧、統一的關系,一旦掉以輕心,勢必禍及地球上一些生物物種的滅絕。卡遜的重大發現,為當代人敲響了警鐘;人類必須要遵循自然規律、維護生態;慎思因果,否則將遭到滅頂之災。
人類“只有一個地球”生態學的一個基本原理:宇宙間任何事物都不能夠從其它事物的關系中分離出去,這一深層次生態觀,提醒人類,人類雖說號稱萬物之靈長,或者說不愧為理性的生靈而獨立生存,在整個生態系統中人類確實具有自己的特殊地位,但前提是要摒棄西方社會所強調的人與自然分離這一二元論觀點,而要遵循進化論所強調的:人既是自然界優越的產物,具有人類高級生物之故,其余物種才有可能存在。或者說更好地生存,但人始終又是自然界中的一個部分存在,而且也只有將自己置身于整個復雜多變的自然關系網絡中,在自然的報復面前,要反思、要律己,人才能體現自己特殊的價值。這個辨證關系警告人類絕不能因此而貴已踐物、凌駕于自然之上,或隨意塑造自然。只有同自然融為一體,方能既改善自身的生存環境,受益于自然,又不致禍及子孫,欠下兒孫債。人與自然的關系如此,建筑的自然的關系亦如此。
生態建筑的核心,可用賴特在他的有機建筑論中的幾個論點作答:建筑設計是整個環境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非主角;強調同周邊環境相依相存、共同工作、不能破壞其它物種生存。這一點同綠色建筑運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生態學家認為,生態系統處于一種活躍的狀態,即處于一種不停流動的狀態之中。而建筑亦如此,同生物圈中所有生態系統一樣都是動態系統,隨時間的改變而變化。哈沃德·奧德姆指出,微生物系統隨時間的變化,能量的新陳代謝處于變化狀態。
深入比較生態學家和建筑師環境概念的異同, 我認為,整體生態建筑觀所體現的空間因素影響至為關鍵。生物圈是個相對封閉的系統,而建筑系統是一個開放系統,與外界生態系統環境存在著相互依存的關系,在承受外部生態系統環境影響的同時,反過來又影響外部環境,但這些相互作用是以一定的空間范圍為基礎的,而不是僅僅促限于指定設計場地之內。空間因素的影響主要表現為,1、對周圍生態系統的空間置換影響;2、對周圍生態系統的空間影響的特定范圍。
森林型生態城市,早于上世紀六十年代已見諸極報端。再說,城市綠化并非光靠大樹進城,而是需要本土“野草”“閑花”和灌、喬植物結構合理的立體生態系統,城市綠化是不能以犧牲異地農業生態為代價的,不能拆東墻補西墻,否則,不僅會加速珍貴樹種的滅絕,破壞水土、惡化環境,還必然因無知或知其不可行而行之,造成對社會、人類的罪過。
值得反思的是,這些年有不少地方的城管部門,有意無知地為大樹進城大開方便之門,僅管容許大樹進城意在促進不同城市綠化上一個臺階,但實效如何?則疏于考慮,或者說一經發現失誤,已無回天之力。古樹進城之風,不僅破壞了自然資源,也助長了社會資本的浮華之舉。凡此種種弊端,又牽扯到一個歷史性錯誤,在50年代末不容抗拒的積左思潮泛濫下,不少城市都在未來綠化建設布置上宏觀失控,比如與城市規劃設想相應規模的苗圃基地,而且是鄉土苗圃區系多樣方能適應國內東南西北中氣候差異驚人的不同環境。以上兩例是對違反自然法則者的報應。為什么?因為宇宙間的不管是植物或是動物,都并非隨人意分布于地球表面,而不同生物的生存,繁殖都與不同地域的地形、土壤、氣候、水文密切相關。一草一木的異地種植都將喪失生態平衡,或者說影響到各種生物的系統平衡。
生態系統中的空間異質性無處不在,幾乎遍及自然界中一切生物。日本《建筑都市報》(A+U)雜志曾以“什么是生態學?何為接近生態建筑的實例?”為題采訪過不少建筑師和相關專業的學者,絕大多數人認為:任何一個建造在生態系統中的建筑,總會對周圍生態系統產生影響,例如建筑會導致土壤腐蝕、改變雨水流量、改變空氣流動的方向和速度、遮擋太陽輻射等,所以建筑系統影響了生態系統的特定空間片段。” 由于生態系統的空間異質性反映特別敏感,建筑系統對周圍自然生態系統的影響程度也隨因地理區位等條件不同而程度不同,因此,伊安·麥克哈格認為,每一個設計地段都應在考慮下列條件的前提下,獨立評價:1、生態系統的自然價值;2、生態系統的過程;3、生態系統的限制條件;4、生態系統固有的自然機制,因為不同設計地段周圍生態系統的屬性會隨著地點的變化而變化。”
鑒于上述,建筑師在設計中必須充分把握設計地段的生物要素和非生物要素的組成,把緊總圖設計關,充分利用自然條件,如以植綠減緩高溫,過濾空氣。“少費多用”使生態系統空間置換中的影響越少越好,同時要考慮建筑系統中各種能量和物質材料的增量適宜于原有生態系統,將間接空間置換影響減少到最低限度。
挪威哲學家阿恩·那伊斯1972年寫道:“深層生態學的本質在于質詢更為深
刻的問題:究竟是何種社會、何種教育,以及何種宗教組織有助于將地球上的各種物種視為一個整體。盡管生態學理論的重點是探討人類和自然的分離以及其它一些關于人類和地球關系的基本問題。深層次生態學家認為傳統的環境研究對于受到傷害的地球的幫助就象止血膠條,對傷口的作用那么膚淺。盡管這一觀點也曾招致不少人認為“說得多,做得少”的批評,但細究其深層次生態學的觀點,它自始至終是與綠色建筑運動關系密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