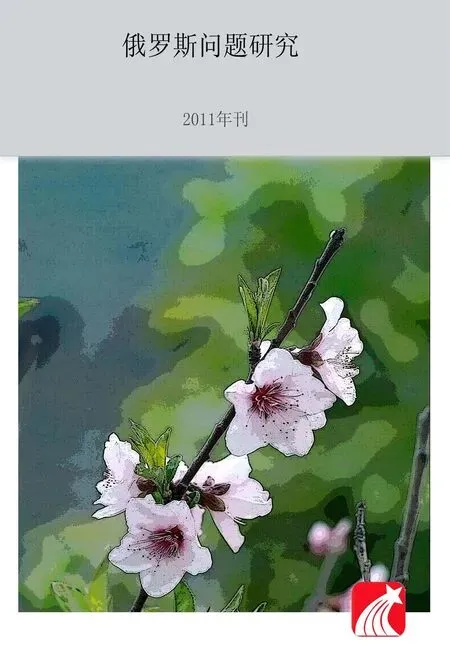梅德韋杰夫的“第三條道路”
阿爾季安·巴伯斯坦 著 黃登學 編譯
梅德韋杰夫的“第三條道路”
阿爾季安·巴伯斯坦 著 黃登學 編譯
《全球政治中的俄羅斯》2010年第5期刊登了英國肯特大學政治學教授阿爾季安·巴伯斯坦所著的題為《梅德韋杰夫的“第三條道路”》的文章,文中指出,梅德韋杰夫執政后改變了俄羅斯的內外政治方針,實行的是一種既有別于自由主義、又與保守主義不同的路線;梅德韋杰夫提出的現代化戰略不是一個促進經濟發展的狹隘技術性方案,而是一個通過融合俄羅斯內外政策、調整國內發展軌道及建立更加穩固的基礎來增強俄羅斯在國際舞臺上作用的大膽嘗試,它應當被視為梅德韋杰夫式的“第三條道路”,這一道路尚未實現的潛力正在為俄羅斯的系統性變革打開通道,從而將推動符合俄羅斯優良傳統的真正的現代化。現將文章部分觀點介紹如下。
一
對于德米特里·梅德韋杰夫總統的現代化戰略,國內外反對他的人都持一種懷疑態度。一些批評者斷言,該戰略過于“迷戀”高新技術,不實行全面的政治自由化與司法改革,它將不會帶來什么成果,而全面的政治自由化與司法改革必然遭到普京和掌控俄羅斯政府與商界的“強力”集團的阻撓。
梅德韋杰夫執政后改變了俄羅斯的內外政治方針,開始實行另外一種既有別于自由主義、又與保守主義不同的路線。對國家與市場相互關系的多元論認識,鞏固作為中介者的公民社會,促進中小商業和地區發展以取代完全依靠個人意志或中央集權的國家機關所具有的至高無上的權力——這些即是梅德韋杰夫“第三條道路”的基石。
梅德韋杰夫的現代化戰略提出,俄羅斯需要更加注重鞏固與那些準備與其進行互利合作的國家和機構的聯系,雙方合作的起點是以自然資源的出口換取技術與投資。梅德韋杰夫總統在2010年7月12日有關對外政策的講話中聲稱,世界經濟危機已經導致“國際關系范式的轉換”,這為俄羅斯帶來了“最為有效地利用對外政策手段實現國家現代化目標的獨特機遇”。他指出,沒有與國內外的廣泛聯系,任何個人、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實現其獨特或至高無上的影響力。
對于最近幾年俄羅斯國內——從不完善的代議制民主到半獨裁的行政制度——所取得的進步,梅德韋杰夫總統并不認同,而是贊成下面這種說法,即:市場經濟與民主制度不僅需要正式的自由主義性質的機構設施,而且需要公民社會框架內的非正式社會聯系。梅德韋杰夫有關“俄羅斯公民社會虛弱,而自我組織與自我管理水平低下”的看法是其現代化戰略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該戰略的目標就是要改變俄羅斯千百年來所形成的行政命令式管理方法,而代之以政治生活中的個體首創精神與公民社會參與原則。
二
考慮到俄羅斯落后的經濟以及世界競爭的壓力,技術現代化是實現俄羅斯國家進步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確保所有權的安全和鞏固法律的權威當然很重要,但技術與外資也需要許多其他機制和新辦法。這里不僅指物質基礎設施以及需要財政扶持的高等教育或者科技發明的轉化能力,而且指健全的公民社會賴以依靠的互信與互助的緊密社會關系。因為沒有信任與始終不渝的公民美德,簽定契約和調動創業積極性的經濟成本可能會高得無法接受。
西方自由主義在強調社會契約以及財產領域契約關系的同時卻忽視了非正式的社會文化因素,這些社會文化因素在經濟發展和政治生活中同樣發揮著關鍵作用,這也是總統將政治經濟改革與社會本身的變革聯系起來的原因所在。
正如梅德韋杰夫多次強調的那樣,僅僅改革落后的經濟是不夠的。俄羅斯是一個擁有相互之間寬容相待的不同宗教與世界觀的多民族國家,俄羅斯的任務是要建立健全公民社會,使俄羅斯的發展符合其多民族國家的這些優良傳統,并使人們養成熱愛大自然的習慣,善待被斯大林工業化以及休克式經濟危機嚴重損害的周圍環境。
人的相互關系與人的聯合體是新發展模式的核心,世界的財政資源應服務于能夠創造收益的生產活動的需要。就俄羅斯而言,就是要發展農村與農業,同時借助于外國資本發展現代生產與高新技術領域。梅德韋杰夫的現代化戰略至今仍然存在有待實現的潛力:將俄羅斯的發展與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結合起來。
三
在西方和東方正在進行的有關多極化與多邊世界的對話沒有考慮到老牌帝國回歸以及新興帝國誕生的進程問題。也許,除了非洲以外,帝國形式正在所有大洲興起:拉丁美洲的巴西、歐洲的歐盟、中東及南高加索地區的土耳其、波斯灣地區的伊朗、歐亞大陸上的俄羅斯、東亞的中國以及南亞次大陸的印度。美國在北美以及中美洲的霸權可能正在走向衰落,但美國仍然是一個世界超級大國。
毫無疑問,這些(以及其他一些)國家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也許需要更為準確地指出帝國、殖民大國以及霸權國家之間的不同。然而,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快速發展的市場國家,其影響力都遠遠超出了它們的國家邊界。歸根結底,實際上任何一個國家政權都天然地抱有帝國追求。首先,任何一個政權都力圖穩定邊境地帶的不安定的形勢(俄羅斯在北高加索,而歐盟則是在巴爾干);其次,任何一個大國都力圖通過地緣政治手段(俄羅斯設在中亞地區的軍事基地或者中國在非洲及橫跨各大洋的不斷擴大的存在)確保自己地緣經濟利益的安全;再次,每一個大國都力圖實現某種文明的使命(美國爭取民主的“十字軍東征”、歐盟方面的人權“出口”或者中國對所謂“和諧發展”理念的宣傳等)。
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意識形態在相當程度上都名譽掃地。蘇聯國家共產主義制度瞬間坍塌之后,與一些人的預判截然不同,世界民主制度并未遍地開花;相反,西方自身還從很多方面偏離了代議制民主與市場競爭的準則與傳統,而走向了專制民主和卡特爾資本主義。同樣,東方宣稱的所謂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絕對至上的說法也沒有引起人們的特別熱情與信任。像俄羅斯和中國這樣的國家,實質上都是帝國性大國,它們認為自己有權在自己的勢力范圍內顯示軟硬實力,甚至有時可以進行軍事干涉(2008年8月南奧賽梯事件即是如此)。
莫斯科和北京在與弱小鄰國的相互關系中仍然保持著納貢體系,它們以提供安全保證來換取銷售市場與廉價商品的進口。俄羅斯出售軍事技術并從中亞地區購買能源以便將其出口到西方,同時引進廉價的勞動力以填補自己人口的不足;中國需要直接獲得原材料以支撐經濟的快速增長,同時需要市場來銷售自己廉價的消費品,鋪設從土庫曼斯坦經由烏茲別克斯坦與哈薩克斯坦到中國的新天然氣管道以及北京對外投資(對非洲以及不久前對希臘和巴爾干管道的投資等)不斷增加的原因就在這里。
中國與俄羅斯對“近鄰”以及“遠處”國家日益增多的經濟干涉可能使它們時不時地卷入到地區沖突中去,因而它們不得不部署軍事基地與軍事裝備來捍衛自己的帝國利益,這也正是兩個大國對海軍艦隊和軍事裝備進行現代化改造與更新的原因所在——因為它們需要在自己的國界之外展示實力。
如同19世紀大國角逐中沙皇俄國與大英帝國劃分自己的利益范圍那樣,21世紀莫斯科與北京也在謀求中亞地區的霸權。就本質而言,這些國家就是某種形式的帝國,和過去一樣,它們的勢力范圍也存在重合之處,因而可能會引起摩擦與沖突。雖然不久前這些國家間的貿易與政治關系發展很快,但它們之間的相互猜疑以及公民社會層次上穩固聯系的缺失卻增加了對抗的風險。在大國新一輪的角逐中,能源安全的地緣經濟意義并不比控制領土的地緣政治意義小,甚至,前者的意義可能還更大。由此一來,中俄合作與伙伴關系將越來越有可能蛻變成一種戰略競爭關系。這一點,再加上對實現現代化的迫切需要,將進一步驅使俄羅斯步入廣闊的歐洲軌道。
四
上述發展趨勢對于俄羅斯的現代化戰略來說具有三重后果。
第一,正如現代化的自由主義辯護者所斷言的那樣,經濟與法制的現代化決不意味著必然能夠促進政治向代議制民主方向發展,民主的革新更有可能發生在現有憲法與政治制度的框架內——比如說,通過能夠導致選舉競爭的各種力量組合的摩擦與碰撞等。
第二,俄羅斯復興的帝國因素使制度的建構與鞏固成為一個更加重要的優先領域。不論在國內還是在國際舞臺上,莫斯科都需要更加廣泛而優化得多的制度化途徑來控制帝國勢力范圍,莫斯科需要現代化的行政、公民與政治制度。
第三,在中亞地區與中國日益加劇的競爭導致不太可能建立長期的東方“軸心”,俄羅斯與西方實現融合的可能性在增大,但這種融合并不是像上世紀90年代初所設想的那樣。回歸西方比較可能的情況是,在梅德韋杰夫時期,俄羅斯利用現代化的目的是要展示自己是西方文明的另外一個支柱,這個支柱擁有構建泛歐經濟共同體以及安全體系的平等權利。
從這個意義上講,今天的俄羅斯現代化戰略具有雙重目標。一方面,美俄關系的“重啟”正在增加俄羅斯在世界政治中的分量,而新的削減核武器條約也將使俄羅斯逐漸騰出資源用于軍隊的現代化建設并提高其戰備水平;另一方面,與土耳其以及烏克蘭關系的改善為俄羅斯提供了其與歐盟關系的另一個杠桿。并未加入歐盟的這一新的國家“軸心”有可能把自己看做是“大歐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沒有它們歐盟將無法在“大中東”以及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黑海地區或歐亞大陸的中心地帶發揮影響。
由此看來,梅德韋杰夫式現代化并不是一個促進經濟發展的狹隘技術性方案,而是一個調整俄羅斯國內發展軌道與建立更加穩固的基礎以增強其在國際舞臺上作用的大膽嘗試。俄羅斯總統擬定的這些政治計劃,實現了俄羅斯對內政策與對外政策的融合。
當然,在梅德韋杰夫的戰略中也存在大量的內部矛盾與缺陷,不過他對促進各種中介組織、對公民參與以及國家間合作的高度關注也表明,其方案仍然屬于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傳統思想譜系,若作進一步的聯想,它應當被視做是某種“第三條道路”,這一道路尚未實現的潛力正在為俄羅斯的系統性變革打開通道,從而將推動符合俄羅斯優良傳統的真正的現代化。
譯者單位: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
——評《中國現代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