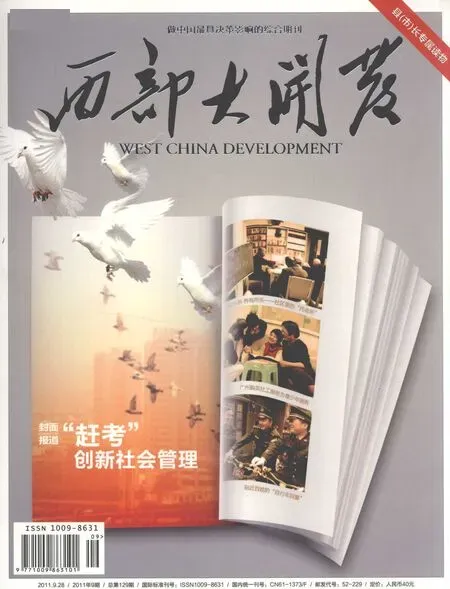發展瓶頸
◎ 文/本刊特派貴州記者 趙良峰 張義學
發展瓶頸
◎ 文/本刊特派貴州記者 趙良峰 張義學
貴州的優勢很多,很多,但這些優勢并沒有進入公眾的視野。除過茅臺酒、遵義城、黃果樹瀑布以外,公眾頭腦中對于貴州的印象,有青山綠水的美麗景象,但更多的是貧困、落后的畫面。
擁有4000萬人口的貴州,今年前半年的GDP總量排在全國的第26位,本刊查閱往年GDP排名情況,貴州也一直靠后。在改革開放的30多年中,在西部大開發的10年里,同為資源大省區的內蒙古GDP能長期保持兩位數增長,同為山區丘陵地形的重慶市也得到長足發展,為什么擁有多種優勢的貴州卻躑躅不前?全省88個縣域,竟然有50多個貧困縣!
瓶頸之一:基礎條件差
“由于山地多、平地少,耕作方式仍然是傳統的原始模式,糧食產量低,再加上人口增長的因素,農業遠遠不能解決當地農民的吃飯問題。于是,農民只有多開墾土地來滿足吃飯需要,亂開墾造成植被破壞、水土流失,非但不能增加糧食產量,而且不少地方土壤退化,出現石漠化現象。由此不少地方陷入了‘越墾越貧’的惡性怪圈。” 宋明所長向本刊記者分析道。
據了解,貴州全省范圍內上萬畝的平整土地僅有40多塊,零碎的土地田塊無法進行機械化耕作。牛犁镢刨等原始的耕作方式一直是貴州農業的主導方式,糧食長期不能自給。農業基礎差,生產力低下,大量的農業人口被“捆綁”在貧瘠的農村田地上。
除此之外,貴州的工業基礎也是相當薄弱。貴州現任省長趙克志在分析全省經濟狀況時認為:“貴州經濟發展慢,慢就慢在工業上。”從1990年到2009年,貴州全省生產總值占全國的比重從1.4%下降到1.1%,這一時期,全省工業增加值占全國的比重從1.2%下降到0.9%,工業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48%下降到30.8%。“即使與新疆、甘肅這樣的西部省區相比,我省工業發展也有很大差距。”趙克志省長為此憂心忡忡,“2010年,我省工業增加值占生產總值的比重僅為33%,分別比新疆和甘肅低5.8和5.9個百分點。由于工業發展滯后,我省經濟實力弱,社會事業發展也處于較低水平。”
謝一認為,貴州經濟落后的原因之一是“工業基礎差,工業產值總量少,工業企業規模小,經濟效益低,產業鏈條短,產業結構不合理!”最典型的現象是“貴州鋁礬土礦藏豐富,當地礦業開發公司開采后,拉到重慶等周邊省區冶煉成鋁錠,再被加工成各種型號的鋁型材,再運回貴州,賣給處在貴州的國防工業企業,生產飛機配件。貴州的工業企業處在產業鏈條的最末梢,由于生產方式粗放,利潤率也最低。雖然擁有豐富的礦藏,卻沒有發揮出相應的經濟優勢。這些現象造成現有的工業企業幾乎沒有利潤可言。”
多位接受本刊記者采訪的貴州學者認為,貴州已經到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時期和緊要關口,要加快實現工業經濟由粗放型增長向集約型發展轉變、工業產品從原材料粗加工向精深加工和配套加工轉變、工業企業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的轉變。
瓶頸之二:觀念守舊
“經濟發展速度,取決于主政者的思想解放程度。貴州經濟發展一直比較緩慢,我認為最大的問題是人的觀念問題,是地方領導決策群體的思想問題,特別是黨政一把手的思想觀念是否真正地解放的問題。”謝一接受本刊采訪時說,“不少縣市的領導人,由于思想不夠解放,沒有抓住發展機遇,造成一方地域的貧困面貌得不到改變,群眾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
“貴州人思想保守!”宋明對此亦有同感。他說,“貴州是典型的‘醒得早,走得慢’。由于思想保守,坐失了很多發展的機遇。比如,貴州的汽車產業,在全國起步比較早,上世紀80年代部分軍工企業轉變經營方向生產民用產品,貴州的汽車工業一度很不錯,‘航天牌’汽車旺銷于全國各地。后來,由于地方與央企的利益博弈中,管理松懈下來,發展日趨緩慢,最終大量丟失市場份額。”
胡錦濤同志在貴州工作時就曾指出,“如果不搞工業,地方財力得不到增加,財政困難的局面就得不到改善;要想發展農村商品生產,不把加工業搞上去,商品生產發展也會受到制約。無論是從壯大我們的財力考慮,無論是從發展農村商品生產考慮,無論是從解決待業青年就業考慮,無論從哪一個方面考慮,都必須發展工業。”
這一思路并沒有被貴州的決策群體充分認識。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很多領導同志都擔心貴州的綠水青山比較多,加快發展會破壞了環境,帶來了污染,在戴上富裕帽子的同時,也戴上一個污染的帽子。領導干部的這一普遍思想長期得不到解放,老百姓只能守著青山碧水過窮日子。
正如前文宋明所說,在生產力低下、工業不發達、物質財富匱乏的情況下,大量農業人口為了生存而過度墾殖,也會使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反之,看一看工業文明高度發達的國家和地區生態環境都保護的非常好,青山常在、碧水長流。比如,我國的福建、江西兩省,和貴州一樣都是多山省份,工業發達,森林覆蓋率也高,均為63.1%。而西部某些省份工業發展滯后,森林覆蓋率卻極其低。
“貴州經濟發展緩慢的歷史根源導致了貴州市場經濟發育不全、發育不夠,市場經濟體系不夠完善。”謝一認為這是貴州經濟的最大劣勢。
與我國整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發展的進程、水平相比較,貴州省的市場經濟改革發展大大滯后,資源配置效率低下,
經濟發展的活力和動力不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還沒有完善起來,催生民營經濟蓬勃發展的土壤、氣候、環境還沒有很好形成,民營經濟自身先天不足、后天發育不良,在經濟夾縫中生存,地位不高門檻高,空間不大風險大,創業艱難。
“改革開放30年過去了,在貴州國有經濟仍然占到國民經濟總量的70%,市場怎么能活起來呢?”謝一告訴本刊記者,“貴州經濟活力不強,開放程度不高。只有各種經濟成分百舸爭流,創造財富的活力才會涌動。民營經濟發展緩慢,實質也是我省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文化思想觀念落后的綜合反映。”
市場主體最重要的是企業。貴州要重視增強企業的市場意識,大力培育市場主體。在這一點上,貴州也曾做過努力。當部分三線企業劃歸地方,地方政府在“保大棄小”過程中把財政拖累后,便失去了信心,由此放置一邊。此時,貴州沒有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以“活”為核心催生壯大各類市場主體。致使大的沒保住,小的沒留下。
教訓尤為深刻。“貴州省為此出臺了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堅決糾正對不同經濟成分畸輕畸重的認識,真正做到對各種所有制經濟一視同仁,讓一批影響力大、競爭力強的大型民營企業和特色產業集群引領我省民營經濟大發展”。 謝一說,“還要引導企業改變陳舊的管理模式,學習先進的管理經驗和方法,跟上市場發展的需要。”
瓶頸之三:城鎮化率低
“我們貴州有88個縣,其中有50多個長期是貧困縣……”宋明在談到貴州貧困地區基數大時指出,“長期以來,國家把大量的資金投入貧困的地區去扶貧,但卻很少使這些地區完全脫貧致富,還給不少貧困地區的老百姓養成了依賴性心理。”
貧困人口多,貧困縣域廣。故而,扶貧工作在貴州一直是一項艱巨而重要的工作。數十年里,貴州出現不少“年年扶貧仍然窮”的現象,甚至出現扶貧工作者把糧食運到貧困村,在卸車分糧時村民要求扶貧工作者支付“卸車費”、“搬運費”的現象,讓扶貧工作者感到工作難做的尷尬。
“這種輸血式的扶貧方式,讓國家投入了大量的財力,扶貧的力度卻不大,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村貧困人口的致富問題。”宋明認為“長期把農業人口捆綁在惡劣的地理環境中,只能使貧困地區和富裕地區的差距越來越大。扶貧工作應該結合農業人口轉移進行,政府要引導農民離土,離開落后的農業生產環境,把有限的資金投入到扶持工業發展和城鎮化建設中,為貧困人口離土創造條件。”
再有,由于民族傳統習慣,特別是一些偏遠的少數民族地區,居民對于市場經濟的需求很少,長期參與流通的商品主要有兩種——食鹽和銀器,食鹽是日常生活消費品,銀器則是人們身上的裝飾品。有的人家里,除過簡陋的房子,不多的糧食外,能值錢的東西就是穿戴在女人身上的銀飾了。“因此,貴州省工商業經濟發展更加緩慢。”宋明告訴本刊記者,“許多少數民族朋友身上的銀飾品可能價值萬元,但卻不會想到生產投入。這種消費觀念和方式,阻礙了工商業的發展,也阻礙了當地經濟的發展。”
這或許是一個特殊的案例,但是貴州工商業總量不高卻是事實。
“貴州全省4000多萬人口,就有800多萬青壯年勞動力在外省打工。這幾百萬農村剩余勞動力,貴州沒有力量解決他們的就業問題。”謝一說,“是因為貴州工商業發展緩慢,城鎮化率太低!我省工業占比和城鎮化率低,是經濟發展慢、群眾收入低的主要原因。只有通過加快產業發展和推進城鎮化,創造更多就業崗位,使群眾能夠就地、就近充分就業、穩定就業,不斷增加收入,加快脫貧致富步伐。”
貴州省推進城鎮化帶動戰略,就是突出自然、歷史、文化和民族特色,加強城鎮體系規劃,加快建設一批各具特色的中小城鎮,形成體系完備、分工合理、特色鮮明、組合有序的城鎮體系,走具有貴州特色的山區城鎮化道路。
在本刊記者看來,在農業人口比重大、經濟總量偏低的現實背景下,貴州的城鎮化之路,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