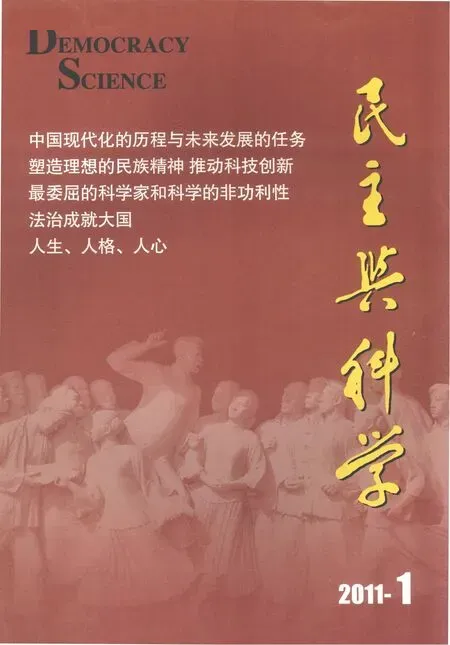值得商榷的“兩個車輪”理論
■王長樂
值得商榷的“兩個車輪”理論
■王長樂
火熱于去年三月的“大學去行政化”爭論,隨著溫家寶總理的“大學不應該有行政級別”的表態,以及大學“要逐步地去行政化”被寫入《教育發展規劃綱要》,而漸漸地歸于平息,并且變得似乎不成問題。然而,參與討論的雙方都明白,在大學是否去行政化的問題上,其實并沒有形成共識,一些圍繞去行政化問題的意見,還經常地見諸報端。而關于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同為大學活動“兩個車輪”的理論(《科學時報》2010 年8 月27 日A1 版),可以說就是這種現象的一個表現。
按照這種“兩個車輪”理論的解釋,大學中的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為承載大學活動的左右兩個車輪,共同支撐著大學中的所有活動。這“兩個車輪”作為推動大學前進的基本力量,既是大學活動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也是可以相互協作而形成合力的。
從字面上看,這個理論無疑是兩全其美的,其中既兼顧了人們呼吁大學去行政化、重建大學學術權力的要求,又肯定了行政權力的作用,安撫了大學中的行政人員,為其繼續發揮作用提供了理論上的合法性。同時,立足我國大學的現實體制和文化,可見這種理論是符合大學實際的,具有實踐和制度的基礎,不失為一種推進大學進步的漸進思路。
但作者對該理論的疑問是,這樣的制度安排真的能解決大學中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之間的矛盾嗎?能解決現實大學制度中隱含的教師權利和尊嚴缺失、進而導致的教師教育信仰缺失、教育責任感淡薄等問題嗎?能使大學脫離行政化(也有人說是官僚化)的窠臼,成為名副其實的大學,并產生大學應有的引領社會文明和進步的影響和意義嗎?作者對此深表懷疑。因為:
第一,大學歷來是被稱為研究高深學問的學術機構和專門培養高層次人才的教育機構的,其學術權力來源于只有大學教師才有能力和資格承擔培養學生和從事學術研究活動的性質。所以,大學中的學術權力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權力,它源于大學的本質和宗旨,是始終存在于大學之中的。那么,我國現實大學中的行政權力是從哪兒來的,它的源泉在哪里?其在大學中存在的條件是什么?它有條件與學術權力相提并論嗎?而將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相提并論,大學中的行政化現象能夠消除嗎?
第二,從世界大學的歷史上看,大學內部的行政權力并非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從學術活動中衍生出的行政性工作中發展出來的。一方面,行政權力是必須用來為學術活動服務的。另一方面,行政權力相對于學術權力而言,是處于附屬位置的。這種行政權力形態不僅是國外大學中的現實,而且也是我國早期大學中的現實。若以“兩個車輪”理論的邏輯來設計大學中的權力結構,那是否可以說大學中所需要的附屬工作,都可以上升到大學主導因素的位置,并因此再衍生出一些可以與學術權力相提并論的其他權力呢?比如:后勤權力,工會權力,婦女權力等。
第三,如果說將大學中的兩種權力比喻為“兩個車輪”,意在說明其可以使大學行進平穩的話,那么為其安上四個車輪豈不是更平穩。比如:是否也可以將一些大學總結的“黨委領導、校長治校、教授治學、民主管理”原則,概括為“四個車輪”理論呢?這樣的說法雖然符合政治正確的要求,在政治上是安全的,但問題是這樣的理論對大學的實際進步有意義嗎?如果這樣的機制有效的話,人們還何必要提出“去行政化”的問題呢?溫總理又何必說“要創造條件讓教育家辦學”的意見呢?因為人們嚴厲批評和詬病的大學行政化現象,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產生,并引發了大學中的種種問題的。另外,任何比喻都是有局限性的。那如果將大學比作一個人,是否就能說“人可以有(學術權力和行政權力)兩個心臟”呢?
第四,在國外的大學中,有“教授就是大學”的說法;在我國早期大學中,有“大學者,非謂大樓而大師也”的說法;也有“大學風氣的好壞,全在于教授的質量”的說法。這些說法都說明教授是大學活動的核心,而保證這種教授作用的學術權力,也自然是大學中的核心。如果說行政權力可以與學術權力相提并論的話,那么是否也可以說:“行政人員——抑或校長、院長、處長就是大學”呢?當然,這里所說的校長是指那些作為行政權力代表的校長,亦即是由行政機構按照自己的標準所任命的校長,而不是作為學術權力代表的校長,亦即是由教授會選舉或董事會聘任的校長。
顯而易見,這些問題是“兩個車輪”理論所難以回答的,但也是大學體制理論研究中應該解決的問題。而對于大學中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的關系問題,作者的思考是這樣的:
一是大學活動是一種系統性活動,不僅需要基礎性的教學和研究工作,而且需要為教學和研究服務的行政工作和后勤工作。但這些行政工作和后勤工作,只能是為了幫助教學和研究工作做得更好而提供的服務性工作,而不能“反客為主”地成為大學中的主導性工作,它們在大學中是處于附屬地位的,不具備與教學、科研相提并論的條件。另外,大學中的行政工作在開展時需要一定的組織及規范,并在保證這些組織和規范時可能會衍生出一些行政權力,這是一種客觀現象。但是這些行政權力只能是在行政活動的范圍內發揮作用的,而不能擴展到大學的所有領域。這句話更明白一點說,就是行政權力只是對行政工作有效的,而不能擴大到學術領域。這與作為大學基礎的學術權力在適用范圍上是不一樣的,因而二者是不能相提并論的。
二是從世界大學的歷史來看,大學首先是作為一個教育和學術機構而延續和發展的,主導大學發展和變化的核心因素無疑是大學中的教育和學術活動。而大學中的行政工作及后勤工作,都是在大學教育及學術活動發展過程中派生出來的。事實上,無論是在國外的大學中,還是在我國早期的大學中,大學中的許多行政工作都是由教師兼任的。而我國目前大學中的許多專職行政崗位,在那時也是由教師或學生兼任的。比如:系主任、教學秘書、教務處長等。這表明在一般意義上,學術活動是可以脫離行政工作而獨立完成的。但行政工作則不同,如果脫離了學術活動,就沒有了存在的意義。所以,大學中的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決定與決定于、主體與服務的關系,而不是有人所解釋的相互依存、相互協作的關系。試想:學術權力怎么去“協作”行政權力?難道要教師和學生去迎合行政組織及其官員的要求嗎?這種現象雖然在現實的大學中普遍存在,但并非“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一方面,這正是大學的問題所在。另一方面,大學去行政化所欲消除的,也正是這種現象。另外,一個簡單的常識是:學術人員可以沒有障礙地去從事行政工作(這在社會學上被稱為順向轉移,比如:中國傳統的“學而優則仕”,以及現在的許多專業人員擔任行政領導職務),但是,行政人員能夠沒有障礙地來從事專業工作(這在社會學上被稱為逆向轉移)嗎?所以,在以往的對大學活動的描述中,人們常說要搞好教學、科研兩個核心工作,而沒有聽說哪個大學說要搞好教學、科研、行政三個中心工作。事實上,許多專職的行政工作人員在對待自己的工作時,都懷有一種謙遜的心態。因為他們明白自己的工作與教師的工作是有區別的,亦即教師的工作是專業性的,自己的工作是服務性的。他們基本上都不會認為自己的工作可以與教師的工作相提并論。這并非是一種人格歧視,而是一種由于工作性質衍生的差異現象。因為教師所得到的較多的榮譽和尊重,是以其較多的心智付出及高度的責任心為前提的。而仔細研究目前大學中的行政化現象,會發現問題并不是出在一般的行政工作人員身上,而是出在行政官員身上。是他們中一些人對行政權力的濫用及以權謀私行為,才導致了大學權力腐敗、學術腐敗等現象的產生和泛濫,導致了大學風氣的墮落和庸俗。在如何擺正行政權力的位置上,梅怡琦先生為后世樹立了良好的典范,他常說:“我就是為教授搬凳子的。”(梅先生絕不會說:“我是為行政人員搬凳子的。”)以梅先生的聲望和地位尚如此說、如此做,那我們今天的一些由于各種原因而掌握了大學行政權力的人,有什么資格對教師頤指氣使呢?
三是在作者所閱讀到的關于世界大學歷史的文獻中,并未發現世界大學內部的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時而相互搏弈,時而相互協作”的史實。與此相反,倒是看到過關于“學生的大學”、“教師的大學”的記錄。而在這些大學中,行政工作基本上都是由學生和教師兼任的,因而根本不存在行政權力的概念。同時,一部世界大學史,實際上就是一部大學教授們主導或決定大學命運的歷史。因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拉比教授關于“教授就是大學”的聲明,其所以能夠在世界范圍內廣泛流傳,可見其是得到世界大學同行們的贊許和認同的。而綜觀一些作為大學美談的故事,比如:哈佛大學解聘校長薩默斯、拒絕授予里根總統榮譽博士學位等決定;牛津大學拒絕阿拉伯商人巨額捐款、拒絕邀請布萊爾首相參加校慶典禮等決定,哪個不是由教師們(教授會)作出的?又有哪一個是由行政人員作出的?這表明在世界大學的發展過程中,學術權力是起主導作用的,行政權力根本不具備與其相提并論的條件。
四是在我國目前的教育研究語境中,顯然存在著兩種內涵的行政權力概念。一種如作者前面所述,是產生于大學內部的行政權力。這種行政權力是由大學中的學術權力派生出來的,在大學的權力結構中處于“下位”的位置,是為學術權力服務的。一種是“兩個車輪”理論主張者所說的行政權力,這種行政權力是由我國大學體制產生的特有現象,它不是發源于大學內部,而是來源于大學外部的政治機構的授受,是代表社會的政治機構來管理大學的,對大學擁有指揮、控制、主導、監督等權力。這種行政權力的表現雖然在大學內部,但其權力的源泉卻是在大學外部,是大學沒有能力左右的。因而不能看成是大學的內部權力,并且與純粹是大學內部權力的學術權力并列來討論問題。而“兩個車輪”理論的主張者顯然是混淆了這兩種行政權力的概念,將后一種行政權力當作前一種行政權力來看待,從而出現了一些讓人感到莫名其妙的問題。顯而易見,這個理論與將現在大學制度等同于現代大學制度一樣,是一種“我注六經”式的、對現實教育體制的巧妙詮釋。只是這種詮釋只能起到為現實體制辯護的作用,而無助于大學問題的根本解決。因為授受于大學外部政治機構的行政權力,與授受于大學內部學術意志的行政權力,在活動的價值方向上是不同的。其中,授受于大學內部學術意志的行政權力,由于是由大學中的學術權力派生的,因而是沒有自己獨立的價值方向的,學術活動的方向就是它們的方向,為大學中的學術活動服務就是它們的職責。而授受于大學外部政治機構的行政權力則不同,它是有明確的價值方向和目的的,這個目的就是要大學成為為政治服務的工具,以滿足政治的各種需要。在這種大學行政權力形態下,大學的本質必須是政治性的,政治的目的就是大學的目的,政治的規則就是大學的規則,政治的邏輯就是大學的邏輯。在這種行政權力背景下,大學中的權力結構是反過來的,亦即不是學術權力決定行政權力,而是行政權力決定學術權力。學術權力的大小多少,則全在于行政權力的讓渡,與此同時,學術權力也是根本不可能有與行政權力相提并論的資格和條件的。在這樣的大學管理邏輯中,大學中的教學和科研活動,將不能是一種自然而然、平心靜氣、寧靜致遠式的活動,而可能是在各種“規劃”或“工程”驅趕下(還有物質或金錢引誘)的“大干快上”、“做大做強”、“跨越式發展”活動。而在這種環境和氛圍下,不進行學術造假很難,出現學術造假則是自然的。而這也正是人們呼吁大學去行政化的原因。
與政府管理大學的不斷要大學出政績的思路不同,世界大學的歷史表明:大學不僅注重革新,更注重對傳統的繼承。許多世界著名大學的特點,不是花樣翻新的變化,而是多少年如一日的對大學理念的堅守,是沉穩、寧靜、淡薄、堅韌地對傳統的維護,是對規律、規則的近乎教徒式的敬畏和尊重。試看歷屆大學校長論壇上國外著名大學校長的發言,幾乎很少有人談自己大學的規劃,而談的都是大學的理念,大學的普遍原則。因為他們明白,大學只有在辦學理念清晰、教育目的合理的情況下,才能真正實現其價值和意義。而在大學理念模糊、教育是非不清的情況下,任何技術層次的努力,都無法改變其整體上落后的命運。而我國大學的問題,或許正在于此。
我國大學的泊來品性質,使其存在著許多先天不足。而這些先天不足所導致的許多誤區和陷阱,使我們常常在錯誤的路上越走越遠,以非為是且不自知。而對人們長期沉迷其中,但不甚了了的一些虛假理論進行澄清,撥亂反正,是教育研究的職責,也是本文寫作的動因。
(作者單位:江蘇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