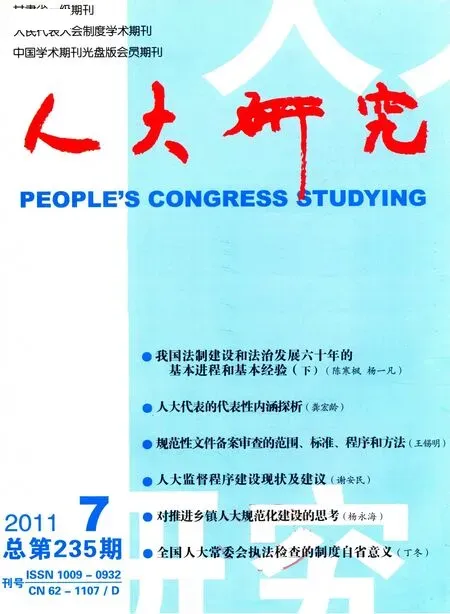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的制度自省意義
丁冬
法律之表達與實踐的背離見諸中國法律的諸多領域,在相當程度上影響著法律的實踐和法治的公信力。
一、沒有發展的增長——法律之表達與實踐的背離
201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如期形成[1],涵蓋社會關系各個方面的法律部門已經齊全,各法律部門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經制定,相應的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比較完備,法律體系內部總體做到科學和諧統一。
從數量觀之,法律法規及其配套性立法不可謂不蔚為壯觀,到2010年底,中國已制定現行有效法律236件、行政法規690多件、地方性法規8600多件。從法律條文的表達觀之,諸多法律的立法理念、立法技術以及法條本身不可謂不先進。以勞動者權利保障領域的法律法規為例,新出臺的《勞動合同法》從立法理念到具體的法律條文無不反映其對處于相對弱勢一方的勞動者的權利的保障,國家諸多保障勞動者權利的政策也相繼出臺。
客觀論之,這些法律表達的背后,確實體現了立法者基于利益衡量的思維對勞動者權利保護的重視。然而,一個不可忽視的現實是這些法律的表達與實踐之間存在的背離現象。《勞動合同法》出臺之前學者之間就該法的立法理念究竟應該是“高標準”的“錦上添花”還是“廣覆蓋”的“雪中送炭”等問題就已經存在很大爭論[2]。《勞動合同法》出臺之后,各企業為了規避法律而頻頻出招,學者就中國非正規經濟的研究,更是深刻揭示了非正規經濟發展模式下,勞動者權利保護領域法律之表達與實踐之間存在的極大背離[3]。
這種表達與實踐的背離,反映在日常生活中,主要體現在民眾的一種普遍觀感:為什么法律越來越多,權利和秩序卻沒有相應的正比例發展?貪瀆問題、食品藥品安全問題、勞動者權利保護問題,諸此等等,無不反映了法律應對的乏力。一方面是法律法規的日趨健全,一方面卻是民眾普遍渴求的秩序感和安全感無法得到很好的滿足。這種矛盾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著民眾對法治和法律的信任,亟待加以認真對待和反思。
法律表達的“華美”是否僅僅是一種空中樓閣式的純粹數量累積的“沒有發展的增長”?要否棄對法律的這種詰難,則不得不對法律的實踐問題作出更為深入的思索。從“立法中心主義”向“司法中心主義”的轉向,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學界對法律實踐問題的高度關注。盡管我們不能完全否認這種轉向的存在,但這并不意味著立法者在法律實踐問題上只是一種“他者”的角色。相反,立法者通過架設監督法律實踐的管道,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和把握法律實踐的問題,為法律之表達與實踐的背離尋求彌合的解決之道。
二、執法檢查:法律之表達與實踐的彌合之道
執法檢查作為全國人大常委會最常規、最穩定、最有影響的監督手段,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發展經過了較為繁復的過程,這一過程伴隨著對憲法就全國人大常委會職權授權范圍的解釋,以及從執法檢查初步確立到成熟實踐的多問題解決[4]。2006年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審議通過,2007年1月1日正式實施的監督法以專章的形式正式確認了各級人大常委會對“法律法規實施情況”進行檢查的權力。自此,執法檢查權具備了明確的法律依據。
霍姆斯曾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邏輯,而在于經驗。法律的實踐是法律生命力之所在。如法律不能得到切實地實踐,則正式通過的法律也無異于一份草稿。受限于有限理性思維的限制和知識獲取機制上無可避免的短板缺陷,一部法律無論制定得如何完備都無法窮盡現實的復雜性。因此,甚至有人斷言,任何一部法律從其制定公布的那天起就已經遠遠落后于時代發展的步伐了。這也就意味著法律的表達與實踐總是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背離,眾所周知的“犯罪黑數”或“違法黑數”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承認這種背離的存在,是避免陷入“法律萬能主義”窠臼的重要保障。但也必須同時注意,這并不構成認可法律之表達與實踐的背離總是能夠容忍的充分必要條件。須知,一個正常的權利和秩序場域的維護,需要法律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能夠發揮其最低限度的作用。否則,我們就可以說法律之表達與實踐的背離達到了不可容忍的限度。在法律之表達與實踐的完美契合和法律之表達與實踐的不可容忍的背離之間,存在著廣闊的第三領域。執法檢查作為彌合法律之表達與實踐背離的解決之道,其意義就在于盡量地將這種第三領域的范圍朝向實現法律之表達與實踐的完美契合這一方向進行限縮。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行使執法檢查權,對重點領域的法律實踐情況進行檢查、評估,并形成報告,不僅能夠通過近距離的觀察,對法律的實踐情況進行把握;更對發現法律實踐過程存在的問題,并進一步提出整改意見,乃至為后續的立法、修法提供參考和借鑒。執法檢查,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立法者傾聽和了解作為執法者的政府、司法者的法院在實踐中是如何思考的一條重要管道,可以在相當程度上舒緩立法者決策信息不周全所帶來的立法疏漏。通過執法檢查,分別從立法者、執法者、司法者的不同層面,為彌合法律之表達與實踐的背離尋求解決之道。
在我國食品安全事件頻發,食品安全公信力普遍不高的當下[5],全國人大常委會于近期開展的《食品安全法》執法檢查工作,無疑具有更為應時的意義。
三、《食品安全法》執法檢查的制度自省意義
(一)食品安全領域的基本情況
1.食品安全法律的歷史沿革與現狀
我國食品衛生領域的法律規制,先后經歷了《食品衛生管理實行條例》(1964),《食品衛生法(試行)》(1982),《食品衛生法》(1995)的幾度變遷。這些法律法規的出臺,在保障我國食品衛生、防控食源性疾病、保障民眾身體健康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因三鹿三聚氰胺事件而出臺的《食品安全法》(2009)更可以看做是“經由個案來認識和解決難題”以實現制度之“鳳凰涅槃”的一個結果[6],是我國在保障食品質量方面的最新努力。從“衛生”到“安全”的轉變,絕不僅僅是簡單的語詞置換,其背后反映的乃是我國食品安全領域立法理念的重大轉變:從農田到餐桌的全程監管理念、食品安全風險檢測與評估理念、加大違法成本的法經濟學理念、社會力量參與食品安全制衡的多主體參與理念,無不在《食品安全法》具體而微的制度設計和考量中得以體現。
《食品安全法》的出臺,集中反映出立法者及時回應我國經濟社會變遷對食品安全領域法律規制的新挑戰、新要求,及時回應民生、關注民生的積極舉動。從體制、機制上就食品安全領域法律規制中存在的新問題作了重大的創新和調整。毋庸置疑,這些努力都是值得肯定和認可的。與此同時,此次《食品安全法》的重大修訂和制度革新也對政府相關監管機構在體制、機制上與《食品安全法》的銜接,對配套性立法措施的及時出臺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因此,對《食品安全法》的實踐情況作出檢查和評估,及時回饋各項制度的落實和革新情況,無疑具有制度上的自省意義。
首先,央地各有關部門紛紛出臺《食品安全法》的貫徹落實意見、通知、具體舉措,為及時發現執法中的問題、累計經驗提供了有力基礎。自《食品安全法》頒布以來,國務院及時出臺了《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全國工商系統共出動執法人員683萬人次,檢查食品經營戶1507萬戶次,檢查批發市場、集貿市場等各類市場31萬個次,查處食品違法案件2.1萬件。不少地方政府也從學習培訓、工作調研、經費與編制、體制銜接等諸方面開展對《食品安全法》的貫徹落實。
其次,《食品安全法》中制度革新舉措的配套性支撐工作逐步展開。《食品安全法》中明確規定了食品安全風險監測與評估制度、統一的食品安全國家標準、食品召回制度、食品安全事故處理等創新性制度,這些制度的落實需要大量的配套性工作以完成支撐。自《食品安全法》頒布以來,衛生部成立了第一屆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審評委員會,會同有關部門完成乳品安全標準清理整合工作,開展食品中農獸藥殘留、有毒有害物、致病微生物、真菌毒素的限量標準,及食品添加劑使用標準等基礎標準整合工作,成立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專家委員會,開展食品安全的風險評估工作。這些工作的逐步推行,為《食品安全法》的具體貫徹落實提供了必要的支撐性基礎。
第三,《食品安全法》頒行,消費者維權意識和信心進一步增強。《食品安全法》基于法經濟學層面的考量,加大了對食品生產經營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特別規定了懲罰性賠償責任和民事責任優先賠償原則。通過這些規定,為消費者權益的維護提供了更為堅實的法律依據,同時也彌補了消費者單純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來維護權益時請求權基礎不足的問題。實踐顯示,自《食品安全法》施行以來,消費者依據該法要求商家支付10倍懲罰性賠償,維護自身權益的案件逐步增多。
2.監管機構與主要職責
我國食品安全監管體制一直以來奉行的是基于各部門分工的分段監管體制。2004年《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食品安全工作的決定》確立了食品安全監管按照“種植養殖、生產加工、市場流通、餐飲消費”四個環節分別由一個部門加以監管的基本監管體制。然而,三聚氰胺等事件的發生表明,這種分段監管模式雖然具有理想狀態下的積極作用,但一旦具體到實踐過程中,就會發現食品從原材料到加工生產再到流通消費環節,并不是一個單線條的線性過程。相反,這一過程中的各個環節之間可能存在一個反向滲透的過程。人為地割裂這一過程,再加上分段監管職責存在的交叉與空白地帶,很容易發生如三聚氰胺事件后各部門相互推諉的現象。
因此,《食品安全法》專門規定國務院應設立食品安全委員會,并賦予衛生食品安全綜合協調的職責。根據《國務院關于設立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的通知》,食品安全委員會的定位為“國務院食品安全工作的高層次議事協調機構”,負責“分析食品安全形勢,研究部署、統籌指導食品安全工作;提出食品安全監管的重大政策措施;督促落實食品安全監管責任”[7]。此舉的目的即在于彌補分段監管模式的不足。因此,目前我國的食品安全監管體制可以稱為“有協調的分段監管體制”。
(二)《食品安全法》執法檢查的制度自省意義
《食品安全法》自頒布施行以來,與食品安全有關的各項工作在逐步有序改進和加強的同時,仍需要有進一步的調整和強化:許多革新性條款的配套性具體實施細則還需要進一步制定,食品安全的風險監測與評估、食品安全國家標準的統一制定都還處于初級階段。因此,明確《食品安全法》實踐中仍存在的不足,與了解其所取得的成就相比,在全面落實《食品安全法》的意義層面上,其制度自省意義更為明顯。
一是“從農田到餐桌”的全過程、無縫隙監管制度,仍有進一步理順之必要。全過程監管制度的實現依賴于食品安全監管部門之間明確分工的同時,各監管分段之間能有效地銜接和溝通。而三聚氰胺事件、沈陽毒豆芽事件等眾多事件發生后,所暴露出的各監管部門之間就自身職責權限的不同解讀所造成的監管灰色或空白地帶,無疑說明我國食品安全監管體制離“從農田到餐桌”的無縫監管相距甚遠。同時,統一的食品安全監管信息系統尚未建立,監管信息分散于各個部門之間,形成了壟斷化、封閉化、部門化的信息保有體制,也不利于食品安全監管的全過程展開。好在此次《食品安全法》通過第一百零三條為我國食品監督管理體制的革新留下了足夠的空間:“國務院根據實際需要,可以對食品安全監督管理體制作出調整。”因此,可以考慮的改進途徑有:根據現行立法確定的監管模式,在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的建制、職能上,作出積極嘗試,賦予其更多的實質管理權限,同時借鑒美國依食品種類而非食品生產經營階段來分別監管的模式,以規避分段監管的不足;另外的途徑則是對現行的監管體制作較大革新,借鑒加拿大、英國、日本等國的經驗,將我國各部門的食品監管職能進行整合,由統一的機構加以行使。上海世博會期間所確立的“由食藥監局為主,多部門參與的世博食品保障機制”就是對我國食品安全監管體制進行大膽摸索的典型例證。這種變分段監管為一體化監管的實踐,和上海世博園區未發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的現實,在一定意義上說明一體化監管相較分段監管的優勢所在[8]。
二是,配套性法規、標準、機制等《食品安全法》貫徹落實支撐體系的建立和完善有待作進一步的推動。《食品安全法》規定的許多制度性革新措施,需要相應的配套體系支撐作為施行的基礎。目前在食品與食品添加劑生產許可、保健食品監管、食品標簽等方面,尚缺乏統一翔實的規定作為操作指南;食品安全標準的清理、整合工作也需要進一步加強,盡可能做大安全標準的涵蓋周延;食品安全的風險預警體系構建尚處于初步探索階段。如何通過地方配套性立法來進一步推進相關措施的細化和實施,成為《食品安全法》實踐的重中之重。
三是,市場的無限性與監管的有限性矛盾亟待加以解決。與藥品行業相比,食品行業準入門檻更低,食品生產加工企業、零售企業、餐飲企業為數眾多,行業從業人員數量多、素質參差不齊。這對監管機關而言,其工作難度無疑更大。上海有色饅頭事件所揭示的一個問題就是對于小作坊的監管缺位與乏力。與小作坊類似,食品流動攤點、小型餐飲店等等,都存在類似監管難題。實際上,無論食品還是藥品,抑或其他行業領域,囿于行政成本的限制,執法力量的總量不可能無限制增長。以國家藥品安全“十二五”規劃的核心指標研究為例,每百萬人口監管人員的數量擬定為2011年53人,2012年56人,2013年58人,2014年60人,2015年60人。這一指標仍屬于期望結構性指標,即要根據當地經濟發展、行業發展等多重因素做不同修正[9]。由此可以看出,監管力量增長的有限性。如何化解這一監管難題,需要在實踐中加以認真思量。一定意義上,食品安全的保障是一個社會管理的課題,需要社會力量的多主體參與和制衡作用的發揮,需要進一步提升。食品安全的保障,固然需要強化政府的責任意識,但諸如消費者協會、食品行業協會、新聞媒體、科研機構等社會團體、組織,以及消費者個人的積極參與也必不可少。食品安全的保障,涉及生產、流動、經營等諸方面問題,遠非政府的單獨力量所能完全掌控。如何有效地激發社會力量對食品安全問題的關注和參與,是我國食品安全問題能否獲得有效解決的重要環節。《食品安全法》對社會力量參與食品安全維護也秉持了歡迎和鼓勵的態度。在具體操作層面,則關鍵在于如何有效地為食品安全的公眾參與提供暢通的渠道和必要的制度支持。這些都是我國在制定食品安全戰略時應予認真考慮的。
四、結語
執法檢查作為立法者因應法律之表達與實踐背離的舉措,發揮著其制度自省的重要意義。這一點對《食品安全法》而言尤為重要。當下的中國社會越來越具有貝克“風險社會”理論意義上的“風險社會”的癥候[10]。“風險社會”的陰影投向食品藥品安全領域,主要表現為食品藥品侵權事件多發及由此引起的群體事件風險。學者對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近的集團訴訟實踐的研究顯示:集團訴訟的一個顯著趨勢是越來越多地適用于一系列經常發生的情形下的損害賠償請求:醫療產品、醫療過失索賠;經濟損失索賠;消費者索賠;煙草產品索賠;環境問題索賠;災難與事故索賠;不動產糾紛;職業健康以及其他與職業相關的訴求;對政府或其他機構的索賠[11]。概括言之,主要發生在大規模事故、環境侵害事故、缺陷產品事故為代表的大規模的侵權領域。
與此相似,我國近來的大規模侵權事件也呈現出多發的態勢,涉及食品質量缺陷侵權、醫療產品缺陷侵權、房屋拆遷侵權、職業安全侵權等多領域。近年來出現的比較典型的蘇丹紅事件、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毒豆芽事件、染色饅頭事件等無不反映出“風險社會”的征候。一面是食品安全立法的逐步完善和出臺,一面是食品安全事件頻頻通過媒體曝光,風險社會下食品安全的法制應對成為一個不得不認真面對的問題。
在風險社會的語境下,通過對《食品安全法》實踐情況的執法檢查,作為立法者的人大常委會能夠進一步明確《食品安全法》在實踐過程中的短板所在,對于食品安全立法的完善作用助益良多。需要加以注意的是,在執法檢查的過程中如何把《食品安全法》實踐情況準確真實地反映出來,是仍需從執法檢查手段和舉措等方面加以認真思量的另一個重要問題,也事關執法檢查的最終效果。
注釋:
[1]參見顧雷鳴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載《新華日報》2011年3月11日。
[2]參見董保華:《錦上添花抑或雪中送炭——析〈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草案)〉的基本定位》,載《法商研究》2006年第3期。
[3]參見黃宗智:《中國被忽視的非正規經濟:現實與理論》,載《開放時代》2009年第2期。
[4]參見林彥:《從自我創設,到政治慣例,到法定權力——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權的確立過程》,載《清華法學》2009年第3卷。該文對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權的確立歷史脈絡進行了詳細的梳理。
[5]中國社科院2011年5月4日發布的《社會心態藍皮書:2011年中國社會心態研究報告》顯示,根據對京滬穗三地居民的調查,食品、藥品行業社會信任危機嚴重,屬于“基本不信任”的范疇。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食品藥品行業的公信力缺失問題。參見,http://news.hexun.com/2011-05-04/129271500.html,2011年5月7日訪問。
[6]轉引自【德】亞圖·考夫曼:《正義理論——由難題史觀察》,劉幸義譯,載其主頁http://blog.yam.com/lawliu,2011年5月7日訪問。經由個案來實現制度涅槃的例證不勝枚舉,比如確立美國違憲審查機制的馬伯里訴麥迪遜案、2003年廢除施行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的孫志剛事件、促動房屋征收拆遷補償條例修訂的拆遷事件等等。
[7]參見《國務院關于設立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的通知》,國發(2010)6號。
[8]參見世博食品安全保障評估課題研究組:《上海世博會食品安全保障及其后效應評估研究》,載上海市食品藥品安全研究中心編:《食品藥品安全與監管政策研究報告(201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版。
[9]參見江濱等:《國家藥品安全“十二五規劃”藥品監管核心指標研究》,載上海市食品藥品安全研究中心編:《食品藥品安全政策研究》2011年第1期。
[10]參見【德】烏爾里希·貝克:《風險社會》,何博聞譯,譯林出版社2004年版。
[11]See Rachel P Mulheron,the Class Action in Common Law System: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Hart Publishing,2006,pp.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