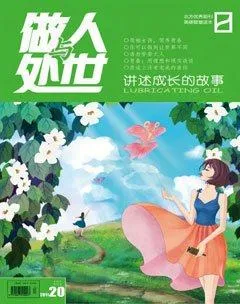人書俱老
近日看書法名帖。一看再看天下行書前三甲,第一為王羲之的《蘭亭序》,二為顏真卿的《祭侄文稿》,三為蘇軾的《寒食帖》。
正逢雨季,陰雨連綿。一個人臥于陽臺的紅沙發里,整個人陷入一場與書法的愛戀與糾纏里。這哪里是書法?分明是人生。三幅行書均為草稿,據說他們也試圖再寫,把那草稿上的瑕疵和涂抹去掉,居然再也不能。
真真是絕品都難以復制。那是怎樣的心情寫就?蘭亭的陽春三月,文人聚集在一起寫詩畫畫,雅囑王羲之為序。他喝到半醉,一揮而就,文與字都美到不似人間。雖然后來沒了真跡,但是,連復制品都讓人嘆為觀止。孫過庭在《書譜》中總結:通會之際,人書俱老。王羲之的老,是回到最初、開始,回到書法的本源——書寫,原來是為了記錄生活之美。
弘一法師圓寂前寫就的四字,也還原到了寫字的最初,徹底斷了人間的煙火氣。出家之后,他拒絕戲曲、音樂、繪畫……所有與文藝有關的事情,他都拒絕。這其中,包括書法。
后來,有人規勸:抄寫經書可以度人。于是他抄經度世,字體線條平靜安詳。所有的書法家都力求表現自己的個性,而他,隱藏起所有個性,只為抄經度人、度世。回歸到書法本身,回歸到字的認真踏實。那最后四字“悲喜交集”,早就失去審美的緯度與經度,人書俱老是境界,到了這里,他連人書俱老都沒有了。
有人曾在曉云法師處看到法師的刺血經書,血跡極淡,卻如金石刻痕,縷縷都游于心上。驚震的同時,只有心酸與慈悲。
初看顏真卿的《祭侄文稿》,如鬼畫符,行、草、隸都摻雜,一字字全是疼痛。此篇上升為精神領域的圣經,完全與書法無關,情緒四處蔓延。這是顏真卿嗎?這是,這正是。顏體的大氣和闊麗,顏體的規范和平直全然皆無。你只看到一個人在寫、在哭、在疼——書法真正的意義是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再看《寒食帖》。彼時蘇軾45歲,幾次被貶,幾經磨難——他書寫時還需要炫耀華麗嗎?還需要書風嗎?還需要矯情嗎?夜風苦雨,陰雨連綿。“今年又苦雨,兩月秋蕭瑟。臥聞海棠花,泥污燕支雪。”連眼淚都覺得多余。一筆寫下來,心就老了。其實,提筆的一剎那,就老了。
流放歲月,此樣寒食節。一個人站在窗前、雨前,九死一生的命運到了高潮。人的一生,如果只經歷大富大貴和平淡從容,哪里會有人書俱老?
那么,落筆吧。因為,此中還可落淚,還可縱情地想念或者拒絕。還可以,一個人獨處的時候,與筆墨為伴,伴著雨聲、秋聲,伴著那烏鴉的叫聲,寫下這千古名帖《寒食帖》。
此中有真意,不辯也忘言。一個人內心有了格局,氣息會別樣不同。弘一法師,到最后,內心與外在完全統一,刺血寫經時,以血為墨,并不覺得疼痛。而行書前三帖,早就失去書法技巧——我們一生所要擺脫的,恰恰是技巧。技巧讓我們華麗、矯情、茫然,技巧讓我們趨之若鶩,技巧帶來利益,技巧也帶來匠氣。
人書俱老的作品,早失去技巧。
有人說長期看書法名帖可以把人看老了——如果年輕的容顏有一顆老心,那真是人生上品。早早地把自己的心收斂起來放好,也無風雨也無晴,慈悲喜舍,靜定安詳,于整個人生來說,是敬重,也是圓滿。這樣的通會之時,來得越早越好。
編輯 邱文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