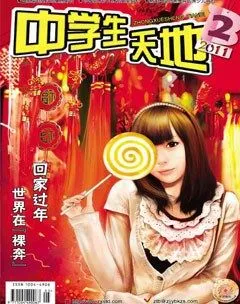青春期在美國
很少人有我這樣的經歷;而有這樣經歷的人,又很少愿意寫出來。從高中一年在美國的交換,到后來的本科、碩士以及剛開始的博士攻讀,我無時不覺得這樣的經歷應該與廣大青少年朋友們分享,為大家展現真實的世界。
剛到美國的時候,因為國內英語老師給我打下了堅實的口語基礎,生性開朗的我一下子就融入了美國社會。喜愛音樂的我,自然而然地加入了中學的合唱團。而正是在合唱團里,我遇見了蘇拉。
蘇拉是一個清純的女孩,一頭金色的卷發,藍色的眼睛,迷人的微笑卻掩蓋不了一絲淡淡的憂傷。她給我的第一印象就好似達·芬奇筆下的蒙娜麗莎。蘇拉父母離異,當時和親哥哥、母親、后爸以及同母異父的弟弟妹妹生活在一起。蘇拉很懂事,每天回家除了做功課做家務,還要照顧小弟弟和小妹妹。而每次到了合唱團,她又把美妙的歌聲帶給大家,絲毫不讓我們察覺她內心的苦楚與孤獨。也許因為她覺得我跋涉半個地球,來到這人煙稀少的地方(我當時交換在美國中北部的威斯康辛州,到處都是一望無際的農田),應該也會覺得孤獨,所以從一開始就對我無話不說。慢慢地,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
美國人有一個概念叫“Personal Bubble”,是指一個私人的空間。簡單地描述,這個空間是以自己為中心,大約一個臂展為半徑的球體。一般情況下,人們是不可以侵犯你的私人空間的。印象很深的是在教室外的走廊上,經常會聽到同學對別人大喊:“Why are you in my personal bubble?”意思就是你靠得太近了,侵犯了我的私人空間。美國的年輕人其實是很在乎這個私人空間的,所以相互之間并不會靠得太近。(大家一直說中國人排隊擠,而美國人比較講秩序,這種看法是有偏見的。很大程度上,美國人是不想讓別人進入自己的私人空間,也不想自己闖入別人的私人空間,所以有意無意地在排隊時隔開一些距離。)
而蘇拉跟我完全沒有這個“Personal Bubble”,也許她覺得我會經常想家,所以偶爾還會給我一個緊緊的擁抱。我會被邀請跟著他們全家一起出游,也會在感恩節的那天晚上去她家參加晚宴。因為這種近距離的接觸,我能夠有幸了解美國青春期少年的生活以及他們和父母的關系。
青春期總離不開“叛逆”這個字眼,溫柔的蘇拉也不例外。尤其是她看著同齡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而自己卻還要幫著家里做事,免不了有逆反心理。而美國這個崇尚自由、崇尚個體獨立的國家,父母對子女的控制能力(或者欲望)是遠遠小于中國的,父母不會正面地告誡她什么事情一定不能做或者一定得做,而是通過其他的渠道達到目的。而蘇拉家,靠的是宗教。她的母親每周都要帶她去教堂好幾次,不僅參加禱告,而且讓她成為唱詩班的主力。雖然她對父母有逆反,但因為教會活動占據了她除了上學、做家務、照顧弟弟妹妹以外的主要時間之后,她就沒有機會去別的地方“闖禍”了。我因為常被請去教堂拉小提琴,也見識過不少次宗教儀式,在那里遇到的青年人幾乎都有這樣的經歷:雖然他們有著年輕人的個性、沖動與叛逆,但因為教會活動比較多,他們沒有時間、沒有精力、也沒有心思去做父母不希望他們做的事情了。
說到青春期性教育,美國高中的教學是一整套的。女孩們不僅要學習生理知識,還有專門的課教她們如何做一個好媽媽。學期開始,每一個女生都會領到一個電子模擬嬰兒,簡直就跟真的一樣:會哭、會笑,需要哄,需要抱,定期要喂奶,否則就會哇哇大叫,幾乎一刻也不肯停歇。經常出現的情況是,女生抱著電子嬰兒去上別的課,因為照顧孩子本身就是全天候的責任。其他課的老師也都是很理解的。這種教育模式的好處在于,不僅讓女孩們學會了照顧孩子的技巧,也讓她們感受到了撫養孩子需要很強的責任心與毅力,這樣就會讓女生們更注意自己的身體,不會輕易地懷孕,生孩子。
與女生相比,美國高中的男生又是怎么想的呢?其實美國中學里,體育是很狂熱的,男生更多的還是和男生在一起,他們需要花很多時間在學校(校際)的各項體育賽事上。男女同學之間平時并不曖昧,并不濫情。即便是有了女朋友的男生,在我看來,也都是毫無疑問地把自己的“弟兄”放在更重要的位置的。是否有女朋友對美國中學生來說,僅僅是一種生活狀態,可有可無,甚至是誰、自己究竟是否喜歡都并不十分重要。美國人的戀愛本身就是很純粹的加深交往的過程,如果合適就發展,如果不合適就分手,這是很自然的,并沒有任何家庭、社會方面的壓力——除非家里知道了孩子可能和不良青年在交往,那會提醒一下,也并不會過多干涉。所以校園里的實際情況就是,絕大多數時候,大家都是有男女朋友的,但誰是誰的男女朋友有的時候是分不清的,尤其是消息慢半拍的同學,經常會跟不上變化的節奏。
偶爾有一天,我和一個同班的男同學網聊到很晚,順便聊了下班里的女同學。他說的讓我大吃一驚。他說據他所知,班里的女生多數都已有了性經歷,有的還很豐富。當我問到蘇拉的情況的時候,那個同學告訴我說,她也有過,只是比較少。我想,她一定是被束縛得透不過氣來,然后叛逆心爆發了吧。在我接觸的美國高中生里,即使有過性經歷,社會也不會給他們戴上道德的枷鎖。有一件事情我印象深刻:學校里有個女生不小心懷孕了,老師家長都訓斥她,但不是因為性行為本身,而是因為他們愚蠢到沒有采取有效的避孕措施。
當然,在美國不同的家庭,對于青春期的萌動也有不同的處理方式。和中國比起來可以總結為疏導為主,預防為輔。疏導是相對于壓迫、阻礙而言的。美國人一般十幾歲就有了性經歷,而第一次往往都是某個人開了一個派對,結束之后留宿發生的。絕大多數時候父母也在家,但他們不會去阻撓——父母親自己也都是這樣過來的,因此就不會去苛求孩子了。
大家聽著不要覺得美國的派對多么狂野、放蕩。其實這和派對主題、參加人員等很多因素都是分不開的,并不是所有派對都一樣。那年我的生日,房東媽媽給我辦了一個大派對,蘇拉自然而然來參加了。大家很開心地玩到9點多,然后紛紛告辭了。本以為美國高中生的派對大家會通宵盡興的,所以伙伴紛紛離去我也有些依依不舍(后來大學我自己開Party才知道原來這都是因人而異、因地而異的)。等其余的人都走完了,她卻留了下來陪我玩。我們下下棋、打打牌,順便聊聊天。她終于忍不住跟我說,她呆在這里很快樂,但一回家要面對家務和弟弟妹妹就很不開心。她很渴望有自己的生活,但是掙脫不了家庭的束縛。她很想能像我一樣去別的國家旅行,自由自在的。在我看來,美國年輕人對“家”的觀念同樣是很看重的,即使整個社會非常強調個體。
進了大學,整個氛圍就變了,新生們帶著行李來到校園,遠離了家庭,仿佛一切曾經存在的束縛都瞬間消失。美國的大學一般都要求第一年住校,哪怕家離學校不遠也得如此。于是不少人,尤其是那些之前被壓抑著的人都開始了各種豐富甚至狂亂的活動,兄弟會與姐妹會尤甚。
在美國的大學里面,有所謂的“Greek Life”,即各種各樣的兄弟會和姐妹會,會名一般都用三個希臘字母。要成為會員必須經受這個會的考驗——按要求做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 ——同時要發誓把會里的每一個同胞都當作兄弟姐妹。而這些兄弟會姐妹會之間也會有聯誼的活動,比如大家都到一個大草坪上搭帳篷睡覺,或者開狂歡派對。很典型的像“Soga Party”,就是所有人模仿古希臘人穿衣服的方式,只在身上圍塊布,然后隨著勁爆的音樂跳舞。
當然,除了這群人之外,還有一些相對保守的人,我自然屬于這一類人。而這些人也有不同于高中時期的活動。沒有了父母的敦促,學校和學生會自然成了管理學生的主體。同樣,他們還是以開導、疏通為主。比如我參加過一個學生會組織的很有趣的活動,叫“Dinner date auction”。這其實是一個慈善活動,有些志愿者主動報名成為“被拍賣的對象”,然后所有學生都可以競拍與此人共進晚餐的機會,所拍得的錢捐給慈善機構。志愿者本身肯定是帥哥靚女,因為誰都不想出現沒有人要、灰溜溜下臺的局面。有些有男朋友的女生甚至為了檢驗男朋友有多愛她,讓男朋友和別人比誰出價高。結果女生實在太受歡迎,男朋友買不起、只能眼睜睜看著她和別人去共進晚餐的事也時有發生。
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正是美國社會這種獨特的“水土”,使得美國年輕人在青春期的開放程度、獨立程度以及生活的方式、作風都與我們大不相同,他們很早就學會了要對自己負責,他們在不斷探索、不斷試錯中豐富了自己的人生經驗,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