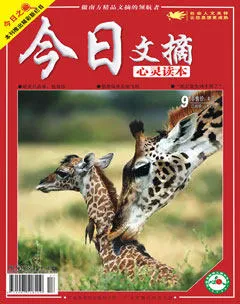皈依是一種心情
2011-12-29 00:00:00史鐵生
今日文摘
2011年17期
所謂命運,就是說。這一出“人間戲劇”需要各種各樣的角色,你只能是其中之一,不可以隨意調換。
躺在透析室的病床上,看鮮紅的血在透析器里汩汩地走——從我的身體里出來,再回到我的身體里去。那時,我仿佛聽見飛機在天上掙扎的聲音,猜想上帝的劇本里這一幕是如何編排的。
但既然這樣,又何必弄一塊石頭來作證?還是什么都不要吧,基地、墓碑、花圈、挽聯以及各種方式的追悼,什么都不要才好,讓寂靜,甚至讓遺忘,去讀那詩句。
有一回記者問到我的職業,我說是生病,業余寫一點兒東西。這不是調侃,我這48年大約有一半時間用于生病,此病未去彼病又來,成群結隊好像都相信我這身體是一處樂園。或許“鐵生”二字暗合了某種意思,至今竟也不死。
生病也是生活體驗的一種。甚或算得一項別開生面的游歷。這游歷當然有風險,但去大河上漂流就安全嗎?不同的是,漂流可以事先作些準備,生病通常猝不及防;漂流是自覺的勇猛,生病是被迫的抵抗;漂流,成敗都有一份光榮。生病卻始終不便夸耀。不過,但凡游歷總有酬報:異地他鄉增長見識、名山大川陶冶性情、激流險阻錘煉意志,生病的經驗是一步步懂得滿足。發燒了,才知道不發燒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體會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詳。剛坐上輪椅時,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豈非把人的特點搞丟了?便覺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瘡。一連數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著。才看見端坐的日子其實多么晴朗。……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