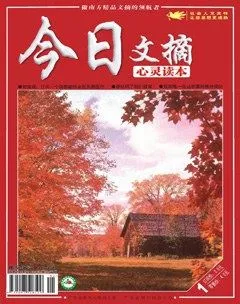懷念索拉圖吉
2011-12-29 00:00:00王龍
今日文摘
2011年1期
1984年8月,我做為一名剛下連隊的新兵,突然接到一紙命令:調動!軍令如山,我毫不猶豫,打起背包就走。去哪兒?索拉圖吉?
是的,索拉圖吉!
那是個大雨天,驟雨像無數支冷箭,能把人的軀體穿透。我裹著一件特大號的軍用雨衣,坐在卡車的后廂里,任憑卡車沿著彎彎曲曲的山路,向北,再向北。
不知過了多久,有人拍打我的肩膀:“喂,醒醒,到了。”
我慢慢地醒來,抬起頭向車外張望。其時,卡車還在開著,令人驚奇的是,車似乎不是行駛在路上,而是開在云霧之中,大團大團的濕氣迎面撲來,一瞬間就驅散我殘存的睡意。我站起來,伏在車廂邊,向著夢幻一般的雨霧大喊一聲:“喂,索拉圖吉,我來了!”
路邊的巨樹越來越密,鉆天楊挺拔俊秀,老柞樹蒼葉虬枝,紫椴樹婷婷玉立,落葉松噴香吐翠。最讓人心醉的是白樺樹,佇立于雨霧中,如出浴的處子,安詳、嫵媚、高貴。稍不留神,白樺樹就有了色彩,就有了音律,就有了觸手可及的靈感和呼之欲出的風流浪漫。
啊,這就是索拉圖吉,這就是令人畏懼被人詛咒的索拉圖吉嗎?
我在索拉圖吉駐扎下來。確切地說,我是被索拉圖吉淹沒。我在下車伊始就成了索拉圖吉的一棵樹,一塊巖石,一團自然的濃綠。
索拉圖吉是滿語,意即偏僻、荒涼。這里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早在300年前,沙皇俄國多次出兵進攻索拉圖吉,遭到中國守軍和當地百姓的頑強抵抗。前后100多年里,俄國哥薩克在索拉圖吉丟下了上千具尸體,中國軍民也有數百人為國捐軀。……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