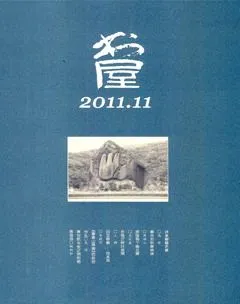閑云野鶴——何兆武
如果不是十四次印刷、發行逾十萬冊的《上學記》被文人學者爭相推薦,我不可能高攀上年逾九旬仍保持著從容適意、柔韌豁達的性格,超然如閑云野鶴、無拘無束的何兆武先生。
當時我正忙于請皓首時賢口誅筆伐大漢奸鄭孝胥的《滿洲國歌》,先生的博古通今、微言大義令我暗自喝彩。
“何老,我是您的小老鄉,想拜訪拜訪您?”我詢問到先生的住宅電話后,急不可耐地撥了過去。
“好!好!”先生的回答干脆利落。
2008年11月29日,我首次走進先生五十多平方米的蝸居。臥室兼書房內,一張小書桌,一張單人床,一堵書墻,一把轉椅,一把椅子,半墻外國音樂磁帶。如此狹小簡陋的斗室,生產出多少影響深遠的精神食糧啊!新世紀初,清華大學分給先生一套一百二十平方米的新房,先生投了棄權票:“年紀大了,搬家每張紙片都得自己細看,勞神費力太麻煩。”
先生祖籍湖南岳陽,1921年9月出生于北京的一個工程師家庭。少時就讀“京都紳商各界公立第四高等小學堂”、北京師大附中,放學后最大的興趣就是去茶館聽評書看京戲,或讀《七俠五義》、《江湖奇俠傳》和新文學作品,家里從不對他的興趣愛好進行限制。抗日戰爭爆發后,先生舉家南遷長沙,進入中央大學附中,后隨校遷入貴陽。
中央大學附中是一所準“軍事”學校,學生每天早晨被軍號叫醒,由教官帶著跑步、訓練、喊口號;晚上聽著熄燈號聲睡覺,睡前點名、唱歌、喊口號。所謂口號的最后一句是“蔣委員長萬歲”。先生覺得自由受到限制,心里有一種前所未有的苦惱,決定提前一年參加統考,逃離這座“修道院”,終于以貴州地區第二名、西南聯大土木工程系第四名的成績被錄取。
先生之所以選擇這個專業,是因為看了豐子愷先生的《西洋建筑講話》,雄偉的希臘羅馬神殿,高聳的哥特式教堂,讓先生覺得建筑非常有意思。但沒想到建筑漂亮房子前的基礎訓練無比枯燥,先生熬到第二學期熱情消失殆盡,于是決定轉系。
這時,先生摯友、后來任教哈佛大學的著名數學家和哲學家王浩先生指出兩條路:一是走數理科學的路,研究哲學;二是用哲學知識去分析文學、社會科學。先生認為第二條路非常對自己的胃口,作出了“理轉文”的抉擇,當時特有的教授治校、學術自由的校風,讓思想上天馬行空的先生如愿以償。
“我在西南聯大度過了整整七年,讀過四個系(土木、歷史、哲學、外文),現在回想起來,那是我一生中最愜意、最值得懷念的好時光。聯大的生活是自由的,你可激進也可保守,可民主也可守舊,任你左狂右狷。讀書是自由的,大小圖書館的圖書一律開架,學生自由進入。選課是自由的,所有教室大門敞開”。先生旁聽過吳宓先生的“歐洲文學史”,沈從文先生的“中國小說”,張奚若先生的“西洋政治思想史”,劉文典先生的“溫李詩”,馮至先生的“浮士德”,湯用彤先生的“大陸理性主義”等。這些必修和選修之外的課程,先生聽得津津有味,至今記憶猶新。
張奚若先生授課喜歡雜著英文講,也經常在課堂上扯閑話,他不止一次地感慨道:“現在已經是民國了,為什么還老喊萬歲?那是皇上才提的。”
雷海宗先生不但非常博學,而且記憶力非常了不起,上課不帶只字片紙,可是一提起歷史上的某某人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或某件事發生在哪一年,全都是脫口而出。
錢穆先生講課自己的想法很多,充滿了感情,往往慷慨激越,聽者動容。
錢鐘書先生講課是啟發式的,他不告訴你結論,總是在提示你,有機鋒,聰明的人才能跟得上他。
陳寅恪先生經常身著一襲布長衫,望之如一位徇徇然的學者,一點看不出是曾經喝過一二十年洋墨水的人。他引用材料時從不查閱書籍,歷歷如數家珍。
……
吳小如先生得知我拜訪過先生后,特地囑我帶路引見。
2008年12月21日,戊子冬至,北京出現了近五年來的最低氣溫,城區風力達五至七級,地面氣溫零下十一至十二攝氏度。
“吳老,這么冷的天還去不去?”我怕老人凍感冒。
“去,拜訪長者怎能失約!”小如先生態度堅決。
“您的書剛一出來我就托人買了一本,中午沒睡覺一口氣讀完了,很有意思,也很想見見您,今天是三生有幸。”
“我也是三生有幸,哈哈哈。”
兩位年齡相加一百七十五歲的長者走到了一起,饒有興趣地聊起了北大、清華、燕京、西南聯大的陳年往事,聊起了朱自清、沈從文、俞平伯、周一良、王瑤、廢名等先生的學問文章,也聊起了嚴嵩、錢謙益、鄭孝胥、汪精衛、黃秋岳等雖擅文翰然而大節有虧的人,不知不覺三個小時就過去了。
歡愉嫌晝短。我請二老到清華園內的餐廳用膳,師生們熙來攘往,沒有人留意飽經風霜、知名海內外的二位學人。這是金錢至上、物欲橫流的悲哀,還是我少見多怪、杞人憂天?
先生因身體原因研究生肆業后,先后任教于臺灣建國中學、湖南第十一中學,新中國成立前夕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后供職于北京圖書館、西北大學(陜西師范大學),1956年調至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師從侯外廬先生,一干就是三十年。“文革”中,先生與“反共老手”顧頡剛先生、“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謝國楨先生關在一個“牛棚”,成為朝夕相處的“棚友”。
先生主要罪名是“為中國復辟資本主義招魂”。上世紀五十年代,毛澤東、周恩來聯名邀請大搞世界和平運動的哲學家羅素訪華,羅因身體原因未能成行,贈送毛澤東一本他的《西方哲學史》,毛批示譯出。商務印書館委托先生翻譯,想不到譯著遂成“為中國復辟資本主義招魂”的鐵證。“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我完全不知道,造反派也不知道,是后來我的老同學、商務印書館副總編輯駱靜蘭女士告訴我的”。另外兩個罪名是“惡毒地攻擊我們敬愛的江青同志”(曾私下議論京劇是古典劇種,穿現代衣服演現代故事顯得不對味)、“崇洋媚外”(午餐怕排隊自帶面包)。
政治氣候的復雜多變、個人命運的沉浮不定,阻礙不了先生聰明才智的發揮。風雨如晦的日子里,先生大鳴大放不發言,文斗武斗不參加,躲進小樓成一統,偷偷開起了“地下工廠”,專心致志譯書撰文。其譯著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康德的《論優美感和崇高感》和《歷史理性批判文集》、羅素的《哲學問題》和《論歷史》、帕斯卡爾的《思想錄》等,全部完成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其《歷史理性批判散論》、《歷史與歷史學》、《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等著作中的重要觀點與論述也形成于這個時段。
先生九十歲時深情回憶:“我一生中的奉命譯著只有《西方哲學史》一本,其他都出于興趣愛好,選譯的都是馬克思以前的西方古典著作,安全系數比較大,當時根本沒有考慮能不能出版發行。”后來撥亂反正了,先生一部部扛鼎之作陸續付梓,確立了自己在思想界、文學界、哲學界、翻譯界的地位。有人這樣評說:“如果想了解當下中國學者對歷史哲學的最高研究狀態,就不能不讀何兆武先生的論著。如果想通過中國學者的目光去審視西方的史學思想,然后反轉身來,再去審視當下的中國史學,同樣不能不去讀何兆武先生的論著。”
先生三個姐妹的命運卻是另一番情景。二姐何兆男(后改名何愷青)就讀北大經濟系時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學生運動中被憲兵第十三團團長、蔣介石侄子蔣孝先抓起來關了一年。三姐何兆儀就讀北大化學系時是地下黨員,“一二·九”運動的積極分子,抬棺游行時被宋哲元的二十九軍抓起來關了好幾天,最后被校長蔣夢麟保釋出來。妹妹何兆華(后改名柯炳生)就讀于西南聯大中文系,也是“一二·一”運動的積極分子,1946年和愛人蕭前一起去了解放區。后來,二姐漂泊海外二三十年杳如黃鶴,三姐“文革”中斗成精神病不久謝世,妹妹在反右傾運動中自殺。
“人貴有自知之明,不是搞政治的材料就別去搞”。先生為姐姐妹妹的坎坷人生嘆息。“政治歸根結底是權力的運作。如果你想把政治作為職業,就必須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否則就不要去碰它。”
先生置身于中國思想文化近代化進程中,曾擔任過中美文化交流委員會中方訪問美國學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魯斯基金訪問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研究所特約研究員、德國馬堡大學客座教授,六十五歲時回到清華園講歷史。兩個研究生、一兩個青年教師圍坐身邊暢所欲言,先生最喜歡這種教學方式。先生還給本科生講課,談“中學”與“西學”、傳統與近代、“五四”與啟蒙、共性與個性、關照與超越等。這些談話收集在《文化漫談》中,讀者稱贊談話耐看有味,沁人心脾。
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先生月旦人物忠實于自己的感受和印象,不虛談,不妄言。如他說:
吳晗先生有兩件事我記憶十分深刻。一件是作為“二房東”經常趕人搬家,另一件是跑警報驚惶失措有失氣度。“文革”后,清華給吳晗先生立了像。講影響,吳比不上梁啟超先生;講學術,吳比不上王國維、陳寅恪先生;講貢獻,吳比不上趙九章、葉企孫先生。這或許是政治待遇需要如此吧!
殷福生學長是一個很怪的人。他狂妄自大,在課堂上公然罵文學院院長“胡適這個人一點哲學都不懂”!尤其是他反共不遺余力,公開為蔣介石集團辯護,即使是三青團骨干分子也不會這么明目張膽。我們都討厭他,認為他是大右派、法西斯。抗戰末年殷參加青年軍,后任《中央日報》主筆,去臺灣后改名殷海光,成為《自由中國》的重要撰稿人,義無反顧地和國民黨文膽雷震先生一道走上了倡導民主與科學、反對國民黨獨裁專制的道路,成為臺灣思想界的啟蒙導師和精神領袖,遭到國民黨的全面封殺,五十歲就英年早逝。殷由死心塌地擁蔣到堅決徹底地反蔣,前后不過七八年時間。
先生褒貶時賢不為尊者諱,多是切身感受,自家之言。
2011年4月21日,清華大學百年華誕。先生與小他一歲的學長楊振寧先生坐到了一起。六十六年前,先生去聽陳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說”,外文系的男生都做美軍翻譯去了,整個教室全是女生,旁聽的先生和楊振寧先生因此格外醒目。楊先生是聯大名人,曾指責愛因斯坦的某篇文章“毫無originality(創新),是老糊涂了吧”。楊先生看了《上學記》后,在校友飯局上給先生解釋:“我不會那么狂妄。”但先生印象太深刻了,固執己見,認為記憶不會有錯。“這本來是理所當然的,正如牛頓所說的一樣,我們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然人類社會就不會發展進步”。
先生不止一次跟我說,西南聯大的新校舍全是泥墻茅草棚,窗戶沒有玻璃,僅支著幾根棍子,一間房子二十個雙層床,住四十名學生,雙層床之間擠著一張很窄的書桌供四人用。這么艱苦的環境卻培養出那么多的優秀人才,靠什么?靠的是最大限度地允許個人自由而又人人充滿希望。學子們深信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戰爭一定會勝利,勝利后一定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過上美好幸福的生活。這種希望的力量催生出蓬勃向上的朝氣,感染和激勵著每一個人,“它確實給我們帶來了堅定的信心和無窮的力量”。
“假設您是今年的清華新生,未來會怎么樣?”我問先生。
“不知道!但我知道金錢不是衡量幸福的唯一標準,所謂‘標準答案’培養不出學術大師、一流人才”。
歷經萬方多難的少年時代、顛沛流離的青年時代、運命多舛的壯年時期的先生,八十五歲時還騎著自行車飛走自如,是清華園里的一道亮麗風景。2006年冬騎車摔成骨折住院治療,門人彭剛和葛兆光先生前去探望,先生正興味盎然地讀著《資治通鑒》。先生大肚能容天下難容之事,唯獨不能忍耐“不自由”和“沒書讀”。他一生中的許多重要選擇,說到底都和這兩點密切相關。
清華曾給先生舉辦過八十壽辰慶祝會,先生早晨家門一鎖飄然離去,獨自漫步清華園,走進了圖書館,說“我不配祝壽”。《上學記》暢銷全國,先生不要一文錢版稅,說“那是文靖女士的勞動”。先生是新中國成立后許多重大政治運動的親歷者,又與二十世紀學術史上有過重要地位的重量級學者過從甚密,讀者朋友翹首以待《上班記》出版,三聯書店也樂觀其成,先生說:“我是個邊緣化的人物,這項工作還得找核心人物來做。”
“存天理,滅人欲”。先生夠得上理學家朱熹所說的道德高標準了。這種超凡入圣、野鶴閑云的名士風范,如今何處可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