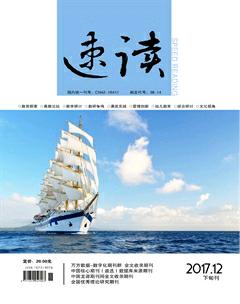淺談高中語文對學生語文思維的培養
宋興平
摘 要: 隨著教育事業的快速發展,學習語文的方式也在不斷變化,循規蹈矩的背誦課文已經不能提高教學質量,教師一味在講臺上講,學生沒有參與性也是不可取的。
關鍵詞:思維方式;培養特點;學生思維
隨著教育事業的快速發展,學習語文的方式也在不斷變化,循規蹈矩的背誦課文已經不能提高教學質量,教師一味在講臺上講,學生沒有參與性也是不可取的。語文的主觀性很強,同一篇課文,每個人的理解是不一樣的,這是自身語文思維決定的。本文主要探討高中語文教學中學生語文思維的培養方式。
社會的快速發展,使得對人才的需要越來越大、越來越高,技術性人才,創造性人才等等這些都需要有靈活的思維能力,而語文教學是培養思維能力的最好課堂。
一、高中語文思維學習現狀
在新課改的要求下,教師的教學觀念要與時俱進,教學模式也會相應改變,這給教師帶來了一定的困難,部分教師無法快速適應新教學方式,導致教學質量較差,這使得學生的思維進步很慢。新課改實施后,有的教師在教學中一味的注重學生的參與性,二忽略了教師的引導作用,比如在講授一個問題的時候教師就直接讓學生去討論,討論的方式方法也不講清楚,是集體討論還是分組討論呢?討論對于學生老說是掩蓋開小差的絕佳機會,如果教師不正確引導和積極參與,那討論可能是達不到教學目的的,思維培養就更談不上了。
二、高中語文思維方式
1.獨立思維。對于學生獨立思維的培養是需要長期積累的,傳統的教學模式是教師主導性的,就是說一堂課下來可能就是教師在上面講,學生在下面聽,沒有參與性、沒有思考時間,進步屬于直接灌輸課本知識,被動接受教學任務,是否能消化就看學生自己的理解能力和思維能力了。新課改就是要教師轉變教學觀念,在教學過程中引導為主,讓學生自主參、積極思考,在恰當的時候教師給出答案,對于出現錯誤的同學要讓他們自己去思考為什么錯了,哪里錯了,下次要怎么去避免這樣的錯誤。
2.全面思維。高中語文不單是學習課本上的知識,還要去思考課本延伸的其他方面,這需要多角度的去分析課本,用良好的思維方式去全面客觀的給出結論。因此,教師在講授課本《雷雨》時,應從多個人物身份出發,從不同的角度去分析每個身份存在的意義和價值,結合課本知識給這個人物一個明確的定位,是好人還是壞人,是好人中的壞人還是壞人中的好人。
三、語文思維培養特點
1.交流性。教師在利用語文思維教學的時候,要積極引導學生去發散思維,要去理解和領悟課本之外的意境,去理解課本深層次的內容,課堂上教師要給學生留點問題,讓學生在合上課本的時候可以去思考去想象,在下次上課的時候再一起探討這個問題,這樣會有很好的交流性和互動性。
2.滲透性。語文教學并不是單純的去教課本上的知識點,教師應該在教學的過程中自然的代入一些思想、品德、價值觀等做人做事方面的知識,畢竟教師是應該去研究學生的、去發現他們的變化、去引導他們、在基礎教學中去滲透這種思想。
3.廣泛性。語文教學所涵蓋的知識面是任何一個學科不能媲美的,可以說中國上下五千年歷史都有所涉獵,所以學生所學習的知識面也是非常寬廣的,看似一本書,內容卻不是一本書所能包涵的,也不是一堂課所能講明白的,需要學生以點概面的去理解和思考。
四、高中語文教學對學生思維的培養策略
1.教學方式對語文教學思維的影響。很長時間以來,教師照本宣科、學生死記硬背的教學方式一直根深蒂固,教師在講臺上滔滔不絕的講,學生在下面安安靜靜的邊聽邊做筆記,這種教學方式使得教學過程非常乏味,很容易讓學生注意力不集中、打瞌睡。隨著時代的發展,教育手段的現代化,目前多媒體教學已經占據半壁江山了,多媒體教學可以做出和課堂知識相關的畫面或是動畫,也會引用相關的影像,這樣就使得學生注意力不容易分散,互動性和積極性也會隨之高漲。在備課過程中教師可以提前規劃好相應的知識點,在課堂教學的時候適當利用多媒體,讓學生有身臨其境的感覺,這樣就會使語文教學行之有效。老師在課堂上提出一些問題讓學生帶著這些問題去自學課文內容,讓學生自主討論,不管答案正確不正確,教師都不要一味的去否定,因為語文只有最優答案沒有正確答案,教師要給與積極思考的同學多一些鼓勵,對有疑問的同學要耐心講解,尊重每一位學生的回答,長此以往,學生會習慣這種教師學生共同參與的課堂,教學效率就會與日俱增,從而有效培養學生的語文思維。
2.教學內容的廣泛性。高中語文教學過程中,教師在基本教學過程中,比如字、詞、句時,要全方位去啟發學生,去深入了解這個字、這個詞、這句話在書本中所表達的寓意,了解作者當時的歷史文化背景,比如《赤壁賦》這篇文章教學時,就要學生提前預習好文中的語句所表達的歷史意境,語文教學內容是固定的,但方式方法是靈活多樣的,所折射的內容是無限廣泛的,這就要求教師和學生都要用心去教去學。結論結合上面所說,高中語文思維能力的培養離不開教師的用心備課和職業操守,更離不開多媒體教學等輔助教學工具的幫助。高中生是有個性和主見的,不比小學生,你給他講什么他就學什么,高中生是有個體思維能力的,教師要去頻繁的啟發這種思維能力,在新課改的基礎上去引導學生,在教學中多提問題,多和學生共同探討問題,學生參與進來了,學習才會有進步,教學才會碰撞出不可思議的火花。
高中語文的教學期間,專業的學生思維開發是目前的一個教育空白,教師應該有針對性地去理解學生、尊重學生、提倡學生的個性化發展,如教育學家蘇霍姆林斯基曾說:“世界上沒有才能的人是沒有的。問題在于教育者要去發現每一位學生的稟賦、興趣、愛好和特長,為他們的表現和發展提供充分的條件和正確引導。”
參考文獻:
[1]劉克健. 論新課程背景下教師的專業發展[J]. 經濟師, 2009,(02).
[2]曾麗英. 高中語文教師如何適應課改的需要[J]. 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 2001,(07).
[3]陳湘才. 新課程下語文教師的觀念嬗變[J]. 湖南教育, 2005,(07).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