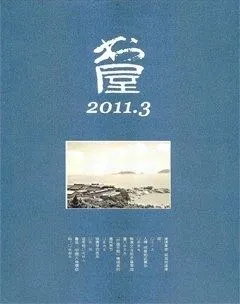讀書人的擔(dān)當(dāng)情懷
宋仁宗慶歷三年,范仲淹由參知政事貶知鄧州(即今河南鄧縣)。兩年后,貶到湖南岳陽的好友、同年考中進(jìn)士的滕子京約請他寫岳陽樓記。
范仲淹,江蘇吳縣人,二十六歲中進(jìn)士,北宋前期政治家。入仕前曾多年在書院講學(xué)。早在秀才時即胸懷以天下為己任的大抱負(fù),自稱“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在宋代初期,學(xué)風(fēng)開闊,胡瑗(教育家)之道德,歐陽修之文章,范仲淹之氣節(jié),堪稱三鼎足。
范仲淹接到朋友的托請,正是政治上不得意之時,他想到青年時的抱負(fù)何時得以實現(xiàn),他當(dāng)然要借這篇文章一吐心中郁悶。洞庭湖上,君山一點,岳陽樓頭,他要做這千年一記。他雖則被貶,卻一點也不消沉。他昂揚(yáng)的志氣,像洞庭湖水一樣翻騰起來。他從“若夫霪雨霏霏”,寫到“至若春和景明”,是想要告訴人們,不管逆境,還是順境,總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堅持自己的政治理念,“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不愧為這一時代開風(fēng)氣的人物,他的君子之德,政治家的胸懷,是要感召時人的。所謂開風(fēng)氣,就好比一陣春雨過,萬物皆發(fā)生。君子之風(fēng),聞風(fēng)而起。一人在前引路向上,人人爭相跟著向上。
范仲淹和他的《岳陽樓記》不僅感召時人,亦更啟迪后人。千年以來,這篇經(jīng)典之作已經(jīng)成為人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生動的教材。
中國傳統(tǒng)的讀書人,即士,即知識分子。他們的人生目的和志向在求道,求治國之道,求天下太平之道。何謂道?道即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也就是莊周講的“內(nèi)圣外王之道”。內(nèi)圣指誠意、正心、修身、齊家,外王即是治國、平天下。而其根本在修身。但不是每個讀書人都有機(jī)會參與治國、平天下的。何況你今天參與了,明天也許要退出。這樣,擺在讀書人面前的,就是兩條路,即“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藏不是消極的,只是離了廟堂,藏于民間。在民間授徒講學(xué),以傳其道。
讀書人的君子之風(fēng)、君子之德,在我國古已有之。像伯夷、叔齊兄弟爭相讓位,不食周粟,隱居山中采薇而食,最后餓死在首陽山。這種大志大勇,高風(fēng)亮節(jié),特立獨行,絲毫不茍且的古之仁人,他們的超階級超時空的美德,正是上古情懷,后世模范。
春秋戰(zhàn)國時,貴族已初具知識分子原始雛形。他們講究道德,人格高尚,意氣豪放。他們指點現(xiàn)實,對理想滿懷積極的向往。屈原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xiàn)的。他的志向從小就遠(yuǎn)大,“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他要“吾與重華游兮瑤之圃,登昆侖兮食玉英,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同光”。他看到現(xiàn)實的丑惡,無限悲涼地喊道“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故將愁苦而終窮”。屈原完美的人格、閃耀的才情成了萬世景仰、萬代勿忘的圣人。
古時農(nóng)家子弟讀書,一年之中有三個月的冬天可以利用。從十幾歲到二十幾歲,有得十年寒窗,書讀得大致可以了。像東漢,政府興辦太學(xué),學(xué)生多至三萬,真是壯觀。戰(zhàn)國讀書人意氣飛揚(yáng),西漢讀書人純樸厚重,春秋及東漢讀書人則儒雅風(fēng)流。他們有平民式的書生式的超凡脫俗,同時亦不脫豪邁氣概。
蘇武的故事是人人盡知的,蘇武出使匈奴,匈奴重視他,要他留下,蘇武不同意。匈奴人軟禁他。小時候我看戲,看到大雪紛飛,蘇武扯下旃毛和雪充饑,眼淚就流下來。匈奴人又將他送到西伯利亞貝加爾湖去牧羊,說等羊生了小羊就放你。其實所牧放的都是公羊,匈奴人騙了他。蘇武在那里以捕野鼠吃草為生,過了十九年,其志不改。他的操守,他的守節(jié)不屈,成了后世人人學(xué)習(xí)的榜樣。
兩晉讀書人向外發(fā)現(xiàn)自然,向內(nèi)發(fā)現(xiàn)深情。他們一崔情深,雖則悼念友人,亦有惜美之意。他們精神自由,將自己像一朵花樣的開放。像王羲之就說:從山陰道上行,如在鏡中游。他們注重人格之美與同情之心,如阮光祿有好車,人借均給,某葬母欲借而不敢言。阮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焚之。
唐代讀書人有豪杰之氣,如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至于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可謂唐代標(biāo)準(zhǔn)之士,他提倡古文,按他自己的說法:“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也。”他要恢復(fù)上古讀書人的擔(dān)當(dāng)情懷,真是有豪杰的志向。
至兩宋,先是王安石與司馬光新舊之爭。后湘人周濂溪以一縣令,置身黨爭之外,繼顏子之學(xué),用則行,舍則藏,以退隱講學(xué)為生,為道學(xué)之開山。于是理學(xué)興起,經(jīng)二程,至南宋大盛,有朱熹集大成者。
南宋末年,國之將亡,文天祥說:“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數(shù)度抗元失敗,再移兵廣東潮陽,兵敗五嶺坡被俘。一路千辛萬苦,被元將押送京城。忽必烈勸其投降,文答“愿一死足矣!”他的正氣歌“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青照汗青”,光照日月,氣壯山河,足以感天地而泣鬼神,成為寶貴的民族精神財富。文天祥亦是光耀天地的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
明代,王陽明在野講學(xué),其弟子亦大多不入仕途。王本就一豪杰之士,在南京作閑官,日與門人游山水間,月夜環(huán)龍?zhí)抖邤?shù)萬人,歌聲震山谷。又如中秋之夜,與弟子百余人宴飲天泉橋,酒至半酣,狂歌曼舞,擊鼓泛舟,仰天長嘯,如游于羲皇之世。而明末顧亭林有旬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zé)。其時滿清入關(guān),亡國在即,他欲維系中華民族文化生命免遭毀滅。
清代是一個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作總結(jié)的時代,道光咸豐后,政權(quán)下滑。湘人曾國藩力挽狂瀾,他曾有言,“吾令讀書人率農(nóng)夫以平天下”。朝廷日益衰弱,社會責(zé)任落到曾國藩、李鴻章、文祥等人肩上。戊戌政變失敗后,譚嗣同送梁啟超到日本領(lǐng)事館避難。由于不懂日文,只好與日本人筆談。譚嗣同寫道:“梁君甚有用,請保護(hù)之。”日人寫道:“君亦應(yīng)留此。”譚嗣同一笑置之。其時,梁啟超面如土色,譚嗣同則意氣洋洋,一如平日。后有人問譚為何不一同留在日使館,譚答:“中國眼看將被瓜分,我沒有心再活下去了。”譚嗣同被捕后,在牢房墻上題詩:“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臨刑前,仰天浩嘆:“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孟子說要養(yǎng)浩然之氣,即是要樹正氣,人的內(nèi)心總是要翻騰的,要有志氣,要尚氣立節(jié)。這是中華民族數(shù)千年的傳統(tǒng),我們怎么能將它去掉呢?我們要對先人有敬畏之心,要學(xué)會認(rèn)識傳統(tǒng),尊重傳統(tǒng),要將先人的美德來養(yǎng)育自己。當(dāng)然我們不會拒絕來自人類任何一方的精神財富,只是我們要警惕,不要沒學(xué)像他人,最后連自己也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