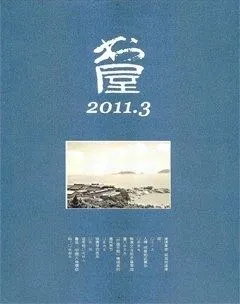歌劇《洪湖赤衛(wèi)隊(duì)》的臺(tái)前幕后
被認(rèn)為紅色經(jīng)典的歌劇《洪湖赤衛(wèi)隊(duì)》在中國(guó)戲劇史上寫下了輝煌的一頁(yè),在中國(guó)音樂史上也是一段華麗的樂章。自1959年上演以來,至今仍被人廣泛傳頌。但是人們看到的只是舞臺(tái)上的演出,卻不太知曉其幕后隱事。筆者有幸與原創(chuàng)人員有較深友誼并對(duì)其創(chuàng)作過程有所關(guān)注,現(xiàn)不揣淺陋略述一二,也算提供一些史料。
生活是創(chuàng)作的唯一源泉
說起歌劇《洪湖赤衛(wèi)隊(duì)》,則必須提及湖北省文聯(lián)。
1949年新中國(guó)建立后,掀起第一次文藝高潮。在全國(guó)范圍內(nèi)不止是縣、市,連一些單位、學(xué)校、企業(yè)都成立了文工團(tuán)隊(duì)開展文藝宣傳活動(dòng)。湖北省文聯(lián)自不例外,時(shí)任省委宣傳部副部長(zhǎng)、詩(shī)人鄭思兼省文聯(lián)常務(wù)副主席,詩(shī)人伍禾為副主席、兼任《湖北文藝》主編,音樂家黃力丁任秘書長(zhǎng),早在抗日時(shí)期從印尼歸國(guó)的華僑張空凌為文工團(tuán)團(tuán)長(zhǎng),他們遵循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原則,從1950年起便先后數(shù)次到昔日革命根據(jù)地洪湖(當(dāng)時(shí)還是沔陽(yáng)的部分轄區(qū))深入生活。我當(dāng)時(shí)在沔陽(yáng)任文工隊(duì)隊(duì)長(zhǎng)(后任縣文聯(lián)副主席兼秘書長(zhǎng))負(fù)責(zé)聯(lián)系。省文聯(lián)及其文工團(tuán)成員包括以后《洪湖赤衛(wèi)隊(duì)》的文學(xué)主創(chuàng)人員梅少山、音樂兼文學(xué)主創(chuàng)人員張敬安等在內(nèi)一行人,來到“洪湖岸邊是家鄉(xiāng)”的峰口一帶,投身清匪反霸等斗爭(zhēng),當(dāng)他們站在一望無際、波濤滾滾的湖邊時(shí),腦海里必然會(huì)呈現(xiàn)出采訪中得來的赤衛(wèi)隊(duì)的傳奇故事,我相信此時(shí)此刻他們已產(chǎn)生了創(chuàng)作的欲望。以后省文聯(lián)又負(fù)責(zé)燕窩區(qū)姚湖鄉(xiāng)的土改工作。親身經(jīng)歷了一場(chǎng)火的洗禮,與此同時(shí),他們還編《湖北文藝》并及時(shí)創(chuàng)作了反映現(xiàn)實(shí)斗爭(zhēng),由鄭思、伍禾編劇,黃力丁作曲,在湖北省算得上真正意義上的歌劇《全家動(dòng)員》,后在這部獨(dú)幕歌劇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作了大型歌劇《土地的主人》,還有伍禾創(chuàng)作的歌劇《門板》等等。這就是說,以后的《洪湖赤衛(wèi)隊(duì)》的主創(chuàng)人員梅少山、張敬安等正是在這時(shí)獲得了斗爭(zhēng)生活的實(shí)感,并初步接受了歌劇藝術(shù)的啟蒙教育,一旦構(gòu)思成熟,創(chuàng)作激情便會(huì)噴薄而出。
《洪湖赤衛(wèi)隊(duì)》是現(xiàn)實(shí)主義的杰作,不論是矛盾的設(shè)置、場(chǎng)景的安排、人物的刻畫等都有很厚實(shí)的根底,如下面一段唱詞:
湖上北風(fēng)呼呼地響,
艙外雪花白茫茫,
一床破絮像魚網(wǎng),
我的爺和娘啊
日夜把兒貼在胸口上
……
這不是僅憑文才就能寫出來的,這是作者發(fā)自肺腑的呼喚,是心靈的火花,包括演員在內(nèi),如果沒有生活實(shí)感和創(chuàng)作激情是寫不出來也唱不好的。大家至今還贊賞王玉珍的演唱,并不是她的聲樂技巧高超,而是她的歌聲里蘊(yùn)含著別人難以企及的革命情愫。
我和大家一樣,至今仍然喜愛這部紅色經(jīng)典,只是不同的是,每當(dāng)我看到和聽到它的音廁時(shí),我也不禁滿懷深情緬懷湖北省文聯(lián)第一任領(lǐng)導(dǎo)人鄭思、伍禾、黃力丁、張空凌等。當(dāng)然,我也有深深的遺憾,在“胡風(fēng)事件”中,鄭思、伍禾均不幸遭難,鄭思還因此以死明志,但是,他們是湖北歌劇藝術(shù)的奠基者,這是我們不應(yīng)忘卻的公共記憶。
《洪湖赤衛(wèi)隊(duì)》的主題歌及其他
自《洪湖赤衛(wèi)隊(duì)》上演以來,其主題歌《洪湖水浪打浪》被人廣泛傳唱并歷久不衰,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這首主題歌并非音樂主創(chuàng)人的原作,而是借用了一首名為《襄河謠》的歌曲。
《襄河謠》的作者為吳群,他當(dāng)時(shí)是襄陽(yáng)軍分區(qū)文工團(tuán)的音樂創(chuàng)作人員,1953年在全國(guó)性的歌曲評(píng)獎(jiǎng)中,《襄河謠》榮獲三等獎(jiǎng),并刊發(fā)于《湖北文藝》。其原詞是歌唱襄河即漢江的:“襄河水,長(zhǎng)又長(zhǎng),河水滾滾向東方……”《洪湖赤衛(wèi)隊(duì)》的主題歌,只是改填了歌詞,并根據(jù)其曲調(diào)延伸了后面的副歌:“四處野鴨和蓮藕,秋收滿畈稻谷香,人人都說天堂美,怎比我洪湖魚米鄉(xiāng)。”《襄河謠》是根據(jù)民歌《月望郎》改編,其曲調(diào)流暢、優(yōu)美,有很強(qiáng)的地域色彩。但當(dāng)時(shí)并沒有在社會(huì)上流傳,以后在文聯(lián)漸漸傳唱,這還得感謝編輯部的一位襄樊籍的女士,她對(duì)歌頌家鄉(xiāng)的《襄河謠》情有獨(dú)鐘,只要稍有空閑,便坐在鋼琴前自彈自唱。別人不聽也得聽,越聽越有味,由此引起大家的關(guān)注,恰好這時(shí)音樂主創(chuàng)人員張敬安對(duì)這位女士有所接近,也許正是這一切,《襄河謠》在他的腦海里留下了永恒的印痕,使他后來創(chuàng)作《洪湖赤衛(wèi)隊(duì)》時(shí)不由自主地借用了這首歌。
借用別人一首歌作為歌劇創(chuàng)作中的主題歌,當(dāng)時(shí)大家都習(xí)以為常,因?yàn)槿藗兯枷肷虾翢o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的概念,直到改革開放后,《洪湖赤衛(wèi)隊(duì)》因文本發(fā)生過糾紛,后得到實(shí)事求是的解決。但借用《襄河謠》一事,公開披露的還不多,據(jù)我所知,后來雙方在私下達(dá)成了協(xié)議,原作者的后人得到了一定的補(bǔ)償,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以為有的妥協(xié)是值得贊賞的,試想,當(dāng)年如果音樂主創(chuàng)人員沒有借用這首《襄河謠》,它的曲調(diào)還能不脛而傳并成為不朽之作嗎?
原在襄陽(yáng)軍分區(qū)文工團(tuán)工作的吳群,后轉(zhuǎn)業(yè)到天門花鼓劇團(tuán)。1980年,珠江電影制片廠應(yīng)東南亞華僑之約,將有“華僑之鄉(xiāng)”之稱的天門花鼓劇團(tuán)最有代表性的花鼓戲《站花墻》拍攝成戲曲片《花墻會(huì)》。吳群是這部戲曲片的音樂主創(chuàng)人員,這也是他最后一次展示音樂才華。
《洪湖赤衛(wèi)隊(duì)》的舞臺(tái)劇是由楊會(huì)召、梅少山共同執(zhí)導(dǎo),謝添則是電影版的導(dǎo)演,他還在影片中飾演了張副官一角,戲份雖不多,但在犧牲時(shí)的一段表演,處理得干凈利落,那昂然正氣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影片中重要場(chǎng)次母女牢房相會(huì),聲情并茂的表演催人淚下。可是人們也許沒有想到的是韓母的演唱并非原唱,而是一位也是原省文聯(lián)文工團(tuán)的張玉瑚的配唱,這在所有文字宣傳中從未提過,原本理所當(dāng)然地說明。就在筆者動(dòng)筆寫此文時(shí),我再一次向張玉瑚咨詢,她除了證實(shí)此事外,還特別叮囑我不必把此事公開,以免對(duì)這部紅色經(jīng)典和韓母扮演者有所損傷。另外,還有十分動(dòng)聽的“小曲好唱口難開”是向玉梅配唱,小紅的三棒鼓則是著名歌唱家蔣桂英配聲,因?yàn)橹挥兴娜艄拇虻们宕啵謵偠?br/> 別人借用自己的歌曲,默默獻(xiàn)出自己的歌聲,這在今天看來不可理解,但在那個(gè)年代提倡的是“把一切獻(xiàn)給黨”,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殊不知也就在那個(gè)時(shí)候,有人就說:“我們時(shí)代的另一個(gè)特征就是承認(rèn)個(gè)人的新的重要性,人與人要像主權(quán)國(guó)家之間那樣相待。”(美國(guó)作家愛默生語(yǔ))
“彭霸天”——當(dāng)代的雷海青
彭霸天是《洪湖赤衛(wèi)隊(duì)》中的反派主角,但我把他的名字打了引號(hào),這表明別有所指,我這里說的“彭霸天”就是指扮演此角的演員陳金鵬。而雷海青則是唐代的一位宮廷樂師,他精通琵琶,據(jù)《明皇實(shí)錄》記載:安史之亂中,叛兵攻人長(zhǎng)安,掠文武朝臣、宮嬪及樂師,送至洛陽(yáng)凝碧池聚宴,并露刃脅迫眾樂師奏樂,雷海青拒不從命,擲樂器于地上。安祿山為之憤怒,當(dāng)眾將雷肢解。詩(shī)人王維有詩(shī)詠其事。陳金鵬與雷海青相距一千三百多年,但他們都有令世人敬仰的節(jié)烈精神。
陳金鵬原是一名藝劇演員。其劇以“三小”戲?yàn)橹鳎惤瘗i是戲班里的當(dāng)家小丑,武漢解放后,他從戲班轉(zhuǎn)入新型文工團(tuán),后又并入歌劇團(tuán)。這就是說,他從“下九流”一躍成為“靈魂工程師”,這使他感到無比自豪,也激勵(lì)他努力奮進(jìn)。以他僅有的一點(diǎn)文化知識(shí),堅(jiān)忍頑強(qiáng)地鉆研藝術(shù),后來竟然成為歌劇團(tuán)藝委會(huì)主任,集編、導(dǎo)、演于一身。
在陳金鵬塑造的一系列藝術(shù)形象中,最令人難忘的當(dāng)是彭霸天。他的表演深沉,含蓄,既不火,也不蘊(yùn),藝術(shù)適度感強(qiáng),他創(chuàng)造角色幾乎達(dá)到忘我程度。他認(rèn)為演員創(chuàng)造角色不僅是在排演過程,且是在每次演出之中。因此他每次演出必提前到場(chǎng),化好妝,穿好服裝便找個(gè)地方像和尚入定似的閉目靜坐,體驗(yàn)角色,演出時(shí)也不與別人閑聊,散戲回家記演出日志,方上床入睡,以至后來有人贊譽(yù)其為“活彭霸天”。
就是這樣一個(gè)優(yōu)秀演員,卻因生性耿直,遭來殺身之禍,說來令人心怵。那是上世紀(jì)六十年代初,當(dāng)時(shí)《洪湖赤衛(wèi)隊(duì)》也譽(yù)滿神州,忽然陳金鵬有回鄉(xiāng)一行,他的家鄉(xiāng)黃陂與全國(guó)農(nóng)村一樣,正陷入饑荒困境,也許是受到傳統(tǒng)戲曲中那些直言上諫的農(nóng)民影響,他極不適宜的在一些場(chǎng)合說出了一些與當(dāng)時(shí)氣氛不協(xié)調(diào)的言論,甚至上萬言書進(jìn)諫。別人在賞賜的盛宴上狼吞虎咽,他卻停箸沉思,這不是“伸出頭來接石頭”么?果然一塊大石頭砸在他的頭上。如果他當(dāng)時(shí)能夠及時(shí)“悔悟”,本可避免更大的劫難。孰料他臨危也不改初衷。有一次他被關(guān)在“小屋”里反省,與他結(jié)婚不到兩年的愛妻抱著出世不久的乳嬰來探視,希望以人倫之情打動(dòng)他凝固的心,促使他“迷途”知返。他雖然聽到門外愛妻的悲啼和愛子的哭泣,但他依然面壁靜坐,不為所動(dòng),由此可看出他為堅(jiān)持正義的堅(jiān)毅意志與不屈精神。就這樣的“頑固不化”、“死不悔改”,其后果可想而知。不久,陳金鵬被逮捕并被判刑,但他仍然堅(jiān)持自己的立場(chǎng),甚至絕食抗議,直到囚禁五年多后的1969年死于沙洋農(nóng)場(chǎng),這就是“當(dāng)代的雷海青”之死。從陳金鵬和雷海青的身上我們都能感受到中國(guó)傳統(tǒng)道德中的氣節(jié)。“氣為敢作敢為,節(jié)是有所為,有所不為,就是不合作”。這就是我們需要薪火傳承的高風(fēng)亮節(jié)。
陳金鵬于1965年元月被省高院以反革命罪判無期徒刑,過了將近二十年的1984年10月,又是省高院再次宣判陳金鵬不構(gòu)成反革命罪。雖然人已不在了,但歷史終于恢復(fù)了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