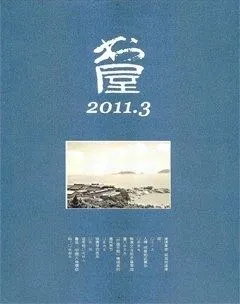魯迅:中國人有信仰嗎?
國民性批判是魯迅終其一生堅(jiān)守的工作重心、他力圖以此動(dòng)搖中國人普遍遵循的共同生存根基:“我總還想對(duì)于根深蒂固的所謂舊文叫,施行襲擊,令其動(dòng)搖。”而他對(duì)國民性許多精神側(cè)面的批判都與他對(duì)國民信仰問題的關(guān)注相勾連,與西方的尼采和克爾凱郭爾一樣,中國的魯迅也敏銳地把握到中國國民精神信仰式微的走勢。
如果孔丘、釋迦、耶穌基督還活著,那些教徒難免要恐慌。對(duì)于他們的行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樣慨嘆。
人是一種信仰的動(dòng)物,托克維爾斷言:“一個(gè)沒有共同信仰的社會(huì),就根本無法存在。”中國沒有西方基督教意義上的本土宗教。楊慶塑認(rèn)為:“中國不是沒有宗教,而是與西方、近東和印度的宗教不同。”中國宗教的特點(diǎn)是混合宗教,而不是如基督教、伊斯蘭教和佛教那樣的獨(dú)立宗教。自晚清以來,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梁漱溟、陳獨(dú)秀、胡適等人均對(duì)宗教表明了自己的態(tài)度,宗教與社會(huì)之間的關(guān)系成為中國現(xiàn)代性的基本問題之一。人的生活在物質(zhì)與精神兩個(gè)維度上展開。所有的宗教都旨在將個(gè)人與社會(huì)的心靈提升到精神的境界。宗教的功能在于制衡不斷膨脹的物質(zhì)欲求,它對(duì)民眾的精神提升力是省察一個(gè)民族國民性的重要方面。魯迅在留日時(shí)期就對(duì)宗教信仰問題給予了高度重視。在《科學(xué)史教篇》、《文化偏至論》和《破惡聲論》中,包含有魯迅對(duì)宗教文化的獨(dú)特理解。關(guān)于宗教起源問題,魯迅認(rèn)為:“夫人在兩間,若知識(shí)混沌,思慮簡陋,斯無論已;倘其不安物質(zhì)之生活,則自必有形上之需求。故吠陁之民,見夫凄風(fēng)烈雨,黑云如盤,奔電時(shí)作,則以為因陁羅與敵斗,為之栗然生虔敬念。希伯來之民,大觀天然,懷不思議,則神來之事與接神之術(shù)興,后之宗教,即以萌蘗。雖中國志士謂之迷,而吾則謂此乃向上之民,欲離是有限相對(duì)之現(xiàn)世,以趣無限絕對(duì)之至上者也。人心必有所馮依,非信無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在這里,魯迅把宗教視為人類脫離有限相對(duì)的現(xiàn)世而向無限絕對(duì)的超世提升的一種努力,因而,他十分重視信仰對(duì)國民性格的化育功能。在《破惡聲論》中,魯迅明確指出:“宗教由來,本向上之民所自建,縱對(duì)象有多一虛實(shí)之別,而足充人心向上之需要?jiǎng)t同然。”如果我們將宗教信仰視為“向上之民”的標(biāo)志,那么,《文化偏至論》中“中國在昔本尚物質(zhì)”的斷語就隱含著魯迅早期對(duì)中國國民缺乏真減信仰的痛惜與批判。在他看來,中國社會(huì)普遍存在著的是“精神窒塞,惟膚薄之功利是尚,軀殼雖存,靈覺且失”,毫無信仰的“澆季士夫”。作為啟蒙思想者的魯迅,一方面高揚(yáng)科學(xué)旗幟,另一方面又反對(duì)“舉世惟知識(shí)之崇”、“不思神閟變化”的傾向,他把借“科學(xué)”之名廢除宗教者稱為“偽士”。
在中國,幾乎所有的信仰對(duì)象都被異化為實(shí)利主義者做戲的道具。這是魯迅對(duì)中國信仰史所做的一個(gè)歷時(shí)性掃描:
其實(shí)是中國自南北朝以來,凡有文人學(xué)士,道士和尚,大抵以“無特操”為特色的,晉以來的名流,每一個(gè)人總有三種小玩藝。一是《論語》和《孝經(jīng)》,二是《老子》,三是《維摩詰經(jīng)》……宋儒道貌岸然,而竊取禪師的語錄……(清代)儒者的相信《太上感應(yīng)篇》和《文昌帝君陰騭文》,并且會(huì)請(qǐng)和尚到家里來拜懺。
耶穌教傳入中國,教徒自以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卻都叫他們是“吃教”的。這兩個(gè)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可以包括大多數(shù)的儒釋道教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于許多“吃革命飯”的老英雄。
清朝人稱八股文為“敲門磚”……近年則有雜志上的所謂“主張”。《現(xiàn)代評(píng)論》之出盤,不是為了迫壓,倒因?yàn)檫@派作者的飛騰;《新月》的冷落,是老社員都“爬”了上去,……稱之為“上天梯”罷。
“教”之在中國,何嘗不如此。
在這里,魯迅的國民性考察已明顯地深入到國民精神信仰層次。
克爾凱郭爾終其一生批判基督教教士和教會(huì)的市儈氣和虛偽性,其核心思想正是在對(duì)所處時(shí)代信仰危機(jī)的批判中形成的。在他眼中,向工業(yè)化闊步邁進(jìn)的十九世紀(jì)是一個(gè)物質(zhì)主義甚囂塵上的時(shí)代,技術(shù)在改善著人們生活,也在逐漸物化著人們的心靈。在克爾凱郭爾看來,沒有“上帝”的生存是向動(dòng)物性生存的沉淪,只有真正的信仰才能賦予人的生存以意義感,“信仰是最高級(jí)的”。“假如沒有一種神圣的契約將人類聚合在一起,世世代代只是像森林中的樹葉那樣生長,像森林中的飛鳥那樣自鳴得意”,那么,“生命該是多么空虛與無味啊!”克爾凱郭爾敏銳地覺察到:信仰已淪為有關(guān)信仰的言說,雖然每個(gè)人都能感受到基督教氣氛的濃郁、教會(huì)勢力的強(qiáng)大,然而這些與真正的信仰相去甚遠(yuǎn)。
在東方,魯迅對(duì)中國國民性中普遍存在的信仰虛偽性進(jìn)行了深刻的批判,國民精神信仰問題是魯迅一生所關(guān)注的核心,他傾盡全力批判中國國民性中“無堅(jiān)信”、“無特操”的人格缺失,這是他自覺不自覺地以佛教、基督教等宗教作為參照系而得出的結(jié)論。在魯迅看來,中國人雖各有精神招牌而其實(shí)是什么都不信的:
中國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像很少“堅(jiān)信”……崇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戰(zhàn)士,明天信丁。宗教戰(zhàn)爭是向來沒有的……
人而沒有“堅(jiān)信”,狐狐疑疑,也許并不是好事情,因?yàn)檫@也就是所謂“無特操”。
然而看看中國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們的對(duì)于神、宗教、傳統(tǒng)的權(quán)威,是“信”和“從”呢,還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們的善于變化,毫無特操,是什么也不信從的,但總要擺出和內(nèi)心兩樣的架子來……
將這種特別人物,另稱為“做戲的虛無黨”或“體面的虛無黨”以示(與俄國想、說、做一致的“虛無黨”——引者加)區(qū)別罷。
信仰難嗎?克爾凱郭爾說:信仰實(shí)際上是“最困難的事情”。因?yàn)椤靶叛鲆詶壗^為前提”。魯迅發(fā)現(xiàn)中國人“永遠(yuǎn)只能看見物質(zhì)的閃光”,在“中國歷史的整數(shù)里面,實(shí)在沒有什么思想主義在內(nèi)”。中國人是徹底的實(shí)利主義者,“要做事的時(shí)候可以援引孔丘墨翟,不做的時(shí)候另外有老聃”。“悟善社里的神主已經(jīng)有了五塊:孔子,老子,釋迦牟尼,耶穌基督,莫哈默德”。只要可以利用,“至于所掛的招牌是佛學(xué),是孔道,那倒沒有什么關(guān)系”。所有的信仰對(duì)象均可變?yōu)槭浪资澜绲墓ぞ撸热纾瑲v來尊孔者莫不“把孔夫子當(dāng)做磚頭用”。魯迅對(duì)于佛教徒的認(rèn)識(shí)也與此同,他“以為堅(jiān)苦的小乘教倒是佛教,待到飲酒食肉的闊人富翁,只要吃一餐素,便可以稱為居士,算作信徒,雖然美其名曰大乘,流播也更廣遠(yuǎn),然而這教卻因?yàn)槿菀仔欧睿蚨優(yōu)楦』蛘吒偟扔诹懔恕薄t斞赶裎鞣降哪岵尚妗吧系鬯懒恕币粯有骈L期影響中國人心靈生活的佛教和孔教“都已經(jīng)死亡。永不會(huì)復(fù)活了”。
當(dāng)信仰僅僅變成一種言詞和招牌,信仰已不存在,那么,它將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什么?魯迅以此為基點(diǎn)對(duì)中國國民性進(jìn)行了深層拷問。在談及廣州人的迷信時(shí)魯迅說:迷信本身是“不足為法的,但那認(rèn)真,是可以取法,值得佩服的”。而中國人由于沒有“堅(jiān)信”,“有許多事情都只剩下一個(gè)空名和假樣”。魯迅看到了中國人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做戲”傾向:“中國本來喜歡玩把戲”,生活本身變得極“富于戲劇性”,許多事情只不過是“做做戲”而已。而這種“普遍的做戲,卻比真的做戲還要壞”,因?yàn)椤罢娴淖鰬颍侵挥幸粫r(shí)”,而“普遍的做戲者,就很難有下臺(tái)的時(shí)候”。印度“甘地的把戲”若發(fā)生在中國“倘不挑選興行場(日本語指戲場)就毫無成效了”。在這樣的國度,許多事連“說教的人,恐怕自己也未必相信罷”,而普遍的“不相信”又成為“‘愚民’的遠(yuǎn)害的塹壕,也是使他們成為散沙的毒素”。如此循環(huán),使實(shí)利主義甚囂塵上,徹底阻斷了一個(gè)民族向上的精神提升。由此可見,在魯迅的國民性批判中,信仰缺失是一個(gè)非常重要的觀察視角。由于無信仰導(dǎo)致的做戲、不認(rèn)真,彌漫于社會(huì)各個(gè)角落、各個(gè)階層,成為中國國民性的一項(xiàng)頑癥。魯迅認(rèn)為,“玩玩笑笑”的態(tài)度,正是“開開中國許多古怪現(xiàn)象的鎖的鑰匙”。這把鑰匙可以打開“特別的中國”的國民性的深層秘密之門。
在政治生活領(lǐng)域,“升官不過是一種發(fā)財(cái)?shù)拈T徑。所以官僚雖然依靠朝廷,卻并不忠于朝廷,吏役雖然依靠衙署,卻并不愛護(hù)衙署”。“對(duì)付的方法有‘蒙蔽”’。甚至連“歸隱”一旦掛上招牌也脫不了“換飯”的嫌疑,因?yàn)椤罢娴摹[君子’是沒法看到的”。正如路德所認(rèn)為的:信仰一旦用漂亮的言詞言說就已遠(yuǎn)離信仰本身。“登仕,是啖飯之道,歸隱,也是啖飯之道”。“肩出‘隱士’的招牌來,掛在‘城市山林’里,這就正是所謂‘隱’,也就是啖飯之道”。正是由于把從政視為“啖飯之道”,所以中華民國之后就有人“扮成憲政國家的選舉的人和被選舉人”,而且“大都扮演得十分巧妙”。魯迅感嘆道:“中國實(shí)在是太不認(rèn)真。”正是由于“無堅(jiān)信”、“無特操”,“中國的政客,也是今天談財(cái)政,明日說照像,后天又談交通,最后又忽然念起佛來了”。
如果仔細(xì)考察魯迅與許多文化人或文化團(tuán)體的沖突,其原因也大多由于這些人或團(tuán)體所體現(xiàn)出的“無堅(jiān)信”、“無特操”上。在魯迅看來,中國文人最善于用文字玩弄把戲。他說中國是“最不看重文字的‘文字游戲國”’,有些人“總愛玩些實(shí)際以上花樣”,為的是撈些“冠冕堂皇的名目”而已。有些巧猾的“暴發(fā)戶”甚至以“做作的頹唐”當(dāng)做…爬上去’的手段”。到處充滿了“文章之做戲”,到處是文字的“夸大、裝腔、撒謊”。身處文界的魯迅深切體會(huì)到:文人的“做戲”主要體現(xiàn)為多變善變,“革命到時(shí),便是革命文豪”。魯迅在分析“現(xiàn)代評(píng)論派”之變調(diào)時(shí)指出:“我真疑心他們得了一種仙丹,忽然脫胎換骨。”并結(jié)合佛教信仰的墮落進(jìn)一步分析道:“革命也如此的,堅(jiān)苦的進(jìn)擊者向前進(jìn)行,遺下廣大的已經(jīng)革命的地方,使我們可以放心歌呼,也顯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實(shí)是和革命毫不相干。”“這樣的人們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會(huì)從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復(fù)舊。”正因?yàn)椤凹僦R(shí)階級(jí)”毫無信仰,所以才能“今天發(fā)表這個(gè)主張,明天發(fā)表那個(gè)意見”。思想似乎天天在進(jìn)步,但在魯迅看來“真的知識(shí)階級(jí)的進(jìn)步,決不能如此快的”。在談到期刊紛出的狀況時(shí),魯迅發(fā)現(xiàn)“他們大抵將全力用盡在偉大與尊嚴(yán)的名目上,不惜將內(nèi)容壓殺。連產(chǎn)生了不止一年的刊物,也顯出拼命的掙扎和突變來”。
綜觀魯迅與現(xiàn)代評(píng)論派、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的論爭,均集中在對(duì)他們“無堅(jiān)信”、“無特操”品性的批判上。在魯迅筆下,他們成為國民生存狀態(tài)的一種符號(hào)和象征。他明確批評(píng)創(chuàng)造派的某些革命文學(xué)家雖然玩著“藝術(shù)的武器”,而他們自己卻是“不大相信”的。他們提倡革命文學(xué),也是因?yàn)楦锩膶W(xué)乃是“時(shí)行的文學(xué)”。他們的突變“其實(shí)是并非突然的事”,而是源于一種“無堅(jiān)信”、“無特操”的人格結(jié)構(gòu)。這種“突變”是“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其間并“無線索可尋”,只是“隨時(shí)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做武器”罷了。“我們只要取一種刊物,看他一個(gè)星期,就會(huì)發(fā)現(xiàn)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頌揚(yáng)戰(zhàn)爭”。“要自由的人,忽然要保障復(fù)辟的自由,或者屠殺大眾的自由”。毫無正信的機(jī)會(huì)主義者總是“一面胡說八道,一面想著將來的變化,就越加縮進(jìn)暗地里去,準(zhǔn)備著情勢一變,就另換一副面孔;另拿一張旗子,從新來一回”。所以,文學(xué)界最大的墮落在于“文學(xué)家的頭銜,已成為名利雙收的支票了”。他們“不過是在‘文人’這一面旗子的掩護(hù)之下,建立著害人肥己的事業(yè)的一群‘商人與賊’的混血兒而已”。知識(shí)分子本是社會(huì)精神的承擔(dān)者與傳遞者,在魯迅的知識(shí)分子批判中隱含著一代先覺者更加深沉的憤懣和悲哀。
信仰意味著精神,信仰的缺失意味著精神的空無。缺乏精神性的“尚物質(zhì)”傾向是中國國民性的深層底色,因?yàn)椋叛霾粌H關(guān)乎宗教,而“是一種根本的行為,我們?nèi)祟惪傮w的存在便是建立在這個(gè)基礎(chǔ)之上,信仰也是我們領(lǐng)悟總體實(shí)在的意義的關(guān)鍵”。當(dāng)代著名神學(xué)家巴特更是明確指出:“信仰并非只和一種特殊的范圍——宗教——有關(guān),它和實(shí)際生活的全部都有關(guān)。”因此,我們可以說,魯迅早期的中國人“尚物質(zhì)”觀是他一生國民性思考的思想原點(diǎn)。俄國思想家別爾嘉耶夫認(rèn)為:“如果沒有上帝,也就沒有秘密。如果沒有秘密,世界就平淡無奇,人就有兩個(gè)維度,否則,就沒有能力使自己不斷提高。”一個(gè)民族普遍的信仰缺失必將導(dǎo)致一個(gè)民族普遍的向世俗生活的跌落與沉淪。信仰是對(duì)純物質(zhì)之生活的不滿,是一種力圖超越“有限相對(duì)之現(xiàn)世”,向“無限絕對(duì)之至上”升騰的“形上之需求”,它所表現(xiàn)的是一個(gè)民族的“向上”之心。,魯迅雖未從純學(xué)理的角度研究過宗教,但他作為一個(gè)獨(dú)異的思想者從宗教信仰這一維度切人中國國民性思考所達(dá)到的深度與廣度,理應(yīng)受到當(dāng)今學(xué)術(shù)界和全社會(huì)的普遍關(guān)注。
另外,魯迅也從未明確表達(dá)過自己曾信仰過任何一種宗教,但多種宗教情愫的浸潤,西方現(xiàn)代個(gè)體生存哲學(xué)家對(duì)宗教信仰“個(gè)體化”的思考都無形中影響著他的心靈。表現(xiàn)在他生活中的韌性戰(zhàn)斗精神、救世精神和自我犧牲精神,都表現(xiàn)出真正的宗教徒式的崇信;他性格中的認(rèn)真與誠實(shí)、堅(jiān)定都顯示出真正的宗教徒式的力量。在紛然多變的現(xiàn)代中國社會(huì),他是最能夠保持思想聚焦性的人。“在生活的路上,將血一滴一滴地滴過去,以飼別人,雖自覺漸漸瘦弱,也以為快活”。內(nèi)山完造甚至尊他為“深山中苦行的一位佛神”。
真正的信仰不在言詞之中,而在行動(dòng)之內(nèi)。從這個(gè)意義上說,魯迅稱得上克爾凱郭爾筆下的“信仰義士”,他像亞伯拉罕一樣毫不動(dòng)搖地持有信念。正是這種信念使他像孤獨(dú)的“過客”一樣,拒絕廉價(jià)的慰安,棄絕巧滑的勸誡而奮然前行,任憑“夜色跟在他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