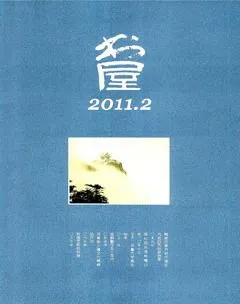她堅守著詩化精神家園
與所有詩人一樣,灰娃也有詩人必備的條件之一,那就是詩人氣質和稟賦。她敏感,富于幻想,向往美好的世界。有時我想,倘若灰娃沒有隨表姐去延安而留在國統區,那她的命運會是怎樣?當然,已逝歲月作為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但是我猜測:她極有可能還是一位詩人,就像當時活躍在國統區內的“七月派”和“九葉派”詩人一樣。我之所以作這樣的假設,是因為我覺得對有的詩人來說,客觀環境的變化并不能改變其詩人氣質和稟賦。讀了《我額頭青枝綠葉灰娃自述》后,我覺得灰娃就是這樣的詩人。甚至可以這樣說,灰娃的詩人氣質和稟賦是與生俱來的。書中寫道灰娃在九歲和十歲時在國文課上寫作文,都受到老師的贊揚,并在全班宣讀。其中一位老師還在她的作文本上寫著:“你是未來的作家。”灰娃寫道:“那時心中連‘詩’為何物,一點兒也不知道,可是為什么會寫成一行一行?完全下意識的,順著心中那時輕松歡樂的節奏,把它用文字記錄下來。……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詩’這種文學樣式。之后,我才體驗領悟了:生命及生命精神自有其內在的節奏韻律,自有其音樂性的感應。”一個未受多少教育的孩子,已有如此詩的內心體驗,這說明灰娃從小就具備詩的稟賦。灰娃到了延安后,參加了兒童藝術學園,受到“文抗”的作家、藝術家的藝術教育,又經常進行演出,還讀了不少經典名著,藝術感受力肯定有所提高。只是由于當時處于戰爭時期的根據地,以“為工農兵服務”作為文藝方針和準則,強調文藝作品的“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宣傳戰斗作用,張揚“大我”,擯棄“小我”,因此,灰娃帶有濃厚的“小我”個性色彩的詩人氣質和稟賦無從表現和宣泄,處于沉睡狀態。直到給億萬人民的噩夢“文革”結束后,灰娃的詩人氣質和稟賦在噩夢中蘇醒了!她終于從一個精神分裂癥患者蛻變為一名杰出的詩人。
對灰娃來說,詩人氣質和稟賦無疑是重要的,然而,更為重要的是在她內心深處擁有一個理想的王國,這也是她的美麗的精神家園。這個美麗的精神家園在她童年時就形成了。她與生俱來就具有善良、單純的本性,她胸無城府,人們說她“光長個兒不長心”。她熱愛自然,熱愛藝術,向往一切美好的事物,向往幸福的生活。她堅定地相信生活像她所希望的那樣總是美好的,人與人之間總是充滿著關愛、信任、溫馨。伏爾泰曾說:“個性與幻想、命運、生命交織在一起,表達出生命的意義,這時,就要求想象去把這個特別的世界——這個壓根兒就不是現存的世界作為一個在獨特的關聯中建立起來的世界構造出來。”很明顯,灰娃的充滿個性幻想色彩的精神家園“壓根兒就不是現存的世界”,帶有烏托邦性質,只能存在于詩中。所以。當外界環境和她心目中的美麗的精神家園相對和諧時,她就會感到幸福和快樂。為什么她對在延安度過的童年時光分外留戀難忘?那是因為她生活在一個革命的大家庭中,在這個大家庭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無論是官兵、上下級都是平等的,互相尊重,互相關愛,互相幫助,充滿團結友愛的氛圍。特別是因為她最小,被稱為“八路軍的公主”,得到更多的關懷和呵護。灰娃后來回憶這段時光時,充滿感情地說:“往事往昔種種,雖已遙遠,但依然溫暖地活在心上,撫慰著我的生命,散發出人情人性之美,詩意地照臨著我的內心世界。”當時她的內心世界是充滿詩意的;然而,在更多的情況下,灰娃的美麗的精神家園和現存世界是不可能達到完全和諧的,所以當外界環境和她心目中的美麗的精神家園變得格格不入和沖突時,她便會感到困惑和痛苦。即便在延安這樣的溫馨的革命大家庭中,竟然也會有粗暴、冷酷和自相殘殺的事情發生。所謂的延安整風和“搶救運動”就是散布互不信任的空氣、制造無數冤案、草菅人命的惡行壞事。這個運動連小孩也不放過,康生派來的人居然找灰娃談話,要她交代特務的問題,真是荒謬可笑之極!只是由于灰娃的機智應列,總算逃過一劫。灰娃在書中是這樣描述當時整人的情景的:
當一個人被誘逼到極度,超出忍耐力時,為
了解脫,就承認自己是特務,說的實際是瞎編
的,而且還必須咬出幾個人才行。如此這般,一
個接一個,許多人就都成了特務,真是驚心動
魄,太可怕了。那情狀,與我幼年時見過城隍廟
墻壁上畫的十八層地獄,以及后來十年“文革”
的造反,差不多一個樣。
面對這種恐怖的運動,灰娃感到非常困惑不解,她說:“使我害怕又心急”,“那種痛苦和無奈,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人何以如此不堪呢!”這種令人不堪的運動到建國后更加變本加厲,灰娃在持續不斷的極左荒謬的運動中,“內心卻非常抵觸”,她說:“我個人在種種運動中,總是受到批判,……由于心靈受到打擊、擠壓,漸漸地我有了被虐待狂的征候。”而到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大浩劫“文革”降臨后,她目睹種種滅絕人性、踐踏尊嚴、毀滅文明的暴行,身受粗暴的沖擊和羞辱。那時的中國亂象叢生,民生凋敝,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這哪里還是她在延安艱苦的戰爭歲月里,多少次夢見的幸福美好的新中國呢?她在書中寫道:“‘文革’中的黑暗、荒謬、恐怖和殘暴,是我所從未經歷過的,而且那一切都冠以‘革命’和‘人民’的名義。看到這個真相,使我的精神大受刺激,原本已患有的輕度精神分裂,便加重升級了,表現為對一切極度不解,對外界極度恐懼。”那時,她的美麗的精神家園,也是她的精神支柱轟然倒塌,灰娃的精神終于崩潰了,她從被虐狂發展成精神分裂癥。
當然,有些像灰娃一樣從戰爭年代走過來的老革命、老干部,長期以來習慣于服從組織原則,養成了“小我”服從“大我”的思維定勢,習慣于對上級的意旨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在他們心中沒有“小我”的個人理想,認為這是不健康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只有所謂“大我”的宏偉理想。因此他們雖然在“文革”中受盡迫害,但卻沒有進行反思,反而以“要正確對待”來告誡自己,甚至表現得更左。而對于某些適應性很強的人來說,即使像“文革”這樣的浩劫,他們只要見風使鴕,趨炎附勢,改變操守,照樣可以左右逢源,活得很滋潤。灰娃與上述的這兩種人劃然而分。在殘酷的現實面前,也許,她未嘗不知她的守望是無望的,但是她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依然執著地堅守自己的理想王國,那詩化了的精神家園;她備加呵護,絕不放棄,她為此付出了精神分裂的代價。這是何等啦悲壯!灰娃也因此成為老革命、老干部中的另類。
就在灰娃痛不欲生的時候,是詩拯救了她。人的感性只有由藝術和詩來救護。因為只有藝術和詩永恒地祝福人類的激情、愛戀、痛苦,并創造出一個與現實世界對立的詩化世界。灰娃在書中敘述了她寫詩的起因:“我一直沒有也不可能有寫作的想法。直到‘文革’,殘酷的事實教育了我,讓我看清了一些人和事,引發了我的思想大解放,于是才有在個人的歡笑、痛苦、眼淚和思考之后的自我拯救。”灰娃開始寫詩是富有傳奇性的,殆有神助,且聽她道來:
一九七二年,在家里頭腦就這樣地繼續思
緒紛繁,忽然不由地拿起了筆,隨便拿到什么
紙,便亂寫亂畫。一句話,一個詞。一個字,一段
文字,隨意地寫下當下紛亂思緒的一些碎片,像
采下一片片花冠,零亂而不完整。寫時心緒似乎
寧靜了片刻。
詩到不得不寫時,才是真詩。她在寫詩時感到心緒寧靜,正是詩撫慰了灰娃。她在談到寫詩的體會時說:“我體會,詩是主動的,我乃被動者。是詩從心中催我把它表述出來,寫出的文字是我心靈的載體。這感受是幸福的、奇妙的、迷人的,是我在這人世間的最高的享受。”這是灰娃對詩的真情流露。她用詩宣泄了長期以來郁結在心中的積憤,又在詩中營造了詩化的世界。而灰娃在詩中所創造的詩化世界,正是她在現存世界中無法實現的內心中詩化精神家園的外化。是詩使她擺脫了精神分裂癥的夢魘。這是灰娃創造的奇跡,這是詩的奇跡。 有一種說法,灰娃因禍得福,是精神分裂癥使她成為詩人。這種說法是荒謬的。因為精神分裂癥患者沒有抽象意識,他們的體驗只能降低到具體形象的水平。我們知道,真正的詩是離不開抽象意識的。
(灰娃:《我額頭青枝綠葉灰娃自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