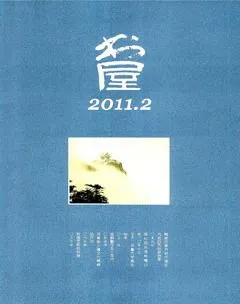也談清末新政的失敗
辛亥革命一百年之際,導致辛亥革命的清末新政成了學界熱議的話題,許多文章試圖從清末新政及其失敗中找出足以為訓的東西,以資改革開放三十年后的今日中國繼續前行。例如上海的蕭功秦先生連發《從清末改革想到當代改革》與《專制帝國的改革為何難以成功》(見《炎黃春秋》2010年第4期、第11期。以下引文均出自此)兩文,以期從失敗的清末新政中“獲得對理解當下中國改革中類似問題的啟示”。然而這兩篇文章給出的答案卻未著問題的要害,其反復強調的推行清末新政的統治者的“權威流失”——這個蕭先生十分看重的“啟示”,實際上是作者對清末新政失敗作了并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分析后,得出的本末倒置的結論。毋寧說,這樣的“啟示”對于“理解當下中國改革中的類似問題”不會產生積極作用。至于蕭先生在獲得“啟示”中為今日中國設計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發展模式”,由于作者對清末新政為什么失敗的誤解,對“當下中國改革中類似問題”的誤識,對“摸著石頭過河”的無視,所謂“發展模式”也就成了既背離歷史事實、又脫離當代實際問題、更有悖歷史發展邏輯的紙上談兵。
一、專制帝國的改革悖論
探討清末新政為什么失敗,雖然有其學理上的價值,實際上卻是誰也改變不了的“無可奈何”——中外史上專制帝國的改革都難逃失敗的命運,鮮有成功的范例。像清末改革引發革命最終導致政權垮臺,在世界上是不乏其例的。法國大革命前的路易十六改革,沙俄尼古拉二世時的斯托雷平改革,伊朗國王巴列維的“白色革命”改革,以及二十年前蘇聯戈爾巴喬夫與東歐幾個國家的改革,都是統治者自上而下發動的改革,都在改革中取得了一定的經濟成就,最終政權都垮臺在改革引發的革命中,成為專制帝國改革多以失敗告終的例證。蕭先生從清末新政破產概括出“專制帝國的改革為何難以成功”這樣的命題,是很具典型代表意義的,但他對這個問題的解答卻并未揭示出“專制帝國改革為何難以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列舉的幾條失敗的原因,像權威流失、政權的社會整合能力喪失、改革幅度過大、改革速度過快、不能把握最佳時機、改革的上下共識等等,并非是所有改革者無法克服的困難,因此也就很難抽象為“專制帝國的改革為何難以成功”的通論。其歸咎于最高統治者能力、才干,及政治智慧欠缺的說法,也不符合領導改革的那些政治家的本來面目。例如缺少“高明的政治領袖”、缺少“能闊視遠想的強勢人物”、缺少“彼得大帝式的統治者”、缺少有“道德人格力量、政治智慧和國際經驗”的政治家——這樣的歸納,不過是以勝敗論英雄、對那些改革失敗的統治者的一言以蔽之。那些推動改革的統治者雖然失敗了,但就發動改革這一點也可看出其絕非等閑之輩,都是深諳國情、熟悉時勢走向的政治家。他們的失敗雖然有著各種各樣的客觀原因,但都像蕭先生所說的“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自己發動了改革又失敗在改革上,說明他們有著相同的不可逾越的個人障礙。唯其這一“障礙”才是他們失敗的根本原因,是“專制帝國的改革為何難以成功”的共同答案。至于社會缺少多元化、統治者與全社會未能達成改革共識這樣的“原因”,其實是改革的目的,怎么會成為改革失敗的原因呢?
事實上,所有改革運動都是歷史演變的結果,都是社會需要改革又產生了改革家的時期。凡能領導國家與社會進行重大改革的統治者都不是庸才,即便是被后人頗多詬病的慈禧太后,雖然頑固守舊,但在晚清遭遇一系列的奇恥大辱后,她畢竟認識到不改革便不能擺脫貧弱無力、落后挨打的局面,甚至不改革,滿清江山都難保住。一個明白無誤的事實是,被蕭先生稱頌不已的清末新政基本上是在慈禧太后的領導下實施的,也就是說“新政明確的現代化導向,……各項現代化政策……長達十一年的……中國實質性的深刻變化”,是在慈禧太后主政下出現的。實事求是地說,中國近代民族資本工業是在清末新政時期發展起來的,有史可查的是,這個期間民族工業以年平均百分之十五的增長率發展,這在當時堪稱奇跡了。讓人匪夷所思的是,蕭先生在贊揚清末新政以后,又莫名其妙地批評新政大權掌握在載灃這個“判斷能力差,意志薄弱,外交知識貧乏,智力平庸”的“平庸之輩”手中,以致于造成清末改革的悲劇命運。這樣的批評,不僅與歷史事實不符——載灃不過是慈禧手下一個聽命的工具,談不上執掌新政大權,也是崇尚英雄史觀的蕭先生不能自圓其說的。其實蕭先生在談清末新政失敗——“專制帝國的改革為何難以成功”時,所看重的統治者的能力、才干和政治智慧的英雄史觀,可以套用在所有歷史事件上,成為這些歷史事件成功與失敗的“原因”。在“人治”的專制帝國里,握有至高無上權力的統治者不僅可以決定人的命運,甚至可以決定國家、決定歷史的命運。這是大家都明白的常識,常識說多了,就成了“正確的廢話”。
當我們沿著這個思路對清末新政深究下去的時候,就不難發現,清末新政中的統治者們不愿放棄“祖宗之法”,不愿放棄既得利益,不愿放棄享用的特權,不愿放棄手中的權力,不愿放棄受到蔭庇的舊體制。唯其這些“不愿放棄”,才使清末改革不能從正義出發、從公正做起,才使清末新政一波三折,最終裹步不前;才使改革變成了有名無實的裝點門面,才出現了人們批評的“虛假改革”、“換湯不換藥的內閣”,才使清末新政的深化改革錯過了最佳時機。清末改革的擱淺——即后人所說的政治改革不作為,致使腐敗愈演愈烈,先前的潛規則成了“明碼標價”;過去的地下交易,成了公開的生意,幾乎所有的王公大臣、所有的官員都在以權謀私,都在做權錢交易的買賣,都在不擇手段地斂財。于是清末新政在創造了經濟成就的同時,也造成了民情義憤、天怒人怨,國人從擁護新政,變成了對新政的強烈不滿,最終對統治者絕望,革命終于不可避免。前述幾個失敗的專制帝國改革,像清末改革一樣,都經歷了“人民擁護改革——人民反對改革——人民推翻領導改革的政權”這樣一個悲壯的過程。于是,蕭先生提出的“專制帝國的改革為何難以成功”便明晰起來:專制帝國里推動改革的統治者看不到社會是一個由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組成的不可分離的整體,任何一部分的變化都是以其他部分的相應變化為條件的,否則社會必定失衡。統治者只看到經濟改革帶來了市場繁榮,增加了社會財富,增加了財政收入,卻看不到這種經濟變化必須有政治的相應變化(改革)為保障,才能使社會處于正常平衡的發展狀態。沒有政治的相應變化,“經濟發展”必定造就權錢交易的廣闊空間,社會因此必定出現不穩定。所以改革最忌“孤軍深入”,在經濟改革的同時必須推動政治改革。由于改革的本質內容與要害問題是利益與權力的重新分配,所有改革最終都會改到改革者自己頭上——這便是許多學者所說的決定改革生死存亡的“坎”。這道“坎”意味著改革成功與失敗的關鍵在于能否從正義出發、從公正做起重新劃分利益與權力,即領導改革的統治者能否放棄既得利益與權力。但是這些統治者無一例外地都在這道“坎”前停步了,都“不愿放棄”,他們無法改革自己,就像人無法將自己提起來一樣。他們無力邁過這道“坎”,失敗是他們的宿命。所以說,專制帝國的改革都失敗在改革者自己手里,學界經常提到的“改革的悖論”,其要義就在這里。
雖然有極少數統治者——例如菲律賓的馬科斯、印度尼西亞的蘇哈托等自上而下發動的改革當時沒有導致政權垮臺,但其跛足的改革造成了社會失衡:權錢交易猖獗,權貴利益集團發達,貧富差距懸殊,大多數人民淪為無產者、失業者,社會長期動蕩不安,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中,這樣的改革對“最廣大人民群眾”來說不啻為一場災難,已經不是通常所說的進步意義上的改革,而是專制政體在經濟上的進一步壟斷,使其統治得到強化。不過,幾年后,他們的政權終歸還是難逃垮臺的命運。
二、權威主義的經濟神話
二十世紀的專制與民主、獨裁與共和、極權與民權的共同存在創造了人類史上最光怪陸離的時期,套用狄更斯的“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那是智慧的年頭,那是愚昧的年頭;那是信仰的時期,那是懷疑的時期;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這樣豐富的語言也不足以概括這個期間云譎波詭、天上人間的大千世界:日新月異的科技進步使先人幻想的千里眼、順風耳、上九天攬月、下五洋捉鱉,都變成了現實,在沒有戰火和天災的“通往奴役的道路”(哈耶克語)上,競留下了餓殍遍野的悲慘景象;政治家的自私貪婪和權大無邊的狂妄使人類經受了空前規模的世界大戰的災難;聯合國、貨幣基金、世貿、世行……等國際組織,使人類的各項活動日漸趨向和平共進,全球化成為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資本主義沒有像預言的“日薄西山、氣息奄奄”,相反還蒸蒸日上。沒有第三世界生活經歷的亨廷頓們,自以為是地在隔岸觀火中給發展中國家指引道路:政治權威——社會穩定——改革開放——現代化。于是權威主義被東方學界一些慣于條陳奏折的知識精英們奉若神明,為發展中國家的改革指點迷津。
實質上,權威主義既不是哲學原理,也不是思想理論,更不是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路徑,權威主義的最高原則是“穩定壓倒一切”——但正如清華大學孫立平教授所指出來的,穩定固然可以在相當長時間內維持,但同時也可能造成嚴重的社會潰敗,即社會肌體的細胞逐漸壞死,機能丟失。一切為穩定讓路,結果是許多該做的事無法做。由此一來,懸殊的貧富差距必定引起人們的不滿,出現不穩定現象;而改革帶來的溫飽解決后,人們開始在精神上政治上要求有更多的自由和發言權,這是某些人不能答應且認為是最不穩定的因素。于是,權威主義提示:用各種手段加強統治者的權威,強化統治力量,以保證政治穩定、社會穩定。這些手段不僅有法律,還有隨時出臺的法令,隨機發布的行政條例,必要時調動軍警力量,以加強對社會各方面的控制,把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中,達到“維穩”的目的。權威主義之所以被蕭功秦認為是發展中國家的唯一選擇,源于這樣的“發展邏輯”: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沒有比吃飯更大的問題了,民以食為天嘛。要解決吃飯問題就要發展經濟,要發展經濟就要先維護社會穩定,要維護社會穩定就要依靠擁有權威的統治者才能實現,所以應該擁護權威,應該崇拜權威主義。蕭先生為發展中國家設計的發展模式:“新權威——政治穩定——社會多元化——約定俗成的契約意識——民主政治”,從對這個模式的解釋中可以看出,蕭先生認為權威主義是可以發展經濟的:因為亞洲個別后發展國家的經驗是權威主義開放了市場,帶來了“市場經濟”,于是經濟社會出現了一定的活力,經濟繁榮起來,物質豐富了許多。蕭先生還想說:清末時民族資本工業的蓬勃發展,不就是統治者開禁,在壟斷的國有經濟中裂開一道縫,讓民族資本創業出現的?然而蕭先生在竭力推崇權威主義的同時,卻忘記了發展中國家昔日的經濟匱乏、人民貧困、國家貧弱,正是權威主義統治下的經濟壟斷限制了自由、扼殺了活力、杜絕了競爭、閉塞了流通,造成了市場蕭條的結果。對此,發展中國家的人民都有著刻骨銘心的記憶。作為歷史學者的蕭先生在文章中怎么可以有這樣的“歷史空白”?這樣把權威主義與經濟發展扯到一起,不僅不能讓人信服,凡是過來人都是深以為警覺的,因為他們吃盡了權威主義在經濟領域肆虐的苦頭。何況經驗和常識告訴人們,權威主義與發展經濟之間并不存在邏輯關系,不管怎么論證,都不能自圓其說。蕭先生的過人之處是,權威主義在他設計的模式中有一個前置詞:“新”,所謂新權威主義、新權威,這個“新”的唯一含義就是權威主義者看到了市場才是走出困境的出路,看到了市場經濟的巨大能量和作用,這是新權威與舊權威的根本區別。于是,具有權威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給長期封閉、停滯、蕭條的市場吹進了新風:當消費產業、消費產品、消費市場、農產品、價格一放開,經濟繁榮奇跡般地出現了。不過這種“經濟奇跡”并非像像權威主義者喋喋不休的是東南亞某國的經驗,遠在四十多年前,伊朗國王巴列維已經用他的伊朗特色的“帝國市場經濟”創造了,只是巴列維因其特殊的國情,被宗教勢力推翻了,無法記入權威主義的經驗簿上罷了。新權威創造的“奇跡”沒有什么奧秘:當市場部分地放開以后,長期在專制帝國壟斷經濟中受盡貧困折磨和精神壓抑的人們,其天生的“致富欲望”(馬克思語)像開了閘的江水般洶涌成經濟社會微觀層面上蓬勃的生機和旺盛的活力,這才是國家財富源源不斷的活水源頭,是新權威創造“經濟奇跡”的基礎。但這種“經濟奇跡”的好景不會太長,因為新權威仍控制著資源,仍壟斷著資本市場,壟斷著金融,壟斷著證券,壟斷著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上游產業。于是,新權威領導的“市場經濟”出現的生機和活力,出現的中小型企業,在短短幾年的風光后日漸被“壟斷”所吞沒。何況政府永遠熱衷于用權力的大手筆創造“經濟奇跡”,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制造了泡沫,這些泡沫一有風吹草動就會破滅,于是危機必然出現。蕭先生不應忘記,曾被權威主義者奉為楷模樣板的東南亞諸國,輝煌了不幾年就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被金融危機一夜間摧垮,某國總統在本國經濟瞬時跌入深淵中罵金融大鱷索羅斯偷襲,罵西方財團貪婪。這個義憤填膺的新權威似乎不懂得商場如戰場,罵商人貪婪,猶如罵小偷盜竊,罵強盜搶劫,不是很無知嗎?作為過來人的蕭先生,似乎直到今天仍未從東南亞新權威樣板的神話破滅中醒悟過來,并未反思新權威的權大無邊——政府進入市場“發展經濟”造成了虛假的經濟泡沫,才使國民經濟不堪一擊。要不,蕭先生怎么會在今天又操起二十多年前一度聒噪學界的權威主義崇拜,為處于改革困境中的今日中國設計出同出一轍的“發展模式”?
不知為什么,推崇權威主義的蕭先生沒有注意到,權威主義的“市場經濟”創造了“經濟奇跡”的同時,也為人人都有的自私與貪婪提供了方便,經營者利用裙帶關系敲開了權力者的后門,權力者則將權力物化后通過后門拿到市場上去交易,于是,這些發展中國家都在改革中一夜間冒出一個暴富的權貴階層。這樣,專制帝國時代僅表現在極少數特權人與最廣大人民群眾之間的并不扎眼的貧富差距,便被明目張膽的權錢交易造成的兩極分化所代替。兩極分化是社會動亂的溫床,蕭先生不惜筆墨地為新權威張目的理由——“不穩定因素”多是從這個溫床孕育出來的。上述幾個國家的改革所導致的革命都與兩極分化有關,所以兩極分化是所有統治者極為關注的事情。由此看來,改革中之所以會出現不穩定,是源于不公正改革造成的兩極分化,于是決定改革成敗的一個關鍵問題便明朗化為公正的原則。蕭先生只看重權威主義可以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中,卻無視不穩定因素是怎樣產生的這個根本問題。于是,這種顛倒的認識不僅使他的新權威“維穩”是治標不治本,而且其“發展模式”都是在這種本末倒置的結論中設計出來的。不難看出,蕭先生的“發展模式”把決定改革生死存亡的要害完全掩蓋了。
實際上在專制帝國里,統治者不僅不缺乏權威,那權威都是“君臨天下”,讓萬民五體投地、誠惶誠恐的。從官員到平民百姓,都是國家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都被牢牢地限定在相應的位置上,為國家機器的運轉老老實實地恪盡職守,唯恐失職有誤。當人的生存都系于“一元化領導”的權力體系上時,連人自身也交給權威了。誰若不唯權威的馬首是瞻,誰必定要吃虧、要倒霉,連生路都成問題,這是專制帝國里人人都能感同身受的平常事。所以在專制帝國里談加強統治者的權威,猶如畫蛇添足一樣,本來就“威加海內兮”地凜立在那里,還有什么可加強的?再加強豈不成了暴政?當然,蕭先生所說的加強統治者的權威是針對改革時期說的,因為他發現清末新政之所以失敗,是由于統治者在新政中權威流失,以至“無力駕馭大幅度的急劇改革”,無法平息“各種請愿運動與立憲活動”及“保路運動”,無法控制社會動蕩,于是“五花八門的不同階層與利益集團”“形成一種反政府的神圣同盟”,局面終于不可收拾,辛亥革命爆發,各省紛紛獨立,宣統皇帝退位,滿清王朝壽終正寢……這樣說,看上去符合歷史事實,也是順理成章的說法。然而問題的要害是:清末統治者的權威是怎樣流失的?是因改革流失的,還是因不改革流失的?如果是改革流失的,按照蕭先生的“維穩”的邏輯,這新政原本就不應該有,不應該推行改革,滿清的統治者的權威便不Y3KRe4MrSu2WlcDwhzuWt7CHvZTIaLNuYgS7e7ZvePQ=會流失,即便出現“不穩定因素”,也會被權威消滅在萌芽之中,達到“維穩”的目的。若其這樣,談什么清末新政,談什么改革,豈不也成了毫無意義的多余的話了?說歷經近三百年的滿清王朝因為推出新政,因為改革,因為資政院、咨議局這樣的“說話平臺”的出現,其權威就在國人心目中一夜間消失了,能符合當年的社會實際情況和國民心態嗎?事實上有著兩千多年專制主義文化浸淫的中國人,直到新政失敗若干年后,仍然有著帝王情結,有著發自骨子里的權威崇拜。不是嗎?連蕭先生這樣的知名學者,都還在講著太多的權威崇拜的話,更遑論百年前的國民了。所以一場清末新政,怎么能輕而易舉地將幾千年形成的對統治者的權威崇拜給改革掉了呢?若不是事關切身利益,若不是生死攸關,若不是關乎中國人的命運與前途,若不是統治者明目張膽地欺騙天下人,誰會吃飽了喝足了沒事找事地去“請愿”,去“保路”,去“立憲活動”?細究這些在蕭先生看來是應該平息的“不穩定因素”,其實并沒有要打倒誰的意思,那些一腔熱血要求改革、追求進步、希望國富民強的“神圣同盟”們,不是仍以維護滿清王朝的統治者的權威為自己行動的前提?當然清末新政最終還是引發了革命,說明統治者的權威最終還是流失了,不過流失的原因只能歸咎于統治者自己不改革、假改革。當國人正滿懷希望、充滿信心地擁護新政、期盼改革時,竟發現“改革是虛假的”、“內閣換湯不換藥”,“資政院”“咨議局”成了沒有作用的清談館,僅供裝點門面欺民惑眾,唯一的真實是,政權的力量已經無法解決改革中愈演愈烈的腐敗。不僅革命黨人絕望了,連滿清王朝俸祿養活的各省大吏都絕望了,全體中國人民都絕望了。人在絕望中還有什么選擇?今天,我們面對這些受盡奴役與屈辱、并被“不愿放棄”的統治者欺騙后而絕望了的先輩,怎么可以那么輕巧地責難他們絕望后的革命?蕭先生怎么可以對他們那么不動情地只看到王朝政權失去的“整合”能力,并為統治者的權威流失一唱三嘆,而對民族危亡下水深火熱中的當年國民無動于衷?又怎么可以既不顧歷史事實,又不顧今日中國改革困境的真實情況,在書齋里好為人師地為時下的國人獻上-一條開歷史倒車的“新權威主義”?
美國金融海嘯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三年后還未復蘇,蕭先生不應該不知道,導致這次全球經濟地震的美國次貸危機,恰恰是美國前任總統的“住者有其屋”的政治承諾在實踐上的全民不良貸款造成的。也就是說是政府干預金融參與發展經濟的結果,與當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日本金融崩盤,與中國近三十年來的幾次通貨膨脹一樣,都是政府發展經濟后的必然現象。毋寧說,都是權威主義這個幽靈的魔力多么令人驚駭的表演!所以凡有見識的經濟學家和負責任的政治思想學者,無不重提市場那只“看不見的手”,無不倡言把發展經濟的權力還給企業家,政府應該收回在市場上的那只“看得見的手”,政府應該回到本職工作——堅守正義,維護公正,為社會發展經濟提供保障與服務。在一個正義守道、公正行世的法制社會里,相信蕭先生所擔憂的“不穩定因素”會被公民克制在自身的理性中,會被社會各界特別是民間組織消化在“萌芽中”。這樣的社會不相信權威,相信法權;不相信國家,相信憲政;不相信權威主義,相信“無賴原則”——這些都是人類自十八世紀啟蒙運動以來歷經三百年時間才成熟起來的經驗!這個經驗向蕭先生擔憂的隨時會有“不穩定因素”出現的發展中國家昭示,人類文明的進步是以淡化政治權威為標志的!在一定意義上說,中世紀、專制帝國、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落后,都是因為這些國家在權威主義的籠罩下無法出現成熟的法治社會,無法實現民間自治,無法兌現作為個體的公民之自由——而人類的經驗告訴發展中國家:唯這些“法治”、“自治”、“自由”才是經濟發展的不可或缺的條件和土壤。歷史的教訓是,這一“條件和土壤”在權威主義的魔力下只能遭到破壞和沙化。作為歷史學者的蕭先生怎么能無視人類歷史的經驗教訓,無視人類文明進步的事實,自以為是地重彈權威主義的老調,借今日中國改革困境之機,推出用最具誘惑力的“民族特色”包裝起來的“發展模式”呢?
蕭功秦先生一開始就開宗明義地說道,“通過對清末新政的研究,獲得對理解當下中國改革中類似問題的啟示”。那么類似于清末新政的當下中國改革的問題是什么?他在文章中沒有具體的表述。關于“當下中國”,他卻用了不少文字談了“就我個人的研究而言……當政者現在的權威……出現了增殖”,“中國兩極分化的程度實際上已經有相當程度的下降”。對此,李維民先生已在《清末新政破產的教訓》(見《炎黃春秋》2010年第lO期)中作了有理有據的批評,這里不贅。我這里只想提醒蕭先生,若能走出書齋,到各大城市坐坐出租車一一確如眾人所說的,出租車司機都是城市的窗口和社會的溫度計——便會從他們罵一部分人是怎樣先富起來的,罵大多數人是怎樣淪為新的無產者,罵官場腐敗、教育腐敗……我們應該吃驚地發現蕭先生的“研究”結論是多么的與“當下中國改革的類似問題”南轅北轍!更不用說“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落后”,城鄉差別、工農差別不是縮小了,而是擴大了這樣的現實情況。其實,“當下中國改革的類似問題”不必“研究”,連不專門研究的平民百姓都清清楚楚,像愈演愈烈、久治不愈的腐敗;像創造了大多數中國人就業機會的民營企業、中小型企業,陷入國進民退帶來的困境;像房地產總市值為GDP的兩倍這樣的高危泡沫及民怨鼎沸的房價;像在“發展經濟”中失去土地的農民叫苦連天;像學校越來越官僚化、衙門化……這一切困境,都與中國目前的政治體制密切相關,對此,溫家寶總理已直言不諱地承認政治改革面臨困難和阻力,并大義凜然地表達了“在我能力范圍內,推動政治改革,風雨無阻,至死方休”。蕭先生何必在文章不該回避的重要問題上或“猶抱琵琶半遮面”,或“王顧左右而言他”呢?如前所述,如果說清末新政失敗在政治體制改革的不作為上,那么,時下中國走出改革困境的唯一辦法就是推行政治體制改革,別無選擇。因為產生時下中國改革困境中的所有問題的根源都指向政治體制。這是誰也掩飾不了的人所共知的事實。說到底,這個“事實”正是三十年改革開放中政治體制改革滯后的結果。
三、未來的道路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歷史就其涵有的“人類社會、某種事物的發展過程及個人經歷”的意義來說,是沒有規律可循的。規律是可以重復再現的,這“過程”與“經歷”是不可以重復再現的,歷史的變數太多,歷史總是在偶然中出人預料地或柳暗花明,或如臨深淵;或一帆風順,或一波三折……。于是人們在欲知又不可知的無奈中得出了這樣一個常識:未來是不可以預測的,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人到中老年回顧往昔時,都會發現走過的路其實都是事先不曾預料到的,都會發出“命運”的無奈感慨,“五十知天命”至理也。作為人構成的歷史又怎能是可以預料到的呢?所以縱觀人類發展史,凡是為人類設計的發展道路、發展模式在實踐中無不以失敗告終。因為它違背了“未來是不可以預測的,只能摸著石頭過河”這個常識。作為歷史學者的蕭先生不顧這一常識,煞有介事地為今日中國的走向設計什么“發展模式”,確實讓人匪夷所思。于是奇怪,蕭先生怎么連鄧小平理論中的著名論斷“摸著石頭過河”——這個家喻戶曉的“偉大告誡”也忘了?“摸著石頭過河”——沒有“模式”!這是一種實事求是的表現,三十多年前,當“堅冰已經打破,中國正在起航”時,駛向哪里?怎樣走?前程會遇到什么?沒有人知道,這是前無古人的事業。“摸著石頭過河”更體現了鄧小平在中共政治領袖中十分罕見的虛懷若谷:“摸著石頭過河”實際上是鄧小平坦誠地告訴中國人,作為領袖,他沒有理論供人們描繪未來的前景、規劃前進的道路,那是只有神才能辦到的事情;我不是神,“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只有實事求是地告訴大家“摸著石頭過河”。“只要有利于發展生產力,有利于提高綜合國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可以“大膽地試,大膽地闖”,“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因為“發展才是硬道理”。鄧小平的這些廣為傳頌的話,確實算不上什么高深的理論,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樣都是明白通曉的常識,都是實實在在的常理,唯有這些常識、常理,才彰顯出鄧小平一代政治家為中國開創了一個新時代的豐功偉績——后人不可能理解中國人曾經在遠離常識的立場上荒謬的自我折騰了很久很久。三十年過去了,這條路走完了嗎?連蕭先生這樣的學者教授還說著有悖常識的話,誰說走完了呢?
可能中國人受的苦難太深,受的壓抑太久,受的屈辱太多,所以中國人總是不愿正視現實和過去,因為有太多的絕望和不堪回首。所以中國人對自由、平等、幸福、美好的向往,總是寄希望于明天,總是寄理想于未來,“理想主義”成為這個民族的通病,中國人慣于從理想出發而不是從現實著眼空談明天怎樣、將來如何,選什么模式、走什么道路云云。實際中的問題困難雖然多如牛毛等著解決,人們竟熟視無睹無動于衷,用滿腔熱忱去規劃明天的路、描繪未來的遠景。由此衍生出來的口號、目標、計劃、指標很快地變成人們的一致行動,大干快上熱火朝天,蔚為無與倫比的壯觀。幾年后大家都會覺得這種并不成功的做法很可笑,在當年卻是人人都全身心投入且深信不疑的。其實就是事后“笑笑”而已,鮮有人做深入的反省。于是笑過之后,新的理想主義又開始行動了。雖然蕭先生身為大學教授,其知識學養肯定為我輩望塵莫及,但是先生也未能脫俗,他之所以津津樂道“發展模式”,表現出先生并未擺脫凡事從未來著眼的“理想主義”的思維習慣。以至于將“當下中國改革中的類似問題”理想化為“當政者現在的權威出現了增值”與“兩極分化的程度有相當程度的下降”,對舉國皆知、人人憂慮的最深重、最關鍵的困難——政治體制改革這個最現實的問題避而不談,竟推出權威主義作今后“發展模式”的靈魂和方法。看來蕭先生對“摸著石頭過河”這個雖淺白易懂,卻意味深長的常識并未做深入的思考。先生不應該忘記中國人曾經走過了很長一段并不“摸著石頭過河”的彎路,這條“彎路”曾經被描繪成光明的康莊大道,是通往理想社會的“金橋”。但這條“彎路”留給今人的是太多的不堪回首。
“摸著石頭過河”是句中國民間的老話,反映了老百姓的生活經驗和生存智慧。但經過政治領袖的倡導,便有了非同尋常的政治含義和思想啟迪。凡是從那段“彎路”過來的人,會痛切而又興奮地感到,政治領袖的這一倡導,既是對那段“彎路”十分委婉的否定,也是對今后中國充滿信心和智慧的勇往直前的探索。
“摸著石頭過河”是一種面對現實社會的實干精神,河是要過的,猶如問題是要解決的一樣;雖然過河是危險的,猶如解決問題是困難的一樣。“摸著石頭過河”從實際行動上揚棄了主宰中國人精神很久的“理想主義”,將那種不面對實際問題,不干實事,只會拿未來說事的空談扔進了河里。讓人感到不解的是,提出“摸著石頭過河”已經三十年了,蕭先生怎么仍舊不能“摸著石頭過河”,還要設計一個什么“發展模式”,蕭先生在文中不遺余力地批評激進主義,似乎若沒有激進主義的辛亥革命,晚清新政就會和平地、穩妥地實現君主立憲,中國的民主社會、現代化早就實現了。且不說辛亥革命及革命后中國走過的彎路,是否像蕭先生所認為的是激進主義的結果,蕭先生讓中國不“摸著石頭過河”,繞過現實中最困難最關鍵的那道“坎”,踏上他的“發展模式”是不是激進主義?歷史早已證實,不能“摸著石頭過河”,將人類推上預先設計的發展道路都是荒謬的激進主義。時下中國面對的不是走什么路、選擇什么發展模式,而是如何解決造成所有問題的“問題”——政治體制改革。雖然這是個千頭萬緒的“問題”,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唯謙卑地、敬畏地“摸著石頭過河”——讓能夠表達民間社會監督與批評的渠道健全暢通起來,這才是先生關注的“當下中國改革中類似問題”的大問題,是完善政治改革措施的基本條件,是今后改革成功的不可替代的保障;是走出目前改革困境的最有意義最可能做到的第一步,毋寧說,也是充滿希望的一步。
不是尾聲的尾聲
從清末新政十年的悲劇與今日中國改革三十年后的困境對比中可以看出,最主要的“類似問題”是政治體制改革:滿清王朝垮臺在政治改革的虛情假意上,今日中國困擾在政治體制改革滯后。不同的地方是清末朝野大部分人對問題看得清清楚楚,只有執掌大權的最高統治集團無法邁過那個生死存亡的“坎”。好在今日中國從最高領導到平民百姓,對邁過這道“坎”形成了上下一致的共識。剩下的問題就是如何克服溫家寶總理所說的“困難和阻力”了。溫家寶總理近年來多次強調政治體制改革的極端重要性,認為“如果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也不會取得徹底成功”。他還指出,政治體制改革最重要的是保證憲法和法律賦予人民的各項自由和權利,使每個人能得到自由和發展,是民主和自由的主要內涵。值此本文結尾時,忽然想到清末要求改革的呼聲主要來自知識階層;而今日中國的知識分子面對社會問題、面對改革困境、面對政治改革,竟集體失語,像蕭先生這樣負有使命感和擔當精神的人在當下中國已屬鳳毛麟角。這里不可能再現讓人無法樂觀的今日國民精神狀態,僅看看原本應是社會良心、應有社會擔當的知識分子們都在忙活什么,就知道蕭先生精神的可貴,就不能不對先生肅然起敬了。何況蕭先生拿今日中國改革與清末新政類比,是需要政治膽量與理論勇氣的。先生提出的“專制帝國的改革為何難以成功”這種振聾發聵的命題,反映出先生洞若觀火的眼光和卓然不群的智識。其肝膽相照的赤誠,無私無畏的精神,以及多么感人的人間情懷,不僅在當今學界十分稀缺,也是當代中國十分可貴的。不久前,著名學者資中筠先生呼吁知識分子應該“鐵肩擔道義”,蕭先生堪為楷模。實際上,正是先生的這種精神深深地打動了我拿起這支笨拙的筆與先生商榷,雖不敢茍同先生的觀點,卻不能不起身向先生表達我由衷的敬